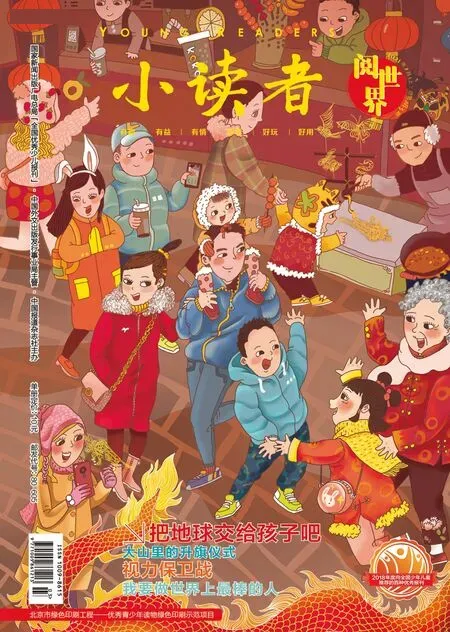視力保衛戰
□ 高源

我對大寫字母E 有心理陰影,原因說出來可能讓人有點哭笑不得:它總是出現在視力表上,由大到小,翻來覆去,不懷好意地刁難著近視的人。
我討厭視力表,因為我近視。
本來我不覺得近視有什么大不了,頂多戴眼鏡不方便或者不美觀。但我媽可不這么想,她對近視深惡痛絕。
所以當我小學四年級漸漸開始看不清黑板的時候,她的反應激烈得讓人誤以為這是什么不治之癥,仿佛近視會危及生命,仿佛我的人生已經完蛋了,并且害得整個家族都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夸張”的寫作手法。在長達數年與近視的交戰中,她的如臨大敵與焦灼憤怒,都一遍又一遍地加深我的這種感覺。
如今手機電腦早已成為必需品,孩子們的近視率越來越高,大人們雖仍擔心近視,但多少也有些司空見慣,不至于神經緊張到那個程度。而在我小時候,戴眼鏡的孩子還是少數,誰要是有一副眼鏡,大家還覺得蠻新鮮,甚至暗自羨慕——戴眼鏡的人多了一股書生氣,一看就覺得是學霸。
我是班里第一撥配眼鏡的,近視度數是一只眼150,一只眼200。眼鏡是粉色金屬細框,小心翼翼裹了層眼鏡布,裝在花里胡哨的眼鏡盒里。教室里人多,小孩子又愛打鬧,我怕眼鏡被碰壞,平時都塞進書包,只在瞇起眼也看不清黑板時才拿出來。擦眼鏡也從來都是一絲不茍,滿滿的儀式感:輕輕捏住鏡框,用流動的水或清潔劑清洗鏡片;就算沒有水,也要先朝鏡片呵幾口氣,起了白霧后再溫柔地擦,以避免小顆粒留下劃痕。
奇怪,我明明很討厭眼鏡,可為什么還是本著善良的原則,盡可能地愛惜它……
當時我個子很高,這直接導致了在班里按個頭排座位時我要坐在最后兩排。為此我苦惱了很久,虔誠地向蒼天祈禱別讓我再長個子了,因為坐在后排看不清黑板就會挨我媽的罵。不幸的是,蒼天貌似應允了。三四年后,那些發育較晚的同學噌噌噌一個勁兒地長個子,我卻絲毫不見動靜。是的,直到今天,我都沒再長高一厘米。
當年做眼保健操,我永遠是班里最積極最認真的一個,動作熟練到位,把老師感動得不行。
在室外,我也會抓住機會盡可能地遠眺——雖然周圍全是干巴巴的樓群。
在家寫作業,媽媽會不時以怒吼或呵斥的方式提醒我:“頭離書太近了!”“該休息眼睛了!”“往遠處看看!”一驚一乍,每次都把我嚇得心惶惶。其他可能會損害視力的事當然也一概杜絕,比如在過強或過弱的燈光下看書,在移動的車上看書。
諷刺又悲哀的是,無論怎樣努力,我的近視度數還是以一年一百度的速度穩步上升,初中時五百度,高中時就七八百度了。等到我成年,媽媽才松了口氣——聽說成年后眼軸不會再變長,度數基本不會再增加了。
我也終于可以理直氣壯地躺在床上看書了。后來得知并非如此,不當的用眼方式,還是會導致度數繼續加深……
我當然能理解我媽的良苦用心,青少年時期眼球還在發育,近視度數很容易加深,若放任不管,發展成高度近視是非常危險的。我這種恐怕是帶有遺傳因素的病理性近視,不是一般的措施可以遏制的。況且學習那么忙,課余時間我還抱著小說不撒手,用眼過度不可避免。只可惜,如臨大敵了這么多年,最終也還是被高度近視攻占了陣地。
假如沒有我媽及時的監督和挽救,我現在會不會已經瞎了?
近視對我的人生有什么影響嗎?
主要也就是常年戴眼鏡把鼻梁壓塌了,拉低了本來就不高的顏值,以及,坐過山車或跳樓機之前必須摘眼鏡有點麻煩吧。
以前我喜歡戴半框或無框眼鏡,鏡片厚度一覽無余,有個朋友一見我就絮叨:“呀,你這鏡片真夠厚的!多少度?”我總是認真而感動地回答左眼多少,右眼多少。問了恐怕有一百遍,卻也沒記住到底是多少度,我才明白過來,人家可能就是寒暄,并非真正關心我的視力——畢竟,還有比近視更無聊的問題嗎?
后來技術進步了,鏡片度數再深也可以做得很薄,隱形眼鏡也越來越普遍。視力保衛戰基本塵埃落定,而童年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
雖然把家里的兩張近視表都非常解氣地撕掉了,如今我一看到字母E,還是會條件反射地心里一緊,雙腿一軟,兩眼一黑。
《破譯外星語》答案:
佐羅力逃跑了!
佐羅力對公主一見鐘情,但是又被公主驚人的美貌嚇得逃跑了。
公主哭得很傷心。長得太美也是一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