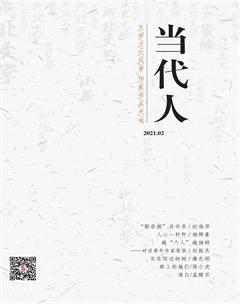走向新生的詩意(評論)
無疑,趙海萍的兩個短篇《一個人的平安夜》和《“斯奈德”啟示錄》揭示了當代個體(價值)如何獲得“新生”覺醒的故事。或許,這里應該稍微強調一下女性主義,但兩篇的主角是一男一女,正好形成了一個家庭結構的雙性組合,也就不單提了。
工業化和城鎮化以來,獨立家庭才作為倫理新常態的基本單元,逐步成為當代生活的基本模式。幼小的獨立家庭制,和一再疏離與解散的共同體家族譜系的衰亡,成為我們正在經歷的嬗變。這種嬗變,我寧愿稱之為家庭生活的當代歷險,它將在一再告別過去形態的曲折歷程中緩慢完成自身。
兩篇作品都圍繞婚姻家庭生活展開,凸顯當代個體在新倫理單元中的內在成長。《一個人的平安夜》描述一個平民家庭,男方是礦工,女方則由全職太太通過努力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男方逐步衰敗,女方通過自學穩步成功,做到了一個大酒店的客房經理。《“斯奈德”啟示錄》中的家庭基本是畸形的,殘廢的獨臂父親“懶”,啞而傻的母親“偷”,懶父親不掙錢,卻以各種方法折磨懲罰小偷母親。“我”呢,也連帶著走出一條四處行騙的路,并在神秘的報應般的身心抑郁中企圖自殺,結果偶遇了療愈者,感受到了個體的幸福。《一個人的平安夜》中的“我”,作為獨立家庭的第一代,走的是一條常居不變的道路,來達到個體覺醒,定位于現實人群層面;《“斯奈德”啟示錄》中的“我”,作為獨立家庭的第二代,走的卻是一條離家出走、四處流浪的道路——就像《一個人的平安夜》里父母雙方“誰也不跟”的第二代兒子——但他迎來了個體的新生,取自于特殊人群層面。這兩代男女,便成為既常居在家、又置身不斷迭代面臨異變的當代社會的人物縮影。
在象征意義上,我要把《“斯奈德”啟示錄》中的病名“隱匿性抑郁癥”帶得更遠。幾個人物,比如《一個人的平安夜》里與“我”作伴的小狗“妹妹”母親的主人,離婚后一再辭職、自暴自棄的丈夫,包括《“斯奈德”啟示錄》中的“我”和療愈者巫小涼,假如都是處在一種“隱匿性抑郁癥”的病態之下呢?毫無生氣的家庭生活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家人對此的無動于衷。
“我”在行騙有成的喜悅中得了抑郁癥,這個結果暴露出行騙的空虛本質。“我”在茍且中,走遍了遠方,卻唯有在同樣得了抑郁癥的巫小涼眼中,具有了詩意——她“誤認”為我是大詩人斯奈德,并因此愛上了我。小涼病得是多么嚴重呵!雖然她開了咨詢室,理智清明,但她其實一直住在“詩歌——斯奈德”這個心靈之家里,對我一見鐘情未免荒謬,但因此暴露的心靈真實,反而愈加刺目。
在這覺醒的心路歷程上,《一個人的平安夜》是靠緩慢的、相對靜態的日常生活為底座,沒有夸大,也沒有降低,漸變式的,只是女主人為了一點點改觀,逐步掌握了命運,并在社會身份的站位上一點一點覺醒了個體價值和獨立自主的意識。而《“斯奈德”啟示錄》中,種種特殊的際遇,似乎是被壓縮的,或者有所變異的:忽然得病,命定般的邂逅,自殺而不死,一見如故的愛,體悟到的生命存在感(幸福),好像人生早在一個時間點等著他了。這堪稱“頓悟式”的天啟時刻。
趙海萍的敘述特色,一是自帶氛圍的風格,一是現在進行時態的轉化。這兩篇應該還是探索階段的作品,不過已經顯露了她的語感維度:綿密、呈現,有種模模糊糊的動態感。作者在用第三人稱時,回憶時,也都能巧妙駕馭自述式的筆觸,給讀者一種“現在進行時態”的閱讀感。兩篇作品都是倒敘式,大致遵循了“現在——過去——現在”的敘述結構。《一個人的平安夜》的起點,是離婚后仍然同居的“丈夫”自顧自出去喝酒、自己在愛欲蒸騰中的心靈戰和遭遇戰,《“斯奈德”啟示錄》的起點,是行騙得病企圖吃藥自殺而(被騙)未遂的幸福一刻。作品中段則都是大篇幅的回憶,以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交互的視角敘述。這種自帶氛圍始終把讀者放在當下生活情境的敘述體驗,一如游園、移步換景。
《一個人的平安夜》最大膽的是對當夜荷爾蒙泛濫的女主角的敘述,語速非常快,房間的冰涼與寒意和身體的躁動與狂熱呼之欲出。作為女性,接納自身的愛欲,本身就是一種覺醒的考驗,這不意味著放縱,而是一種體認。獨立并非不需要再融合,這也是巫小涼以病治病的悖論式主題。就在陌生的來電中,命運再次給予了對她身體和才識的認可與誘惑,而她沒有放任自流。盡管之前她幾乎愛欲焚身、不可自制,但在愛慕者降臨時,她依然懂得把握自身。
閱讀《“斯奈德”啟示錄》的頭尾,似乎不能確定,到底是因為巫小涼的愛令獻出童男之身的他獲得幸福而新生,還是吃了她的假藥并沒真的死去而新生。好在,他終于治好了自己的抑郁癥。就剩巫小涼,不知道是否同樣獲得療愈。頭尾的敘述,均停筆在巨大的希望面前。這意味著,歷險的選擇權,還在我們自己。
(曹英人,河北廣宗人,青年文化學者,河北省網絡作家協會理事。曾入選“中國80后詩歌十年成就獎”之10佳理論建設者。)
編輯:耿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