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緣:作為讀者的焦慮
蒲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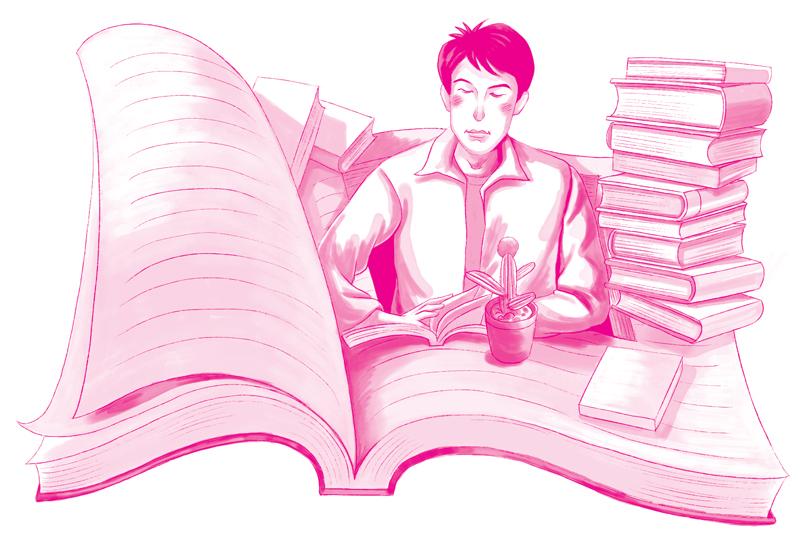

少長江漢,負笈金陵,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熱愛美術,業(yè)余從事版畫創(chuàng)作、設計、攝影工作。
和大多數(shù)小朋友一樣,我的童年記憶被試卷覆蓋。談起讀書經歷,首先想到的是作為“作業(yè)”要求的書,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片焦躁的色彩。中學語文老師每年布置的寒暑假作業(yè)都包括課本上的“必讀”名著,為檢驗閱讀效果,每一頁上勾畫、批注數(shù)量都有最低要求。《童年》《駱駝祥子》《傅雷家書》《大衛(wèi)·科波菲爾》《名人傳》《水滸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讀完的。其實,進入大部頭名著的情境十分需要精力投入,但時間規(guī)劃又是做作業(yè)永恒不變的主題,這一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令一些同學草草了事,以便留出更多時間攻克數(shù)理化難題——盡管“草草了事”也會花費不少時間。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tài),我常常選擇有計劃地認真讀。進度的指針敲打著我的神經,在有限的時間里,雖能“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終究是黃粱一夢,沒有能夠進入更加廣闊的天地。可是,閱讀不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嗎?
“5·12”地震后,成都的中學放起了長假。對于地震,大家都很陌生,也不知住在自己家里是否安穩(wěn),小區(qū)居民紛紛在公園里搭起了帳篷。我那時初中一年級,還沒有手機,自然也不存在“網癮”,除了收聽地震救援最新進展,唯一可做的便是讀書。我在一家尚未關門的書店里買到了巴金的《春》和《秋》,縮進狹小而悶熱的帳篷里讀了起來。沒有人催促進度,也沒有人規(guī)定任務,甚至沒有太多外界干擾,我便得以與覺新、覺民一同成長,直到覺非出生。他們的名字已然烙在我的大腦里,像是我的親戚一樣熟悉。相似的情景還有軍訓:本科時全年級被拉到什邡軍區(qū)軍訓,數(shù)百人在大倉庫里打地鋪,紀律嚴明。我在枕頭里藏了一本張愛玲的《小團圓》,午休時翻看一二。正如它的幽藍色封面一樣,書中的文字像一股泉水給酷熱難耐的綠色軍營帶來清涼。少年的記憶力是值得欽羨的,在這樣的情形下讀過的書更是印象深刻。本師常在自述中提及當知青時熟讀詩歌的經歷,我能與之共鳴的,便是這些微不足道的插曲。我也時常悔恨自己沒有在十幾歲時多讀一些于現(xiàn)在有用的書,可惜時過境遷,這樣的焦慮沒有與閱讀行為本身相伴,竟成了我心中的余震。
仔細思索起來,中學時我也并非不看課外書。一種情況是憑興趣選擇的書。有段時間我津津有味地讀起了三秦出版社編選的《三言二拍》。一些篇章經我一講,同學們便爭相借閱,最為精彩的故事被大家的手摸黑了書頁,一眼便能識別出這些經驗累積而成的“重點線”。這本書的命運十分悲慘——一位同學在物理課上悄悄看,最終被沒收。但有趣的是,后來我們發(fā)現(xiàn)物理老師自己也在看這本書,他的解釋是:“這種書大人可以看,小孩子不可以。”當年在物理課上看這本書的同學一向熱愛數(shù)理化,后來也考上了一流工科專業(yè),現(xiàn)在仍在讀博。身為這本書的主人,我后來也做了古代文學專業(yè)的博士生。不禁好奇,熱愛物理的同學在物理課上讀起古代小說,他是焦慮的,還是愜意的呢?我想,或許都有吧。
另一種情況是大量訂閱雜志,諸如《讀者》《中國國家地理》《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它們能最大限度地滿足課余碎片化閱讀的需要,但我抱有些許功利主義心態(tài),那便是為了積累考場作文的寫作素材。如此一來,讀書依然是一件令人焦慮的事。作為一個可鄙的讀者,我不能與作者一道體驗喜怒哀樂,僅僅是在字里行間披沙揀金,最終也只將金子打造成了流俗的工藝品,終究是心存愧疚的。直到今天,我閱讀專業(yè)領域書籍仍大多是為撰寫論文積累材料,這樣的焦慮恐怕會伴隨我一生了。
蘇軾說“人生識字憂患始”,經過這一番梳理,誠知所言不虛。值得一提的是,小學畢業(yè)時我曾在書店買到一本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的《楚辭補注》。兒時習字臨帖,也熱愛《紅樓夢》,看過各類抄本,自是對繁體豎排的舊注本充滿興趣,后來學《離騷》《橘頌》時也與教材對參。以彼時的學識,我又怎么知道王逸、洪興祖注的是什么呢?但是,這就像一粒種子,扎進了我內心深處。高考后填報了中國語言文學專業(yè),讀書不算多的我真如那句中小學生愛引的名言一般,看到書便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饑餓的人有了面包就不再焦慮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會為吃不了太多面包而焦慮。雙十一購物節(jié)緩緩落下帷幕,我今天收到了新置書架。組裝好,放上一墻新近購書,想起上電梯前樓管阿姨熟悉的問候:“你們文學院的同學買了這么多書,真的能看完嗎?”
|推|薦|的|詩|
《書齋》
周裕鍇
夏日半窗綠影,
午風一室清涼。
開卷游華胥國,
曲肱即白云鄉(xiā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