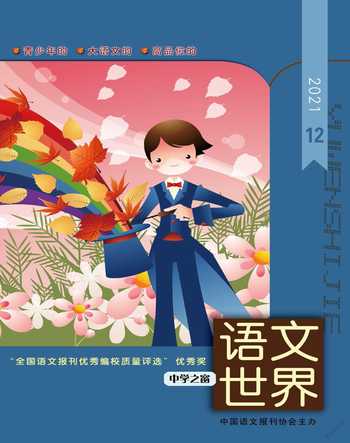《短歌行》的交響曲
鄭朝暉
曹操的《短歌行》當然可以算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不過大家都比較關注它的內容,關注曹操因為感受到生命苦短而格外渴望建功立業的壯心——我現在發現“生命苦短”常常是中國詩人抒情的觸發點,或者是邏輯起點。現在新的教材還是選了這首詩,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新的視角來感受一下這首詩呢?
按照傳統的解讀,這首詩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對酒當歌”到“唯有杜康”,這是詩歌的第一部分,是詩人因為感悟生命短促而內心充滿憂思。“青青子衿”到“不可斷絕”是詩歌的第二部分,那是對于能輔佐自己建功立業的人才的渴望之情。“越陌度阡”到“心念舊恩”則是第三部分,是對于眾人來歸,熙熙而樂的場景的憧憬之情。“月明星稀”到“天下歸心”則是詩歌的第四部分,通過問答,表達自己的雄心壯志。從詩歌情感的推進上看,脈絡很清楚。如何才能有新的視角呢?
我算是一個音樂愛好者,所以,內心反復吟誦這首詩時,自然會想象怎樣的旋律和配器才能和這樣的情感相配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其實旋律和配器,就是將主觀情感客觀化的一種手段,但是這樣更直觀可感一些。比如第一部分,“人生如朝露”,那是中外一詞的認識,比如歌德也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可見最基本的人性的感悟是無問西東的。作者想要借酒澆愁,情緒上自然是哀婉低沉的。所以這里必須要有一個“交響”的意思,比如低音大提琴,木管樂器甚至間或由定音鼓輕輕敲擊出天邊低沉的雷聲,所有這些都只是背景和底色,襯托出的必須是小提琴和中提琴哀婉如歌的淺吟低唱。
第二部分則不同,是對于遠方之人的思念與渴慕,抒情婉轉,充滿柔軟綿長的情致。不過情感還是有些微的變化,“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是一種傾訴,而“呦呦鹿鳴”開始就有了一種輕快的感覺。從“明明如月”開始,情緒又轉為哀婉。所以是一波三折的。如果比之音樂,那我心里覺得,這一部分的一開始應該延續第一部分弦樂所呈現的旋律,只是更為悠長明亮,所以不妨有一些銅管樂器尤其是小號的加入,提亮整個旋律的色調。而“呦呦鹿鳴”開始,旋律則變得輕快跳躍,豎琴配合小提琴將抒情性進一步張揚,鈴鼓、三角鐵的加入,讓音樂具有了舞蹈性;而在“鼓瑟吹笙”部分,則讓那種歡樂之情達到一個高潮。然后那種焦慮感再次進入(“明明如月,何時可掇”),低音樂器加入進來,弦樂的抒情性在高音區雖然依然維持著抒情性主題,但是逐漸地被低音區的凝重沉郁的力量摧毀,變得凌亂衰弱……
第三部分是一個短章,描述的是詩人所期待的新朋故友紛至沓來,把酒言歡的場面。在這一部分里,第二部分中有力低沉的低音部分的旋律完全被高音區和中音區接管,讓這個旋律變得明朗、抒情響亮。但這個時候,木管、大提琴和低音貝斯也不閑著,用沉郁的音色應和主旋律,不斷提醒大家人生苦短的主題,同時也告訴人們,所有這一切是詩人內心的一個夢境、一份期盼……
第四部分則是全詩的終章,也是高潮,詩人借助問答的方式,將自己內心凌云的壯志和盤托出。在樂曲的一開始,是弦樂奏出遲疑彷徨的旋律,仿佛在詢問在探索:“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這樣的詢問隨著樂曲的推進,從遲疑變得急切,甚至變得來勢洶洶不可遏制——因為“人生苦短”可不是曹操一個人的感受,而是天下所有人的感受,是所有在離亂中渴望人生歡樂者的吶喊。當這種如疾風暴雨一般的旋律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應該有定音鼓的一聲巨響,然后是強烈的休止停頓;這時,那個抒情的旋律變得莊嚴而富有使命感,聲音好像從地底下涌現出來一樣逐漸增強,莊嚴神圣,仿佛一個對于自己也是對于世界的承諾。在這個時候,那個詢問的主題再次出現,兩個旋律交匯在一起變成一股旋風一樣的洪流,而此時應該有人聲合唱的加入,讓音樂具有那種圣歌式的莊嚴雄壯的感覺,不過細心的聽者應該還是能分辨出那個“生命苦短”的低沉的音色,因為這是所有旋律向前推進的動力和底色。渾厚雄壯,直達高潮,樂曲在莊嚴雄渾但依然不失悲愴的氣氛中達到了真正的高潮。
經過我這樣一番設想,真的覺得曹操的這首詩《短歌行》,很適合讓貝多芬先生將它譜寫為一首交響曲,四個樂章,完整豐富又起伏跌宕。當然這樣的設想也再次說明,音樂是無國界的,所有藝術形式的呈現都是最普遍的人情人性使然,不必像某些所謂的大咖所以為的,喜歡西洋音樂就是“殖民思維”。B2F0871F-9F1C-4AD2-8ED0-ACADAFE6F5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