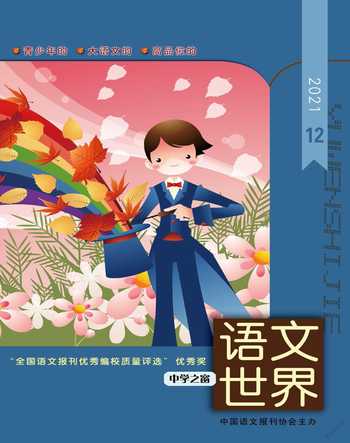郭沫若向馮至推薦老友李春潮
慕津鋒

馮至兄:
我的朋友李春潮同志,他很愿意知道德國文壇的情形,特別是最近關于歌德與浮士德的評價,特為介紹,請接談,并介紹些有關資料。您在這方面是有研究的,望您幫忙。如更有適當的朋友,并望特為介紹。此致敬禮!
郭沫若
三·七
這是中國現代文學館“馮至文庫”中珍藏的一封郭沫若書信。在信中,郭沫若將自己朋友李春潮推薦給馮至認識。因李春潮喜歡德國文學,尤其是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希望馮至能給李春潮講講這方面的知識,并推薦一些資料和這方面的專家給他。(李春潮譯著日文版《歌德詩選》,并在1945年創作《懷歌德》。)
通過閱讀該信,可以看出作為文壇泰斗的郭沫若對于提攜、幫助自己這位老友的心情,為讓李春潮對德國文學、歌德、浮士德有更多了解,郭沫若不僅親自出面將李春潮推薦給中國研究德國文學、歌德專家馮至,希望他能講講;而且還希望他再介紹一些研究專家給李春潮認識,可見他們的交情很深。
1936年,郭沫若與李春潮相識于日本,對于這段交往,李春潮好友李華飛于《在東京親聆郭老三次講話》中有過描述。
1936年春節期間,由春潮、華飛、子豪、永麟、虹冤五人在東京目黑町華飛、永麟的住所川村“貸間”開始籌備,決定各自征求成員,自費出刊,并推春潮、華飛去市川市邀請郭沫若先生參加成立會,并給刊物命名。
成立會在御茶之水附近一家“中華料理店”召開,郭老大約9時許就來了,我們二十多個文學青年鼓掌歡迎,春潮主持不拘形式的座談,然后請郭老講話,我擔任記錄。郭老命名刊物叫《文海》:“海,波瀾壯闊,容納百家。”大家聽得歡呼起來。接著轉入正題,他說:“關于‘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兩個口號的論爭,在國內的刊物上,已經發表過不少的文章,現在像已經成了過去了。在個人方面說起來,還是保持著《文學界》(1卷3期)上面那文章的意見,想來各位早已看過。‘國防文學這口號之提出,自然它有一定根據的。它的好處,除了一聽就牢記清楚之外,還能給我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
郭沫若先生對當時中國文壇兩個口號的論爭作了具體詳細的分析,給當時在日本留學的中國文學青年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
《文海》在創刊號中刊載了一篇郭沫若先生的《關于天賦》和李春潮“反駁”郭沫若先生的文章《郭沫若先生“七請”理論再認識》(以下簡稱《再認識》)。《七請》是郭沫若先生發表在《雜文》(后改名《質文》)第四期上的一篇關于詩歌創作的文章。1935年前后,中國留日學生盛極一時,單東京一地就將近三四千人,組成的進步文化團體不下十余個。當時寄居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如潛龍得水,不顧日本便衣的監視,活躍于各種講壇,并配合國內蓬勃興起的“國防文學”,給《雜文》等刊物寫了大量文章。當時有人寫信向郭先生請教詩歌問題,后發表在《雜文》第三期上,標題《“關于詩的問題”的兩封信》,此信一發表便引起了一些評論家的批評。郭沫若閱后,立即推出一篇較系統的詩論《七請》予以回應。李春潮看此文后,對李華飛表示他要寫一篇反駁郭沫若的文章。李華飛在《郭沫若在日本二三事》中,對此曾有詳細描述。
同學李春潮看了拍案叫絕,可是再次閱讀后,跑來向覃子豪和我說:“詩論寫得好,也很全面,可還有漏洞,我要寫文章駁他!”“你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我和子豪大笑,春潮把煙尾巴向地一擲:“別瞧不起人!”第二天上午李春潮拿著一大疊稿子來登門:“走,找郭先生去!”我看看他熬紅的雙眼,閱讀了題為《郭沫若先生“七請”理論再認識》的萬多字文章,對其刻苦鉆研的精神,不禁肅然起敬。
李華飛在該文中,對于郭沫若的《七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
一、文學上思想性的重要。“意識是第一著,有了意識,無論用什么方法,無論用什么形式,無論取什么材料都好。”郭的這個觀點,當時“曾惹起一番議論”,因為像這樣引伸發展,豈不是會“導致標語口號的詩了”。
二、新文學的基本要求。郭說:“我寫那幾句話時,是兼顧著文藝的政治與藝術價值兩方面來說的。新時代的文藝非有前進的意識根本不成功。”所以,“意識是第一著”。“有了意識又有很好的技巧或者是發明新的方法,那自然是最好。”這里說的“基本要求”,無非更加強調了“思想性的重要”。
三、藝術的技巧問題和作家的能動精神問題。郭說:他自己是素來尊重技巧的人。而技巧是包括在他那幾句話(注,即意識是第一著)里面的。春潮認為“意識是否可以包括技巧或代替它呢,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四、意識的修養問題。郭說:“意識并不是不修養不努力便可獲得的東西,獲得了之后不繼續修養,不繼續努力,也不能保存,而會喪失的。”春潮認為所謂“修養”與“努力”,可能意味著社會實踐,那樣應予肯定。
五、藝術家的天賦問題。郭在文中以“一個文人”為例,列成圖式:
天賦+教育+努力+ 實踐=一個文人。
春潮認為從這個公式看出,郭沫若雖沒明顯提出“七分天才,三分努力”的主張,卻把天賦擺在“一個文人”的首位,毫無疑問強調天才。春潮完全不同意這一看法,將郭的公式倒轉過來:
實踐+教育+努力+天賦=一個文人。
六、文學上宗派主義的清算和標語口號詩的新解釋。20世紀30年代,蘇共中央因鑒于普羅文學藝術的飛躍發展,狹隘的文學團體不能適應形式的需要,提出關于文學藝術團體的再組織的提案,接著舉行進步作家的大聯合,決定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藝術及文學批評的基本方針。郭當時受的影響較大,他在《七請》中主張“大家也應該緊緊地攜起手來,清算文壇上狹隘的宗派觀念,和俱樂部主義,建立起統一的文藝戰線”。
七、文藝與其他幾個部門的不可分性。與小說、詩歌表現主題的區別。郭說: “文學中的幾個部分,詩、小說、戲劇、雜文,各種形式幾乎各有職能,就和音樂、繪畫、建筑、雕刻之各個分化了一樣。它們有它們的通性,然而各有它們的個性。C358C678-5DAC-42E5-B9C8-34E8D9952E0E
李春潮在他萬余言的《再認識》中,對《七請》的“六請”洋洋灑灑作了補充的闡述,唯獨對第五“請”持相反態度。
正是因為李春潮的反駁和他執意前往郭沫若住處與之交流的想法,也就有了不久他們對郭沫若先生的拜訪,以及郭沫若創作《關于天賦》一文的原因。對于那次拜訪,李華飛也在該文中有著較為詳細的描述。
我和春潮以及他一位陜西老鄉,搭“高架電車”轉往千葉縣的市郊公共車,趕往市川市郭府。郭沫若傲岸地接過那疊厚稿,臉色隨著對文稿的翻閱而解凍,逐漸流出笑容:“春潮,你把我的文章讀得很仔細,領會也很深啊!”“我只讀了兩遍。”春潮得意地狠狠抽了口煙。“他是專攻文藝理論的。”我從旁插話。“不錯、不錯。你有幾處闡明恰到好處。個別地方我還有保留。至于天賦問題,想寫篇短文,不妨讓我再補說幾句。”“郭先生關于談天賦的文章,春潮的《再認識》,我們打算在《文海》第一期上同時發表可以嗎? ”我抓住這個良機提出請求。郭沫若爽朗地說:“完全可以。春潮的稿子留下,過兩天你們一齊來取。”
告別的時候,在郭先生住宅的庭院里,我為郭沫若、李春潮、王君、郭志鴻(郭的小兒子)攝影留念。
1936年12月底,因為李春潮的進步文學活動受到日本當局的注意,不久日本當局以“瘋人”罪名,將李春潮關押收監于東京“瘋人院”。后經郭沫若及留日同學多方營救出院,李春潮不久回到國內。回國后一直到新中國成立,李春潮在革命之余還從事詩歌創作和民歌的編輯工作。先后著有《黎炎詩集》《戰地之歌》,編輯有《山歌聯唱》一、二、三集。因喜歡歌德與雪萊詩歌,李春潮還先后譯著了日文版《歌德詩選》《雪萊詩選》。
但有關他和郭沫若的交往記載并不多。但從此信可知,李春潮和郭沫若在新中國成立后,還是時有聯系。據李春潮子女回憶:
1956年,正當父親年盛力強,創作力無比興旺時,他希望寫一部長篇抒情敘事詩……他還希望對郭沫若同志的詩歌創作,從《女神》到《新華頌》九部詩集以及其他詩作進行深入研究,寫出一系列的探討文章。
1955年,李春潮因受所謂胡風反黨集團一案賈植芳問題牽連,受到審訊,1956年3月3日去世。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位喜歡歌德、喜歡寫詩的郭沫若小友李春潮,漸漸被人們遺忘。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像一朵小小的浪花,早已被卷走,但他為新中國、為自己的文學夢想所做出的努力,我們不應忘記。謹以此文,紀念這位文學逝者。C358C678-5DAC-42E5-B9C8-34E8D9952E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