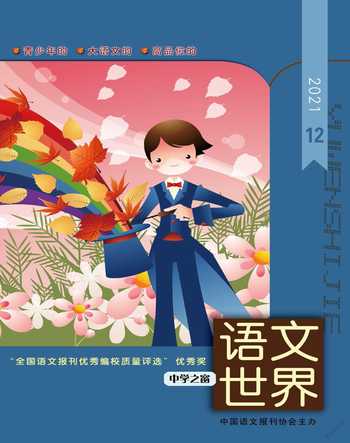夢回紅樓
厲雨嫣
“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首葬花吟,夢回紅樓。
記得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讀《紅樓夢》了,小時候素來不愛讀書,那印象中大觀園的奢華與喧鬧似乎就是兒時對《紅樓夢》的理解。寶玉的輕浮,黛玉的清高,寶釵的大方,劉姥姥的樸實,鳳姐的潑辣,其他人物各自或輕佻,或刻薄——總之,這本書只是記錄了清朝時一戶人家的興衰史。
而今我再手捧香茗,身奉書閣。“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我同呆雁般凝視著這行字——這本書在我心中,不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俗氣的故事,它開始有了更深遠的寓意,那故事背后所揭示的那些不為人知的悲戚,也讓我領略到了曹雪芹這個懷才不遇的學者的深刻思想和反叛觀念。
寶玉曾言:“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前者在婚前純潔,而在婚后受泥土玷污,自然也渾濁了。”寶玉為何有此感?這也不正是當時社會重男輕女現象的映射。憤懣難平而無能為力。我們又何曾想過:黛玉為何生性郁郁寡歡,喜散卻不喜聚?
曹雪芹正是借這所謂“閬苑仙葩”,以表達自己內心所受到的凌辱,以及對封建社會文人沒有自由故心中悲憤郁結的心境。而其他的像鳳姐之類人物的刻薄尖酸也正是那個年代猥褻小人的真實寫照。
然實則亦有善良的主兒。襲人、平兒以及前面所說到的尖酸小人,也有樂于助人、熱心、善良的一面,縱使是“機關算盡太聰明”的王熙鳳亦曾用心打點劉姥姥。這也正是作者心中對善的渴求以及對善的贊頌。然而,悲劇色彩如迷霧一般,仍籠罩著這個美麗卻極具諷刺意味的故事,榮寧二府家破人亡,到底天各一方。寶玉出家,賈雨村同甄士隱殊途同歸——曹雪芹內心對社會的極度失望和看破紅塵的那一份灑脫與傷感,令讀者不覺為之震撼。
雖說這本書字里行間顯露出社會的世態炎涼,著實令人如作者一般不經長太息,然而其中也有美好的一面:如大觀園中的一家人一同飲酒行酒令,一同開詩社時的少年恣意,一同喜接春聯的熱鬧、開心,亦如寶玉面對黛玉時的那一份討巧與能言善辯,一家人在一起的溫馨,也使讀者在閱讀時心中泛起漣漪。
其實,這也正是民間風俗、良好教養與中華民族豐富文化的真實寫照。然而越是如此,結局變越顯得滄桑凄涼,越覺不舍,若非如此,作者那犀利的語言和矛頭也不會直指人們內心的最深處,如此傷感。此外,作者向我們塑造的是一個復雜的圓形社會——有溫情,自有酷寒“嚴相逼。”
讀完《紅樓夢》,從那個壓抑封建的社會中剝離。長吁,環顧四周,自己生活的環境至少能有讓自己長吁一口氣的空間,而當時的人們呢?身不由己,思想倍受枷鎖的禁錮,他們的心情又將如何?

是故,每當讀完一遍《紅樓夢》,內心對苦難、悲愴的理解也氤氳一份深刻,對詩與遠方的追逐也越發執著。我們也理當為此而慶幸,在生活中,有艱苦,有困難,但那是人生歷程中不可避免的,和環境、觀念無關,但是,比起封建社會的人,我們至少有權利去戰勝它,我們至少有能力去戰勝它,我們至少有資格去戰勝它,這,難道不值得慶幸嗎?
靠在書架上的《紅樓夢》,靜靜地散發著淡淡的清香,一遍遍訴述著癡男怨女的悲歡離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