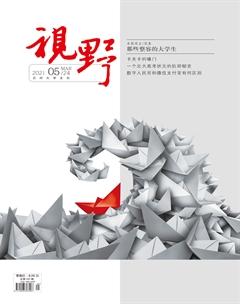外公的夜點心

默思飄逸
從前,我外婆家所在的上海老弄堂附近,有家簡陋的大餅油條店。每天清晨,天還蒙蒙亮時,這里已是爐火通紅,香氣撲鼻了。小時候,外婆帶我去小菜場買菜,每經過那里,我總會纏著她給我買一只甜大餅解解饞。“好吃伐?”這時候外婆就會笑著問我。“好吃。外婆,你也咬一口。”我一邊回答,一邊把大餅舉向外婆。“儂還是自家吃伐,省得饞勞儂外公的夜點心。”
外婆所說的“外公的夜點心”,其實也是這種大餅。不同的是,我吃的是剛剛出爐的熱大餅,而被我外公當作夜點心的大餅,是那些大餅攤頭賣剩下來的冷大餅。
我外公有在晚上睡前吃點東西的習慣。聽外婆說,這是因為早年外公在銀行做事的時候,經常要熬夜工作到很晚才能休息。這時候就需要吃點東西了,不然他的胃病就會發作。在民國年間,我外婆家的經濟狀況還過得去,外公夜點心的種類,據說也蠻多的,西式的,有面包、牛奶;中式的,有餛飩、生煎、小籠湯包、陽春面;奢侈的時候,還會有冰糖燉蹄髈、蓮子銀耳羹、紅棗桂圓湯等等……不過,在我兒時的記憶中,從沒見過外公的夜點心有這般豐富。我只是偶爾會看到外公在夜間拿著大號搪瓷杯,到深夜才會打烊的飲食店里去買一份陽春面,或是小餛飩回家來吃。
我能夠和外公一起在夜晚分吃面湯、餛飩的機會不多。因為在多數日子里,外公在睡前享用的所謂夜點心就是那種冷大餅。他的吃法很簡單,但卻有一種儀式感。尤其是在寒冬的夜晚,他靠在床上讀完了《解放日報》《文匯報》,還有一份我舅舅訂的《參考消息》這三份報紙后,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這時候,他就會披衣下床,叫外婆帶著我一起走到后樓,只見他從菜櫥里摸出兩只冷大餅來,然后,他將大餅剪成了大小不一的菱形狀餅塊,并分別放在兩只外黑內紅的湯碗里,再加些綿白糖,撒點金桂花,接著,就沖入滾燙的開水,泡成了兩碗熱氣騰騰的湯燒餅。
那干硬的大餅面塊,在開水的浸泡下,發出輕微的咝咝聲。我傾聽著這悅耳的聲音,看著在裊裊升騰的熱氣中,漸漸變幻著的餅塊形狀,像百合花瓣,像金桂樹葉,像散發出甜香味道的米黃發糕……
寒冬的夜晚,刺骨的北風在窗外呼呼作響,遠處隱隱傳來海關鐘樓悠揚的鐘聲;室內,我們祖孫仨人圍坐在掛燈溫暖的黃光下,一邊隨心隨意地漫聊,一邊品嘗著熱乎乎的湯燒餅。這時候,外公的樣子會顯得非常的怡然自得;他常常會舉起筷子指著窗外,不無感慨地說道:“嘎冷的夜里廂,阿拉有迪個熱乎乎的夜點心好吃,做人已經足夠寫意知足啦!”其時,外婆就會善意地嘲笑他:“是呀,連做皇帝也沒有儂開心噢!”
我那時還年小,只惦記著能否分吃到外公的夜點心,對他在冬夜里享用這寒酸夜宵時的那種愜意滿足的心情還完全不能理解。
屈指算來,我外公外婆離世已有近四十個年頭了。但如今每當我偶爾在街頭小吃店里吃到大餅、油條、豆漿、這些老上海人愛吃的早點時,我依然會想起外公的夜點心;想起我和外公外婆在冬夜里一起分享這份夜宵時的溫暖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