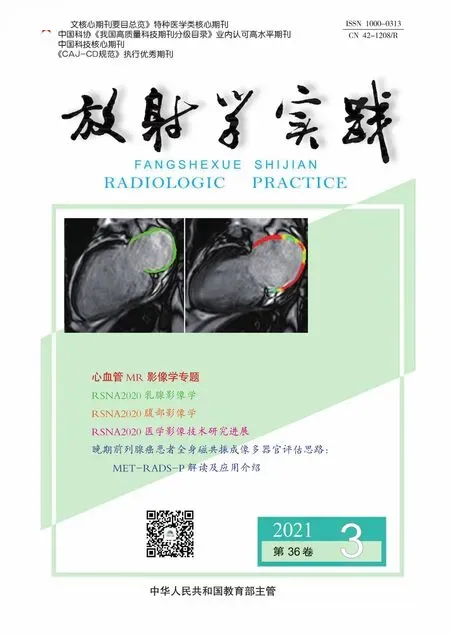CCTA定量斑塊特征及血管周圍脂肪在急性冠脈綜合征中的臨床價值
韓婷婷,穆玥,洪葉,黃明剛
急性冠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是最常見的心血管系統急危重癥,也是導致冠心病患者發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主要原因,它具有起病急、病情進展迅速、病死率高的特點[1]。研究表明,冠狀動脈粥樣硬化不穩定斑塊破裂和血栓形成導致管腔完全或不完全性閉塞引起的急性心肌缺血是ACS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2]。Skiba等[3]研究發現,由于血管周圍脂肪組織與血管壁間存在密切相互作用,當脂肪組織功能失調時,分泌大量促炎性脂肪因子和細胞因子,可直接作用于鄰近血管壁,導致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和氧化應激,進而影響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發生、發展及脫穩定化進程,故血管周圍脂肪組織與ACS的發生可能存在一定關系。心外膜脂肪組織(epicardial adipose tissue,EAT)起源于棕色脂肪組織,直接包裹于冠狀動脈和心肌表面,分為冠狀動脈外膜周圍脂肪組織(pericoronary adipose tissue,PCAT)及心肌表面脂肪組織,由于PCAT直接覆蓋在冠狀動脈外膜上,因此與遠距離的脂肪庫相比,PCAT對心血管疾病和代謝綜合征發生產生的影響更大[4]。目前國內外關于冠狀動脈CT血管成像(coronary CT angiography,CCTA)定量分析ACS患者斑塊特征、血管周圍脂肪的相關報道并不多,本研究旨在通過CCTA定量分析ACS患者斑塊特征以及PCAT、EAT等相關參數進一步探討其臨床應用價值。
材料與方法
1.研究對象
以本院胸痛中心2019年2月-2020年6月收治并住院的35例ACS患者為研究對象(ACS組),其中不穩定性心絞痛17例,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10例,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8例。另同期選取35例穩定型心絞痛(stable angina pectoris,SAP)患者作為對照(SAP組)。入選患者先行CCTA檢查隨后進行冠狀動脈血管成像(coronary angiography,CAG)檢查,結果顯示均為單支血管單個病變。臨床診斷符合美國心臟病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指南中冠心病及ACS診斷標準,表現為典型的發作性或壓榨性胸痛,隨后均經CAG、心電圖及心肌酶檢查等確診。排除既往行經皮冠狀動脈內介入治療或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慢性完全性閉塞者、肝腎功能不全、甲狀腺功能亢進、CCTA圖像質量不佳者。一般資料由住院資料或詢問病史等方式獲得,包括基線資料,高血壓(收縮壓≥140 mmHg 和/或舒張壓≥90 mmHg)、糖尿病、血脂情況、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吸煙史(正在吸煙或6個月內戒煙)等。
2.CCTA檢查及參數測定
檢查方法:采用320排640層寬體探測器CT掃描儀(Acquilion one Vision Edition,Canon Medical Systems,日本),前瞻性或回顧性心電門控技術進行掃描,檢查過程中密切監測心電圖。采用雙筒高壓注射器以4.5~5.5 mL/s流率經右肘靜脈注入60 mL非離子型對比劑碘普羅胺(370 mg I/mL)及30 mL生理鹽水。掃描范圍:氣管分叉水平至心臟膈面下,設定主動脈根部斷面為檢測層面,采用SureStart對比劑追蹤軟件進行智能觸發掃描,閾值為300~330 HU,一次屏氣完成心臟掃描。掃描參數:管電壓100~120 kV,管電流200~400 mA,掃描視野為FOV-M,探測器準直為320×0.5 mm,轉速0.275 r/s,層厚0.5 cm。
圖像后處理:將原始圖像數據傳至佳能Vitrea FX 3.0后處理工作站,選擇心動周期最佳時相進行圖像三維重組,包括容積再現(volume rendering,VR)、最大密度投影(maximal intensity projection,MIP)、多平面重組(curved planar reconstruction,CPR)。
數據測量:PCAT厚度定義為冠狀動脈與心包或冠狀動脈與心臟表面內臟層垂直厚度之和,當冠狀動脈與心臟之間存在兩個垂直的內臟層厚度時,選擇較短的厚度。于CPR短軸分別測量罪犯血管最小管腔面積處的PCAT厚度以及病變近遠端無斑塊處的PCAT厚度,PCAT比值=2 (A2+B2)/(A1+B1+A3+B3),見圖1。EAT厚度及CT值測量在2D圖像模式中進行,分別于橫軸面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狀動脈血管中段心外膜脂肪組織最厚的層面,垂直于心肌表面測量EAT厚度,并于相同區域冠狀動脈周圍放置圓形興趣區(ROI)大小控制為20 mm2,記錄ROI內EAT的CT值(圖2~3)。采用半自動軟件自動計算罪犯病變部位的各斑塊負荷、狹窄程度及重建指數(remodeling index,RI)。進入Vitrea工作站的心血管斑塊分析軟件,采用Average方式進行斑塊分析,設定不同CT值范圍區分斑塊的不同成分[5],依次將總斑塊(total plaque,TP)劃分為鈣化斑塊(calcified plaque,CP,351~1300 HU)與非鈣化斑塊(non-calci-fied plaque ,NCP,-30~350 HU),進一步將NCP分為低衰減NCP(-30~30 HU)、中衰減NCP(31~130 HU)和高衰減NCP(131~350 HU),分別計算其斑塊負荷(斑塊負荷=斑塊體積/血管體積×100%)。狹窄程度=斑塊面積/參考部位的血管橫截面積,參考部位的血管橫截面積定義為:(近+遠端正常血管橫截面積)/2。正性重構(positive reconstruction,PR)用RI表示,RI=血管橫斷面病變處管腔面積/近端參考點(無斑塊)管腔面積,RI>1.0判定為正性重構,RI=1.0為無重構,RI<1.0為負性重構。入選患者CCTA圖像均由2名高年資放射科醫師分別閱片并評價圖像質量,意見出現分歧時,經討論取得一致結果。為保證結論的準確性,所有數據測量由兩名經過培訓的醫師完成,每處測量3次取其平均值,最后綜合評價兩人所測數據的準確性后納入數據庫。

圖1 PCAT比值測量,PCAT比值=2(A2+B2)/(A1+B1+A3+B3)。 圖2 CCTA測量右冠狀動脈周圍 EAT厚度。 圖3 CCTA測量右冠狀動脈周圍 EAT CT值。
3.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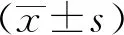
結 果
1.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ACS組與SAP組年齡、性別比例、冠脈危險因素等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兩組冠狀動脈周圍脂肪的定量分析
ACS組PCAT比值高于SAP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而兩組平均EAT厚度及密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兩組斑塊定量參數的比較
ACS組的TP、NCP、低衰減NCP、中衰減NCP負荷及RI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而狹窄程度、CP負荷、高衰減NCP在兩組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表2 PCAT與EAT厚度及密度的比較

表3 斑塊定量參數的比較
4.各類型斑塊負荷在ACS診斷中的價值比較
ROC曲線分析顯示:PCAT比值、TP、NCP、低衰減NCP、中衰減NCP的AUC分別為0.762(95%CI:0.648~0.875)、0.786(95%CI:0.679~0.892)、0.825(95%CI:0.730~0.919)、0.888(95%CI:0.811~0.966)、0.683(95%CI:0.555~0.810);敏感度分別為71.4%、85.7%、68.6%、82.9%、71.4%;特異度為分別為74.3%、62.9%、82.9%、82.9%、62.9%。根據AUC大小診斷效率由高到低依次為:低衰減NCP、NCP、TP、PCAT比值、中衰減NCP,見圖4。

圖4 各類型斑塊負荷、PCAT比值對ACS診斷效能的ROC曲線。
討 論
ACS是由急性心肌缺血引起的一組臨床綜合征,冠狀動脈粥樣硬化不穩定斑塊的破裂或糜爛所致的完全或不完全閉塞性血栓形成是其主要的病理學基礎[6]。因此,定量評估冠狀動脈斑塊性質對心血管疾病危險分層以及指導個體化一、二級預防具有一定的臨床價值。研究表明[7],與冠狀動脈血管狹窄率相比,斑塊性質的評估對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預測價值更高。本研究結果顯示,ACS組冠脈病變狹窄率高于SAP組,但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與有關報道[8]一致,可見狹窄率并不能單獨應用于心血管疾病危險程度的分層和管理,也無法完全滿足ACS防治的要求。
韋章誠等[9]研究發現,ACS組的NCP、TP負荷、RI及狹窄率均高于SAP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證實斑塊成分特征與ACS發生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另有研究表明[10],斑塊負荷較大的病變是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一致且普遍的預測因子,并且ACS與SAP患者相比,前者NCP對TP負荷的貢獻更大。本研究結果顯示,ACS患者的TP、NCP負荷均高于SAP患者,而CP負荷兩組間無明顯差異,原因可能是ACS患者的斑塊類型主要為NCP,它富含巨噬細胞等多種炎性細胞,同時分隔血液和斑塊的纖維帽菲薄,故其分泌的組織因子和蛋白酶很容易將薄的纖維帽溶解,導致斑塊破裂、引發血栓形成,進而增加急性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風險;而CP的主要成分為羥基磷灰石,其并不構成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炎癥成分,因此CP通常比較穩定,多見于SAP患者。
研究發現[11],與SAP患者相同狹窄率的斑塊相比,ACS患者的罪犯病變斑塊往往表現為低衰減、正性重構更大的特點。有研究證實[12],連續CCTA檢測出的高危斑塊(high risk plaque,HRP)進展是ACS的獨立預測指標,其中ACS患者中低衰減斑塊(low attenuation plaque,LAP)出現的頻率明顯高于SAP患者。已往的研究并未對NCP進行詳細劃分,故本研究采用半自動軟件將NCP分為:低衰減(-30~30 HU)、中衰減(31~130 HU)、高衰減(131~350 HU)的斑塊負荷深入研究。結果發現,ACS的罪犯病變與SAP患者相比其低、中衰減NCP負荷明顯增加(P<0.05),而高衰減NCP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與先前的研究結果一致[12-13]。Motoyama等[14]研究發現,通過CCTA識別密度≤30 HU的NCP與經血管內超聲(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驗證的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易損斑塊的壞死核心密切相關,這就可以解釋,本研究結果中低衰減NCP與ACS的關系密切,而高衰減NCP在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此外ROC曲線顯示,低衰減NCP的AUC值最大,且最佳臨界點出現在敏感度及特異度值均為82.9%時,整體表現最優,表明低衰減NCP對于ACS的診斷效能較其它類型斑塊更高,需要重點關注。
本研究CCTA 結果顯示,ACS患者RI均值為1.1,正性重建比例高達66%,以正性重建為主;而SAP患者RI均值為0.8,正性重建比例僅占20%,主要表現為負性重建。冠狀動脈血管重建是指在冠狀動脈粥樣硬化過程中,管腔受血液動力學的作用其結構發生代償性的變化。血管正性重建早期為了減少斑塊對血管管腔的侵犯機體會代償性降低管腔狹窄程度,但研究表明正性重建多與ACS發生密切相關,原因只能從斑塊成分上的差異進行解釋。ACS患者的斑塊類型主要為NCP,通常有著薄纖維帽的NCP容易出現血管重建的生物學行為,且以正性重建為主;隨著病程進展,斑塊鈣鹽沉積,病情處于相對穩定狀態,此時管腔已基本喪失代償能力,進而發生負性重建[15],因此血管重建與斑塊成分關系密切,相信隨著影像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其具體發生機制還會得到不斷的揭示。
由于PCAT在生理解剖上最接近冠狀動脈,故當PCAT功能失調時可產生大量炎癥細胞因子直接作用于血管壁,進而促進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發生與發展,因此它與冠心病的關系可能比整個心包脂肪組織的關系更為密切[16]。哈佛大學醫學院研究團隊[17]分析1403例ACS患者的CCTA和臨床資料,發現PCAT內出現的“fat stranding”表型可用于預測急性斑塊破裂或自發性冠脈夾層的風險,以及識別潛在高風險斑塊的存在。國外學者[18]研究發現,EAT的CT值與冠狀動脈鈣化積分(Agaston評分)呈顯著負相關,并提出EAT的CT值對于冠狀動脈病變具有潛在預測價值。Okubo等[19]通過測量103例患者的PCAT厚度,發現易損斑塊與PCAT厚度有關,而與心外膜脂肪組織厚度無關,其中高PCAT比值(>1.19)是斑塊易損性的獨立相關因素。本研究采用同樣的測量方法結果顯示,PCAT比值在ACS與SAP患者中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而EAT厚度及密度顯示無差異,原因可能與PCAT表型的多樣性以及其在生理解剖上距離冠狀動脈較整個心外膜脂肪組織更近、產生的炎性反應程度更強有關;其次本研究樣本量較少且未對研究對象的年齡、BMI進行分層,未來需要擴大樣本量并對年齡、BMI嚴格分層后進行研究。ROC曲線顯示,PCAT比值的AUC值0.762(95%CI:0.648~0.875),敏感度71.4%,特異度74.3%,在本研究中PCAT比值為定量指標,不能充分反映脂肪組織的炎性活動程度,相比之下PCAT CT衰減這種新型影像學生物指標的改變對ACS的診斷可能會更具有意義,未來需要更大規模、前瞻性的研究進一步證實。
隨著CT技術的快速發展,CCTA在心血管成像領域以其無創、快速、高分辨率成像等優勢,已然成為冠心病患者的首選檢查手段。通過CCTA定量斑塊特征及血管周圍脂肪組織綜合評估病情,有助于冠心病危險程度的分層、治療與管理,值得臨床合理推廣應用。本研究的不足:樣本量較少、存在一定選擇偏倚;目前國內外文獻對于血管周圍脂肪組織的測量方法尚無統一標準;在CCTA檢查中存在部分斑塊與對比劑的CT值重疊,容易受部分容積效應影響。筆者今后將擴大樣本量,并增加PCAT CT衰減這種新型影像學生物指標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