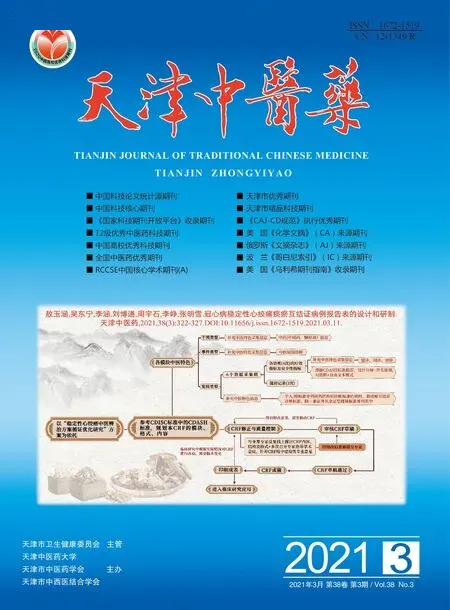三部推拿開竅法聯合康復訓練治療孤獨癥譜系障礙患兒的臨床療效觀察及作用機制探究*
孔亞敏,白青云,劉佳音
(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鄭州 450000)
孤獨癥譜系障礙(ASD)是一種腦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以社會溝通障礙、狹隘興趣和刻板行為為核心癥狀,可嚴重影響患兒的身心發育[1]。根據ASD的病因病機及臨床表現,可將其歸于中醫“語遲”“胎弱”“癲狂癥”“癡癥”等范疇。目前ASD尚不能完全治愈,罹患ASD嚴重影響患兒的生活質量及社會適應能力,給家庭帶來沉重的心理負擔及經濟負擔,并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2]。目前在國際上普遍認為ASD已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更是逐漸成為醫學背景下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研究顯示中醫藥干預在本病的治療中大有可為[2]。據文獻報道中醫針灸療法在ASD的治療中取得了滿意療效,但針灸疼痛感常給患兒帶來的恐懼心理誘發病情加重,且針灸需要留針15~20 min,小兒生來好動,難于配合,易增加斷針、滯針風險。截至目前,中醫藥領域尚未見系統的行業治療指南發布,臨床亟待探討一種安全有效、無痛苦、依從性高的中醫外治方法治療孤獨癥譜系障礙患兒。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探索和評價三部推拿開竅法對孤獨癥患兒智力康復及語言障礙的臨床療效。
1 臨床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6年1月—2019年3月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收治的96例ASD患兒,采取簡單隨機數字表法將其隨機分成觀察組48例與對照組48例。其中觀察組男36例,女12例;年齡 4~6歲,平均年齡(5.048±0.547)歲;病程1~3年,平均病程(1.633±0.268)年。對照組男 34例,女 14例;年齡 4~6歲,平均年齡(4.910±0.598)歲;病程1~2年,平均病程(1.565±0.226)年。兩組患兒基線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觀察組患兒三部推拿治療均未出現暈厥、疼痛加劇及肌肉損傷的現象及其他不良反應,對照組1例患兒因治療期間出現流感癥狀轉至其他病區進行治療,納入剔除病例,觀察組48例無脫落,見表1。

表1 一般資料分析Tab.1 General data analysis
1.2 診斷標準 符合美國精神病診斷統計手冊第5版中制定的ASD診斷標準[5]:1)在多種環境下持續表現為社會溝通與社會交往缺陷。2)局限、重復的興趣、行為或活動。3)發育早期即存在這些癥狀。4)這些癥狀引起了職業、社交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顯著障礙。5)智力發育缺陷或整體發育遲緩不能更好地解釋這些癥狀。滿足以上標準可確診為ASD,其中 1)、2)是 ASD 的核心癥狀。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符合ASD的診斷標準。2)年齡4~6歲,男女不限。3)無家族精神類遺傳疾病。4)無腦進行性病變、急慢性傳染病。5)近1個月內未接受過相關推拿治療。6)患兒家長知情,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準:1)合并嚴重心肺肝腎等重要臟器功能障礙。2)合并精神分裂癥、抑郁癥等精神障礙疾病。3)患兒家長不愿參與該研究。
脫落標準:1)因其他疾病無法進行連續治療。2)因其他原因無法進行連續治療。3)患兒家長不愿繼續參與該研究。
1.4 治療方法
1.4.1 對照組 常規康復訓練,內容主要包括語言溝通、行為矯正、感覺統合、游戲學習等;1次/d,60 min/次,連續治療 6 d,休息 1 d,1個月為1個療程,共6個療程。
1.4.2 觀察組 在對照組治療的基礎上聯合“三部推拿開竅法”,取頭面部、胸腹部、背部三部推拿按摩以益智開竅。
頭面部:1)以開竅手法,揉印堂穴后開天門100次,1 min。2)分推坎宮 120次,1 min。3)推太陽或運太陽150次,1.5 min。4)分推額陰陽、揉耳后高骨150次,1.5 min。5)五指拿頭部五經,點按百會及四神聰各穴1.5 min。6)輕掃少陽經并叩擊語言一區、二區、三區2 min。7)對口周穴位水溝、承漿、地倉,頰車進行順時針方向按揉1.5 min。以上穴位共推拿10 min。
胸腹部循經推拿:1)循經推前正中線上任脈、腎經(旁開0.5寸,同身寸)、胃經(旁開2寸)、脾經(旁開4寸)5次,1 min。2)摩腹:采用平補平瀉法摩腹2 min,并按揉中脘、天樞(雙)、關元穴、氣海穴,以手掌面或食、中、無名指指面附著于一定部位或穴位上,做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的環形移動摩擦,動作應輕柔、速度均勻協調,壓力適當,每穴各0.5 min。共5 min。
背部循經推拿:1)順經推督脈,膀胱經第一線、第二線各5次,叩擊華佗夾脊5次,2 min。2)捏脊:用提捏法沿脊柱兩旁由尾骶部向枕項部推進,捏三提一,重復3~5次,采用重提的手法刺激腎俞、脾俞、胃俞、心俞、肝俞,大腸俞等穴以加強治療,再以按揉、推法等放松手法結束3 min。共5 min。
每天1次,共20 min。每周6次,連續治療6 d,休息1 d,1個月為1個療程,共6個療程。
1.5 觀察指標
1.5.1 孤獨癥治療評估量表(ATEC) ATEC包括4個分量表(Ⅰ言語/語言/交流,Ⅱ社交,Ⅲ感覺/知覺,Ⅳ健康/身體/行為),總分0~179分,評分越高則孤獨癥病情越重。本量表由具有一定資質的醫師根據孤獨癥兒童具體情況進行評定,且評定前后為同一人。
1.5.2 療效判定標準[3]使用ATEC評分總分的減分率作為治療療效指數(N),N=[(治療前ATEC評分總分-治療后ATEC評分總分)/治療前ATEC評分總分]×100%。無效:N<20%;有效:20%≤N<50;顯效:N≥50%。療效總有效率=(顯效例數+同組有效例數)/總治療例數×100%。
1.5.3 t-PA和PAI-1指標水平檢測 空腹抽血10mL,進行血清分離后置于-20℃低溫中保存,使用酶聯免疫吸附實驗(ELISA)法對t-PA和PAI-1指標水平進行檢測。
1.5.4 統計學分析 運用統計軟件SPSS21.0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內治療前后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構成比或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ATEC評分比較 兩組治療前ATEC各分量表(言語、感知覺、社交、行為)評分均無統計學差異,治療后ATEC中各分量表(言語、感知覺、社交、行為)評分及其總分均較治療前顯著降低(P<0.05),且治療后觀察組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治療后觀察組效果優于對照組,見表2。
表2 兩組ATEC評分比較(±s)Tab.2 Comparison of ATEC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分

表2 兩組ATEC評分比較(±s)Tab.2 Comparison of ATEC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分
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
組別 例數 時間節點 Ⅰ言語/語言/交流 Ⅱ社交 Ⅲ感覺/知覺 Ⅳ健康/身體/行為 總分對照組 47 治療前 17.60±3.52 24.43±3.28 24.78±3.62 35.85±4.69 102.66±10.44治療后 11.98±3.09 18.51±4.42 18.17±3.69 23.45±5.84 72.11±13.52觀察組 48 治療前 17.06±3.42 23.90±3.73 24.73±3.62 34.58±4.98 100.27±12.73治療后 10.23±2.62* 14.83±3.51* 16.33±3.40* 19.13±5.84* 60.52±13.50
2.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總有效率為85.42%,與對照組的66.00%相比有明顯提高(P<0.05),見表3。

表3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Tab.3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例
2.3 兩組t-PA和PAI-1指標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t-PA及PAI-1指標水平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治療后兩組t-PA指標水平較治療前均顯著增高(P<0.05),PAI-1指標水平較治療前均顯著降低(P<0.05),且治療后觀察組與對照組之間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治療后觀察組效果優于對照組,見表4。
表4 兩組t-PA和PAI-1指標水平比較(±s)Tab.4 Comparison of t-PA and PAI-1 indexes between two groups(±s) 分

表4 兩組t-PA和PAI-1指標水平比較(±s)Tab.4 Comparison of t-PA and PAI-1 indexes between two groups(±s) 分
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
組別 例數 時間節點 t-PA PAI-1對照組 47 治療前 504.798±182.069 976.061±230.228治療后 636.786±131.800 801.819±175.606觀察組 48 治療前 540.798±182.069 1 046.107±198.426治療后 775.585±268.528* 611.239±133.236*
3 討論
ASD又被稱為自閉癥,是一組起病于兒童早期的廣泛性發育障礙疾病。近年來,本病全球發病率不斷增高,美國研究顯示美國兒童發病率約為1/68,男孩發病率約為女孩的4.5倍[4]。中國目前尚缺乏全國性流行病學數據,依據國際發病率粗略估算,我國約有300~500萬ASD患兒,但目前病因及發病機制不明,亦沒有特效治療藥物,大多需終身治療[5]。目前本病的治療主要采用應用行為分析法訓練(ABA)、蒙氏教育訓練等特殊教育、康復訓練及部分藥物治療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顯示綜合康復治療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病情,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研究顯示中醫干預在本病治療中大有可為[2]。
中醫認為該病因多為先天稟賦不足,肝腎虧損,髓海空虛,后天失養,氣血虧虛。該病病位在腦,與心肝腎功能失調密切相關。心主神明,肝失疏泄可致情志失調,腎主先天,先天性腦損或遺傳因素均可引發腦部病變[7]。本研究從經絡循行和臟腑功能方面辨證分析,采用三部推拿開竅法治療孤獨癥患兒,即選用頭面部、胸腹部、背部三部位實施推拿按摩。
腦為髓海、元神之府,是精髓和神明匯集發生之地,主司思維、意識、記憶、情志活動與感覺運動。腦居顱腔之中,其外為頭面,頭面部推拿具有醒腦開竅的功效。背部推拿取循經推拿與捏脊治療相結合。督脈循行從尾骨端上行脊柱內部,后入腦,上行至巔頂,督脈與腦關系密切。古有“病變在腦,首取督脈”之說。足太陽膀胱經與督脈交予頭頂,循行于脊柱兩側,入內絡于腎,腎為先天之本,生髓,主生長發育,腦為髓之海,腎精不足則腦海失養,患兒表現為先天的全面發育落后。因此頭面部推拿能寧心安神,醒腦開竅,改善口部肌肉運動,促進語言改善;背部循經推拿能達到通理經絡,填髓補腦的作用。從經絡理論來講,腦與脾腎之間也存在密切關系,手三陽經、足三陽經于頭部交匯,通過經絡達到運行氣血、平衡陰陽、調和臟腑的作用,故胃腸道作為人體第二大腦,推拿腹部通過“腸-腦軸”聯系,以“腸”促“腦”,能促進氣血運行,健脾醒腦;胸腹部循經推拿能以改善腸胃功能,促進氣血生成,健脾補腦[8]。本研究通過探索和評價三部推拿開竅法對孤獨癥患兒智力康復及語言障礙的臨床療效,對比兩組患兒治療前后ATEC評分得出,觀察組與對照組患兒治療后較治療前在言語、社交、感知覺以及行為方面均有顯著改善,且觀察組改善效果均顯著優于對照組同期。
為進一步探討推拿治療孤獨癥的作用機制,本課題組對孤獨癥患兒的血液進行相關指標檢測發現,兩組t-PA及PAI-1水平治療前后比較均有統計學差異。孤獨癥是多種原因作用下的神經結構及功能異常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Qian等[9]研究發現t-PA是一種受神經元活動調節的絲氨酸蛋白酶,與PAI-1相互影響,廣泛分布于海馬、大腦皮質以及杏仁核等腦區[10]。由于孤獨癥患兒大腦皮質狀結構的發育錯亂,導致大腦中局灶性斑塊產生,而PAI-1作為t-PA的抑制蛋白酶,能夠有效減輕斑塊對孤獨癥患兒大腦功能的損傷,同時在t-PA過度高表達時適度降低從而達到保護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11]。t-PA在大腦中表達的升高能夠促進突觸的重塑、軸突的再生、神經的生長,對調節大腦功能起到重要作用[12],與本研究中治療后t-PA水平明顯上升結果相符。治療后觀察組t-PA及PAI-1水平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說明三部推拿法能夠有效促進大腦中t-PA的表達,調節PAI-1的活性,促進孤獨癥患兒大腦功能的修復。
人體胃腸道在機體發育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腸道內存在大量的腸道菌群,處于穩態平衡的腸道菌群參與代謝營養、促進免疫、預防感染作用,惡心、嘔吐、腹痛、腹瀉、便秘等胃腸道癥狀是孤獨癥患兒常見的并發癥,有學者研究表明腸道微生物菌群的穩定狀態能夠較好地緩解孤獨癥患兒腸道并發癥[13]。五羥色胺水平的改變是孤獨癥患兒癥狀產生的重要原因,是腸-腦軸系統中的重要神經遞質,Yano[14]等研究發現腸道菌群可能對五羥色胺的合成扮演著重要角色。Sj觟gren等[15]通過對孤獨癥大鼠模型的腸道菌群進行研究發現,擬桿菌類能夠調整胃腸道腸道菌群,刺激調節腸道通透性,使腸道中五羥色胺水平顯著升高,達到緩解孤獨癥患兒異常行為的目的。Patterson等[16]研究發現腸道微生物能夠大量產生腸道神經因子,這些因子通過調節乙酰膽堿、五羥色胺等物質的釋放對神經信號傳導進行作用,改善大腦功能及異常行為。謝文娟等[17]研究發現推拿能夠有效治療小兒腹瀉,陳清云等[18]通過對腹瀉患兒進行推拿后觀察其免疫指標及臨床指標,發現推拿可以有效改善臨床癥狀,調節腸道菌群,提高免疫功能。本研究觀察組和對照組治療后在行為、感知覺、社交等臨床表現中均有統計學差異可能與三部推拿調節腸道菌群,平衡腸腦軸等因素有關。
綜上所述,“三部推拿開竅法”能補瀉同施,通天地之氣,調和陰陽,調理臟腑功能,以達補腎醒腦的目的,聯合康復訓練能夠有效改善孤獨癥患兒的行為、語言、社交等功能,其作用機制可能與三部推拿開竅法能夠調節t-AP的表達及腸道菌群,平衡五羥色胺水平,促進神經發育等因素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