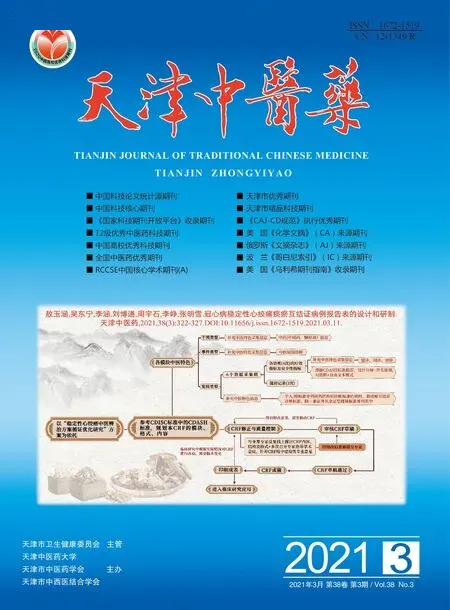基于網絡分析的《千金方》臟腑辨證配穴規律研究*
樊曉靖 ,石錦 ,楊棟婷 ,卞也 ,王立存
(1.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針灸腦病中心,天津 300250;2.脈景(杭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杭州 311121;3.天津市濱海新區中醫醫院,天津 300450;4.天津市機電工藝學院,天津 300350)
《千金方》約成書于永徽三年(652年),由《備急千要方》和《千金翼方》兩部分組成。該著作記錄了唐代及唐代以前大量醫家的針灸處方,在針灸學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1]。同時,《千金方》也是距今為止臟腑辨證理論保存最為完整的一部專著[2]。該書臟腑辨證部分所記載的針灸處方共計742個,從中挖掘其選穴配穴規律對臨床治療疾病、提高療效具有重要意義。2015年,筆者首次提出“網絡針灸學”的新概念,認為網絡分析方法能輔助研究針灸穴位的配伍組合規律[3]。因此,本研究工作將網絡分析技術運用于《千金方》臟腑病證治療針灸腧穴應用規律的研究,通過穴位處方數據的可視化處理,對《千金方》中臟腑病證對應的針灸穴位處方進行歸類、整理和挖掘,旨在探討《千金方》中按臟腑辨證治療疾病的選穴特點及配伍規律等,為指導臨床治療病證提供優選的針灸處方。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的《千金方》。
1.2 納入標準 1)以針刺、艾灸為治療方法。2)處方中腧穴個數大于等于兩個穴位。3)癥狀及取穴完全一致的多個處方作為一條處方處理。
1.3 排除標準 1)涉及婦人方與小兒方的針灸處方。2)治療方法中包含中藥、方劑等除針灸以外的方法。3)只提及經脈名稱但未明確穴名的,如“足三陰三陽”“陽蹺”等。4)只提及所屬位置但無法確定具體穴位的,如“腳大趾”“兩脅下”“肋端”等。
1.4 數據管理與數據庫建立 1)按照納入/排除標準篩選出符合研究標準的針灸處方條文,將條文中所輯錄的病癥按照《臟腑標本虛實寒熱用藥式》[4]中各臟腑本病及標病病癥進行所屬臟腑分類,建立包含來源、章節、所屬臟腑、病癥及穴位組成的Excel數據表,并參照國家標準《腧穴名稱與定位》(GB/T 12346-2006)標準規范腧穴名稱。2)按照臟腑辨證的分類方法,將表里臟腑作為一個系統,對納入的處方所對應病癥進行分類與歸納,建立了肺-大腸病癥處方數據庫、心-小腸病癥處方數據庫、脾-胃病癥處方數據庫、肝-膽病癥處方數據庫和腎-膀胱處方數據庫。其中肺-大腸病癥處方數據庫共包含針灸處方123條,心-小腸病癥處方數據庫共包含針灸處方182條,脾-胃病癥處方數據庫共包含針灸處方142條,肝膽病癥處方數據庫共包含針灸處方166條,腎-膀胱病癥處方數據庫共包含針灸處方129條。
1.5 統計學處理 本研究使用復雜網絡分析軟件Cytoscape[5]建立腧穴配伍網絡,該網絡以腧穴作為節點、以腧穴配伍關系作為邊,并從以下兩個層面進行網絡分析。第1個層面是高頻腧穴的分析,主要通過頻次分析實現,初步反映處方中選用某個腧穴的頻繁程度;第2個層面多個腧穴之間的組合規律,主要通過節點自由度、中介中心性指標分析選取,從而發掘出《千金方》按臟腑辨證用穴的核心腧穴。這兩個層面互相補充、互相印證,共同揭示《千金方》的遣方用穴的規律與特色。在提取出的網絡圖中,不同的節點代表不同的腧穴,節點的大小不同則表明其自由度不同,節點越大則表明其自由度越大,出現的頻次越多,與之配伍的腧穴也越多。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連線則表示腧穴之間的配伍關系,連線的粗細則代表關聯性的強弱,關聯性越強說明腧穴間配伍的次數越多,反之亦然。
2 結果
2.1 腧穴頻次分析結果 肺-大腸病癥處方數據庫共收錄了123條符合納排標準的針灸處方,共包含183個穴位,運用頻次391次,選穴頻次最多的為足太陽膀胱經經穴。其中太溪、天突、章門運用8次,肺俞、巨闕運用7次,尺澤、膻中運用6次。
心-小腸病癥處方數據庫共收錄了182條符合納排標準的針灸處方,共包含224個穴位,運用頻次581次,選穴頻次最多的為足太陽膀胱經經穴。其中間使、巨闕運用13次,水溝運用11次,曲池運用10次,大陵運用9次。
脾-胃病癥處方數據庫共收錄了142條符合納排標準的針灸處方,共包含217個穴位,運用頻次484次。其中章門運用9次,其中選穴頻次最多的為足太陽膀胱經經穴。中脘運用8次,巨闕、厲兌、內庭、腎俞、足三里運用7次。
肝-膽病癥處方數據庫共收錄了168條符合納排標準的針灸處方,共包含235個穴位,運用頻次615次,其中選穴頻次最多的為足太陽膀胱經經穴。其中昆侖運用11次,肝俞運用10次,前谷運用9次,百會、風池、然谷、腎俞、天柱、俠溪運用8次。
腎-膀胱病癥處方數據庫共收錄了129條符合納排標準的針灸處方,共包含180個穴位,運用頻次409次,其中選穴頻次最多的為足太陽膀胱經經穴。其中關元運用11次,復溜、涌泉運用9次,承筋、大敦運用8次。
2.2 腧穴配伍網絡核心腧穴節點分析 本研究從整體網絡圖中,提取除了自由度和中介中心性均在均值以上的節點,進而挖掘出了緊密度高、具有代表性的核心網絡,分別如下:《千金方》肺-大腸病癥處方核心輸穴為:太溪、中脘、厲兌、天容、尺澤、肺俞、章門、天突、云門、風門、然谷,其中配伍頻次最高的穴位為章門、風門。見圖1A。
《千金方》中心-小腸病癥處方中的核心腧穴為:肝俞、陽陵泉、曲池、支溝、百會、間使、心俞、合谷、腎俞、風池,其中配伍頻次最高的穴位為支溝和心俞。見圖1B。
《千金方》中脾-胃病癥處方中的核心輸穴為:本神、昆侖、天柱、間使、曲池、支溝、肝俞、合谷、章門、腎俞,其中配伍頻次較高的穴位為章門和腎俞、章門和昆侖。見圖1C。
《千金方》中肝-膽病癥處方中的核心輸穴為:陽陵泉、百會、昆侖、天柱、腎俞、中渚、曲泉、通谷、俠溪、上關,其中配伍頻次最高的穴位為曲泉和天柱。見圖1D。
《千金方》中腎-膀胱病癥處方中的核心輸穴為:復溜、太白、大敦、然谷、關元、太溪、涌泉、行間、承筋、陰陵泉,其中配伍頻次最高的穴位為復溜和關元。見圖1E。

圖1 核心腧穴配伍網絡圖Fig1 Core acupoints compatibility network diagram
3 討論
3.1 《千金方》中的臟腑辨證思想 中醫辨證有諸多方法,如衛氣營血辨證、六經辨證等,但都與臟腑辨證密切相關。《千金方》沿襲唐代以前臟腑辨證的方法治療疾病,旨在揭露疾病本質,如引用扁鵲所言“寒則腸中雷鳴,泄青白之利而發于氣水,根在大腸”“虛則傷寒,寒則便泄膿血,或發里水,其根在小腸”。《千金方》中表里辨證的思想主要用來參與病癥的虛實辨證[4],從屬于臟腑辨證之中,臟屬陰屬虛,腑屬陽屬實,表現在肺的一些疾病如肺痿、肺癆等陰性虛性疾病,書中論治時皆屬于肺臟,而咳嗽、痰飲等偏于陽性實性疾病在論治時則屬于大腸腑,其他臟腑病癥分類也均有此特點,如心系疾病癥驚悸、舌論等被輯錄在小腸腑一卷中,肝臟病癥吐血等被輯錄在膽腑卷中,尤其關于肺系疾病的治療,主要以臟病治腑、腑病治臟、臟腑同調為其治療特點[2]。
3.2 《千金方》選穴應用特點
3.2.1 以特定穴應用為主 從特定穴使用頻次統計中可以看出,《千金方》腧穴選用中運用了大量的特定穴,其中以五輸穴和募穴最多,占據特定穴使用頻率的60%以上。五輸穴是井穴、滎穴、輸穴、經穴、合穴的總稱,分布在四肢肘膝關節以下《靈樞·九針十二原》曰:“所出為井,所溜為滎,所注為輸,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五輸穴表達了臟腑經絡之氣從小到大,陽氣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6]。對于五輸穴所主病癥,《難經·六十八難》中提出:“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輸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諸逆氣而泄。”《千金方》中五輸穴的使用一是針對病癥,如輯錄在小腸腑篇的“氣短不語”、輯錄在肺臟篇的“短氣不得語”和輯錄在胃腑篇的“干嘔”取穴時都選取了肺經合穴尺澤,二是針對病癥部位,如輯錄在頭面篇的“臂不及頭”、膀胱腑篇的“轉筋在兩臂”取穴時也都選取了尺澤穴。募穴為臟腑之氣匯聚于胸腹部的穴位。《千金方》中募穴主要用于治療所屬臟腑的疾病和相表里臟腑的疾病,如脾臟卷中的“飲食不消、腹哭脹滿”和胃腑卷中的“腹中漲氣、食欲多”選穴中均有脾經募穴章門,且章門是脾-胃病癥核心處方中的腧穴。
3.2.2 以足太陽膀胱經經穴應用為主 根據《千金方》的腧穴歸經頻次統計結果顯示,《千金方》選穴主要以足太陽膀胱經為主。膀胱經為十二正經之中陽氣最盛的經脈,也是十二正經中路徑最長、循行部位最廣、腧穴數量最多、聯系臟腑組織最多、涉及病癥最廣泛的一條經脈[7]。特定穴中的背俞穴均歸于足太陽膀胱經,背俞穴是臟腑經氣輸注于背部的腧穴,“五臟居于腹中,其脈氣具出于足太陽經,是為五臟之俞。”背俞穴在正常條件下可以促進和調整臟腑的生理功能,在病理狀態下又可以不同程度地促進臟腑功能恢復生理平衡[8]。現代亦有研究證明背俞穴的分布規律與脊神經階段性分布特點大致吻合,內臟疾病的體表反應區常是相應穴位所在[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