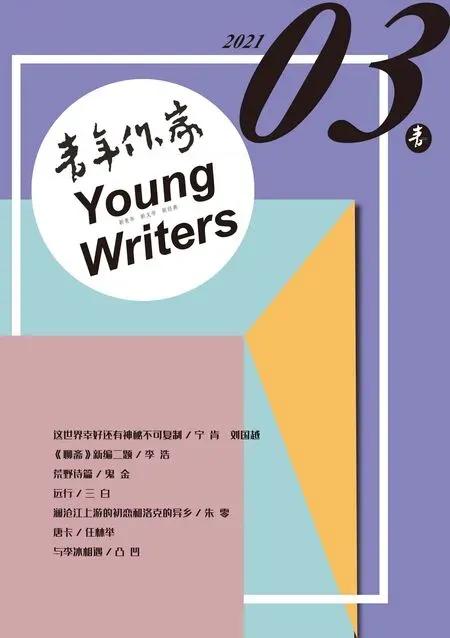唐 卡
任林舉
一
沙來左手托著一只酒盅大的顏料碗,右手擎著一支筆尖細細的畫筆,高挺的鼻尖險些貼上了面前的畫布,而手上那些微小的動作幅度卻小得如同靜止。下午的陽光透過傳習所的窗子從側面照進來,有一道明亮的弧線從頭頂至后背描繪出她凝然不動的輪廓。遠遠看過去,仿佛那并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塊石頭或一尊雕像。
光線終于映射在畫布上時,才看清那是一幅已經近于完成的唐卡。一點點金黃色的顏料正從沙來的筆尖兒落在深暗的畫面上,宛若浩瀚的時間和無限的光明正從背后照進沙來的身體和生命,再由她的身體或內心注入她手中的筆,最后從筆端溢出,凝成畫面上的色彩和線條。
這幅臻于完美的唐卡名為“財寶天王”。畫中本尊全身呈金質,色澤金黃,一面二臂,頭戴五佛寶冠,身穿黃金鎧甲,佩諸種珍寶瓔珞,右手持寶幢,左手持口吐各種珍寶的寶鼠,以菩薩如意坐姿態,坐于伏地白獅子背上,身上放射出十萬旭日之光……依經典所記,在釋迦牟尼佛住世之時,天王在佛前立下誓愿,愿護持佛法,并予眾生以財資,令其成就世間法。雖然其外在顯現為財寶天王之貌,但實質上仍是佛陀之所化現。這是藏地一尊既可佛心又遂人愿,將佛性和人性完美結合在一起的護法之神。
沙來的唐卡尚未完成,早已被人以高價訂購。如今的沙來不僅在藝術上有所成就,物質上獲得報償,最重要的是,在心性和境界上得到了提升。整整十年的精修和參悟,整整一年多的潛心繪制,在這個秋天到來之際,她終于欣喜地看到唐卡這棵生長了兩千年的藝術之樹上結出了自己的心愿之果。十年間,她通過這種紙上的修行,已經由一個心性蒙昧、不諳世事的牧女,變成了對藝術、宗教和生命都有了獨到理解和把握的畫師。難道真如人們所說,唐卡是可以卷起來的佛,對所有走進它的凡俗生命都有著度化之功?
十年前,已經25 歲的沙來,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此生能夠有今天。在平均海拔3200 米以上的壤塘,她作為一個11口牧民之家的第八女,從小到大還沒有接受過任何系統教育。她就像一朵無人賞識也無人采摘的野花,在高原的陽光下自由綻放。從不到十歲開始,她就趕著她家的牦牛群,隨著寒來暑往的風,隨著飄動不定的云,去西山,去東山,去南山,也去北山,在風霜雨雪中悄然長高、長大。在牧牛的間隙,為了貼補家用,她也會隨身帶著挖掘工具,挖一些貝母、蟲草等可以到市場出售的藏藥,但更多的時間她還是習慣于獨自發呆或對著空空的山和空空的遠天唱歌。
起初,她只是用高亢、清麗的調子唱六字箴言,據說這樣可以為自己積下功德,也可以為家人和牛群祈得平安。但是唱著唱著,她就忘記了內容,歌聲如流水、如巖漿,帶著內心的灼熱和波動,日日不停地流淌、噴涌,讓她感覺到了莫名的暢快和愉悅。不管心中有多少哀愁、凄苦或塊壘,只要那么一唱,一切都會煙消云散。她是一個極具藝術天分的女子,唱歌讓她發現了一種不借助任何對象就可以自由交流和傾訴的方式。可是,唱著唱著,她卻發現有什么東西常常會跟著自己的歌聲飛向遠方,內心里就會有一些清晰的空落和朦朧的期盼。
漸漸的,沙來發現自己更適合放牧那些順隨自己心意的歌聲,而那些歌聲又總像無形的鳥兒,飛越只知道低頭吃草的牦牛群,飛越寂靜的山谷,甚至也飛越穿著破舊衣衫的自己,飛向高處,飛向云端。她開始渴望追逐自己的歌聲去一個干凈、吉祥如云的地方。
二
從來沒有離開過牛群和山谷的沙來并不知道大山之外究竟是什么樣子,也不知道世上除了上山的小路還有許許多多的路可供選擇。但是住在縣城里的上師嘉陽樂住知道,他不但知道,而且正在整合各方善緣為她以及和她一樣的年輕人搭建一條條從山地、高原通往大千世界的道路。
2009 年,是嘉陽樂住以藏傳佛教覺囊派第四十七代法王的身份灌頂傳法、收授弟子、開示法要的第十個年頭。那是一宗善緣的發端。十年來,他走遍壤塘的山川和鄉鎮,體察了6800 平方公里縣境內的民情。在總體上游牧多于農耕的藏區,很多家庭子女眾多,少則三四個,多則十來個。有限的家財、眾多的人口,均攤之后,不但人均資財很少,而且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會出現人口過剩和相對閑置。由于放牧所需勞力少,勞動強度低,只要一個女孩子就可以應付,很多適齡男青年只能在春夏之際到山上挖一些蟲草和貝母為龐大的家庭增加些收入。冬天來臨,大地被凍成了“鐵”,待在家里的年輕人體內過剩的精力無處宣泄,便聚在一起滋生事端。酗酒者有之,賭博者有之,打架斗毆和盜竊者亦有之,失去家庭或組織約束、管教的年輕人有相當一部分成了派出所高度關注的對象。當嘉陽樂住上師發現這些現象之后,突然慈悲心動,深深地為這些年輕人感到惋惜。想一個個、一代代鮮活的生命來到這個世界,本應該更多地呈現出他們的芬芳、光明、美好和意義,就這樣一味毫無追求、漫無目標地游蕩頹廢下去,不僅是生命的巨大浪費,也會給社會和蕓蕓眾生帶來攪擾。
從這一年起,嘉陽樂住開始四處奔波,找各種機構、組織和朋友,祈求大家向那些一時丟失了心性的年輕人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從歧途上回歸正軌。然而,這些民間機構或個人,畢竟經驗和精力有限,解決這樣的問題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初步嘗試失敗后,他決定自己親自出手,通過開辦唐卡、藏香、藏藥、雕刻、堆繡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習所,將這些年輕人吸引到自己的身邊,然后再用慈愛和藝術之火將他們的心靈一點點溫暖、照亮。當有人懷疑或質疑嘉陽樂住的發心,認為他不懂世俗、異想天開時,嘉陽樂住總是回以自信一笑。他堅信每一個人的內心都不會是黑暗寒冷的永夜,不管那些年輕人年齡多大,是男是女,有沒有受過教育,出生于怎樣的家庭,每一個人的內心都存有一個善根,只要喚醒,只要呵護,只要施以陽光雨露,那顆小小的種子就會發芽生長,放大成無量光明。“盡管佛店里的燈火如豆,你也不要懷疑它能照亮整座大殿。”只要善根在,希望就在,就沒有理由放棄。
最初的傳習所,是因陋就簡,零星分散的。學員少的專業可以在師傅家里開班,學員多的專業就根據實際需要租用面積稍大的民居作為課堂。費用,當然是由嘉陽樂住個人承擔。不但傳習所的場租費,就連學員的食宿和外出學習的費用都是由他一個人出。為了更多地吸引農牧民子女特別是貧困家庭的青年,他還承諾為每一個來傳習所學習的學員提供每月300 元的資助費。為了打通人才培養以及與外界的溝通渠道,開闊學員的藝術視野,博采眾長,嘉陽樂住上師又求助、聯絡壤塘縣在上海市青浦區金澤古鎮建立了傳習基地,聘請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專家為傳習所的學員授課。夏秋季節學員在壤塘學習,冬季就去上海基地接受高校老師的培訓或到有關藝術機構進行深造、實踐、交流。經過近十年的堅持和探索,傳習所為藏區青年的成長和走出經濟困境積累了成熟的經驗,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模式。最初參加傳習所的60 名學員如今都已經成為壤塘縣縣級藝術大師,其中有6 人已經成為縣級非遺傳承人,學員們獨立創作的藝術作品被全國各地訂購,特別是唐卡,在市場上一幅最高可賣到400 萬元的高價,而且還一畫難求。
2018 年,壤塘縣進一步重視和發揚傳統文化優勢,抓住“脫貧攻堅戰”的歷史機遇,確立文化扶貧為脫貧攻堅的重要渠道,在原來傳習所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投入,擴大了規模。不但通過招商的方式在中壤塘鎮建成了規模宏大的壤巴拉非遺傳習創業園,將唐卡、堆繡、刺繡、藏紙、藏藥、藏香、陶瓷等傳習所都集中到一個園區之內,而且將“文化+旅游+扶貧”的模式推廣到壤塘縣全境,共建立各類傳習所47 個和18 個飛地傳習基地,帶動3000 余名青年以文創產品實現了脫貧致富和人生境遇的改變。
三
對沙來而言,2010 年的天是充滿了慈悲的天,仿佛特意為她開了一道縫隙,有一道奇異的光透進來,照在了她的腳前,讓她一抬眼就看見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那一年,出家多年的哥哥咔隆作為得力助手去了上師嘉陽樂住的傳習所,負責傳習所的管理工作。咔隆無意間向家人透露的各種工作信息被沙來捕捉到之后,經過醞釀、加工,變成了越來越清晰的指引和越來越迫切的愿望。
有一天,沙來居然向父母和哥哥提出要去傳習所學習技藝。這想法讓所有的家人感到意外和震驚。父母和哥哥的第一反應就是強烈反對。簡直是異想天開嘛!一個25 歲的女人,沒上過一天學,想離開放牧了十多年的牦牛群,能干成什么呢?沙來說,我能唱歌。哥哥說,沒有唱歌的傳習所。沙來說,我要畫唐卡。哥哥說,女孩子不能畫唐卡。這是藏族民間的規矩。父母也異口同聲地附和:“別說你畫不來,就是畫出來了,誰會要一個女人畫的唐卡呀?”
“不管是什么,我就是要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沙來充分發揮了她性格里的堅韌不拔。提一次要求不答應,再提一次。反反復復、不厭其煩地提,最后父母和哥哥都屈服了。“那就讓她試試吧!”傳習所里教授的技藝,哪一樣不比放牧復雜千倍萬倍!沒準兒,她去那里看看就知難而退了。哥哥決定帶沙來去傳習所,讓她自己選一種最感興趣的來學習,或哪個也不感興趣,死了那顆不安的心。
那些天,咔隆領著妹妹在縣城里分散在各處的傳習所轉來轉去,以為妹妹會性味索然,沒想到沙來卻每天都處于興奮之中。每到一處,她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藏藥的神秘、藏香的芬芳、刺繡的精致以及藏紙的神奇,每一樣都會令沙來駐足許久,但需要在內心做出決斷時,她又輕輕搖頭,選擇放棄。然而,一到唐卡傳習所,沙來的目光就直了,炯炯然,灼灼然,凝固在那些栩栩如生的畫面上。仿佛冥冥中向她發出呼喚,推動她向著一個陌生領域前行的正是這些圖畫。在高原,很多人是相信緣分的,沙來說不清自己的前世與這些畫有什么緣分,只是一見到這些畫中的色彩和法相,就感覺到了自己的怦然心動,往那里一站,就不想再走開。
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唐卡。這似乎合理也出乎意料的選擇,再一次讓哥哥咔隆感到為難,他仍然認為,在所有的選擇中,沙來的這個選擇是最錯誤的。她的錯不僅在于有違風俗,更在于這是一項對沙來來說難度太大的技藝,幾乎沒什么成功的可能。關于唐卡,雖然事先也曾經提及,但哥哥還是把自己心中的顧慮和看法又對沙來強調了一次。本以為沙來會因為這鄭重的勸告而另行考慮,沒想到她的態度會越發堅決。哥哥既不能有效說服沙來,心又總是不能落地,最后只好帶著妹妹去請教上師嘉陽樂住。
不得不說,在上師的眼中,沙來是一個極其獨特的藏女。他能判斷出來,眼前的沙來在物質條件和生活基礎方面并不及其他學員,但她一定是一個聰慧、勤奮、刻苦的人。她個子高高,身材筆挺,但看她的臉色,深暗、紅紫,足以證明她在過去的歲月里曾承受過曠日持久的風吹日曬;看她的手,大而粗糙,顯然干過數不勝數的粗活兒;再看她的眼睛,雖目光羞還有些許卑微,卻是清澈、純凈而堅定。她并不美麗,卻天生一段清雅、沉靜的氣息,正是這氣息讓上師看到了她的潛力和未來。
上師聽完咔隆的陳述之后,把目光轉向沙來,微笑著對她說:“孩子,你的選擇是對的。”雖然當時的沙來已經25歲,早已經不再是孩子,并且從面相上看,她的年齡也遠遠大于25 歲。這是上師一貫的姿態或心態,對所有來傳習所的學員,他一律稱呼為“我的孩子”。
上師深深知道自己開辦這些傳習所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他雖然并不知道具有魔法的時間,終將他的“孩子”塑造成什么樣,但他堅信,任何技藝,只要有恒久不變的愿力和信念,只要付出足夠的時間和耐性,都一定能被掌握,至于能達到什么程度,最終要看個人的慧根和愿力。關于世俗對女孩子的規約和偏見,他的態度十分明朗,在他這片佛家凈土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上師看來,人是不應該有分別心的,無論男女,不分貴賤,都是一個生命,而任何一個生命都是尊貴的,都有成長和升華的權利。技藝及其高度、價值、價格等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塑造生命,使其成就,使其圓滿。除此,一切都是過程,一切都是手段,一切都是渠道。
四
只有坐在教室里面對老師的授課,沙來才意識到自己的粗糙、無知和心浮氣躁,當然也感到無助。最初的課程幾乎讓沙來失去信心和堅持下去的勇氣。老師的聲音像天邊的雷聲,轟隆隆響個不停,她卻聽不懂那聲音所表達的意思;也像一陣緊似一陣拂面而過的風,從左耳進入,又從右耳溢出,并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沙來發現,自從來到傳習所之后,每天需要做的主要事情,并不是學習什么本領,只是要把幾乎全部精力都用在抵御課堂上難以抵御的困倦和平息隨時都可以襲來的煩躁上。正在她暗暗地盤算自己要不要向哥哥和父母承認自己選擇的失誤,要不要知難而退選擇放棄時,上師嘉陽樂住來了。
上師說,我知道你們遇到了困難,這并不奇怪。大家不要氣餒,更不要失望,反而應該高興才對。我們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讓自己變得完美的過程。這就像一場戰斗,敵人沒有出現,我們去和誰打仗?連個打仗的對象都找不到,我們如何取得勝利?現在很好,我們已經發現了隱藏在我們生命里的敵人,我們就有了目標,只要克服它、戰勝它,我們就離成功和完美更進一步。這是第一關,只要我們堅定信念,咬緊牙關挺過去,就能感受到勝利的喜悅。對你們,我有十分的信心,也堅決不會放棄,我也希望你們知道,我會一直和你們在一起,你們自己也不可以放棄。
上師的話,像陽光一樣帶著巨大的溫暖和能量照耀著沙來的心靈。很快,她的情緒就穩定下來,曾一度渾濁、昏暗的內心仿佛雨過天晴,云開霧散,困倦消失了,煩躁消失了,困惑、迷惘也消失了,繼之而來的是對新知識、新事物的好奇和渴望。
靠堅強的意志度過理論學習關之后,沙來開始跟著師傅按照唐卡的繪制程序一道道向下進展。制作畫布、學習打稿、熟悉顏料的特性和研磨制作、著色、勾線、拉金……
剛剛拿起畫筆,沙來的信心又一次遭到了沉重打擊。這一雙拿了十多年鞭子和鎬頭的手,突然攥住一支細小的畫筆,竟如擎起千鈞重物,不由自主地瑟瑟顫抖起來。也許是年齡稍大的關系,比起其他學員,沙來似乎顯得更加復雜一些,一方面她更有主見,更會把握機遇;另一方面心理壓力也更大,能夠預見和感受到的困難也更多,所以她表現得更加膽怯和自卑。她萬萬沒有想到,當初憑借直覺做出的一個選擇,竟然讓自己進入如此艱難的境地,幾乎步步是坎,坎坎連環。
此時的沙來,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已經對覺囊派唐卡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歷史上曾有“唐卡始于松贊干布,成于多羅那他”的評價。這里提到的多羅那他就是明代覺囊派第二十八代傳承人。他在世時曾以大量的藝術作品和繪畫藝術論述將唐卡藝術推向了一個巔峰,也為覺囊派留下了一門“看家”技藝。在壤塘,選擇唐卡,就算摸到了唐卡藝術的正源,攀上了唐卡藝術的最高枝。憑沙來要強的心性,她并不會質疑自己那定得高高的目標,只是每每反觀自己薄弱的基礎和空空的底子,就覺得心里發虛、焦躁、憂慮。
這個階段,嘉陽樂住上師會常常來到唐卡傳習所,一改公共場所的威嚴,盡量放低姿態,平和如自家父兄,耳提面命,叮囑沙來要放下包袱,要堅定信念,要相信自己,要堅持,要加油,并幾次單獨為她摩頂加持。上師得知沙來有一副清亮的嗓子,能唱好聽的山歌,為了增強她的自信心,便鼓勵她發揮自己的長處,展現自己的才華,想唱歌時就放聲歌唱,并在每次傳習所表演節目時,都為她做了特殊安排,由她領唱或以她的歌聲開場。
于是,沙來開始放開嗓子大聲歌唱,隨著音量的放大和歌聲的飛揚,沙來仿佛掙脫了一層無形的禁錮,原來那個畏縮的自我漸漸地伸展開了蜷曲的腰身。嘹亮的歌聲讓沙來的靈魂超越了自己平平的相貌和拙重的肉身,看到了潛隱其后的另一個更加年輕、輕靈、激情、美麗和充滿了創造活力的自我。歌聲雖已漸漸停息,但有一種透射著力量和信念的光芒卻永久地駐留在沙來的眼眸之中。
很快,她的繪畫便進入著色階段,涉及到色彩所出的顏料。這是唐卡甚至一切繪畫的入口。特別對于唐卡的繪制,顏料還有著特殊的意義。一般來說,唐卡的基本顏料都來源于自然。由于天然礦物顏料具有穩定的物理和化學性質,所以有色彩鮮艷耐久、可保持千年而不褪色的特點。礦石顏料通常用于繪制唐卡的底色。植物顏料主要從罕見的花、草、樹葉、樹皮中提取,這些植物顏料都耐光、耐熱,具有極佳的色彩壽命,通常用于色彩的過渡。此外,還有一些出自動物身體的原料,如蟲子皮、貝殼、鹿角粉等,這些顏料大部分用于唐卡的勾線。因天然礦物的稀缺、昂貴、耐久,如金、銀、綠松石等,加之神佛的繪畫主題,使得唐卡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先天的永恒指向。
作為一個優秀的唐卡繪制大師,必須對每一種顏料的特性都有一個深入的認識和理解,顏料的基本顏色、兼容性、持久性、隨著時間推移所表現出來的變化等等都要做到了如指掌,運用合理、準確,恰到好處。因為對于一幅畫來說,色彩就是主體的衣飾、發膚和氣血,甚至是靈魂,必須在時間的淺表和深處都表現出始終如一的和諧,那是確保主尊具有不竭“生命力”的先決條件。對沙來來說,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大坎。如果把唐卡繪畫藝術比作一座大山,這一坎,就是登頂前最后一道陡坡。沙來雖然已經斷續畫過幾幅習作,但這次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種困惑。
一幅正在著色的唐卡,靜靜地擺在那里,已經有幾天時間了。沙來基本是一直枯坐在畫布前一筆未動,她不知道如何完美處理唐卡中那尊金剛的手腕與護腕之間的過渡線,不知道那道線應該是金色的還是銀色的,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唐卡在整體感覺上要與以往大師的基調一致,還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處理。
這時,嘉陽樂住上師剛好到畫室來巡查,他站在沙來身后看了許久,猜出了沙來的困惑。上師像是針對沙來一個人說,也像是對畫室中所有人說:“藝術是對生命和美的理解與表達,本身就是善、愛和慈悲。當你發現自己畫不好的時候,一定是自己的情緒或心性出了問題,或者自己還不夠完美。這個時候就不要一味糾結下去,要反觀自身,看看是什么成為你的障礙,發現了障礙,然后消除障礙,你就通達了,畫畫就是修行。這時,你應該離開畫室,去調整自己的情緒或生命狀態,唱唱歌,跳跳舞,甩一甩袖子,或做一些幫助別人的事情,讓自己的情緒和心境變得美好起來。只要你自己變得美好了,你就能理解你的畫,就能與那些線條和色彩產生共鳴,你就知道接下來應該怎么處理。于是,你的色彩和線條也就變得流暢、潔凈、和諧、美好起來了,你的畫也就圓滿了……”
五
沙來終于知道自己的問題出在了哪里。原來,她是需要一種想象中的色彩來完成自己的創造。由于傳習所內或市場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顏色,盡管煞費苦心在各種顏料譜系里搜尋,還是沒有自己想要的結果,她正是為此事焦慮,一籌莫展。現在,她已經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也知道必須怎樣做。經過再三咨詢、斟酌和考慮,他決定在礦物顏料庫里選擇一種金黃色的砒石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孔雀石混合研磨。她要的就是那種明黃里透著些許藍綠的奇異色彩。因為沒有先例和現成的配方,她需要親自動手并根據研磨后的混合效果判斷,之后還需要添加哪種礦石,添加多少。邊磨,邊摸索、調配,經過數次調適,最終得到自己理想的顏色。通常,研磨出一種單一的顏色,需要一個星期或半個月的時間,如果制造這種復合顏色,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一個坐在地上的石臼,含住一個從天棚上吊下來的石杵,中間是經過漂洗和浸泡過的小塊礦石。沙來就端坐在石臼旁手扶石杵上的木柄,一圈圈用力研磨。一圈圈,旋轉復旋轉,重復再重復,像誦經,像念咒。在節奏單調的動作和聲音中,一種恒定的力量和信心靠恒定的時間向前推動著,如魔法均勻地施加于礦物之上。十日之后,石塊變成了齏粉,齏粉化作了巖漿,巖漿中那些成分不同的微小顆粒通過一系列物理的或化學的方式融合到一起,終于成為一種鮮艷的顏料。當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能變成了藝術追求之中的可能,沙來似乎終有所覺悟,大約這既是愿力之功,也是時間的造化。
有一天,沙來在工作間隙路過刺繡傳習所,遠遠看見戈登特聚精會神工作的背影,突然心有所動,決定轉到他的工作臺上去看一看。
這個比沙來小10 歲的大男孩,是沙來在傳習所演出時認識的,因為他生得魁偉英俊,被選出來飾演藏戲里的格薩爾王。沙來站在戈登特身后一米多遠的距離,并沒有打擾他,靜靜地看他一雙粗壯的大手在那里飛針走線。說是飛針走線,其實很難看到他兩手間那條細細的彩線,只能看到他的手在空中上下翻飛,只是在“舞”。奇妙的是,一幅美麗的鳶尾蘭在他的“空”舞中已經生動地顯現于他面前的畫布之上。
眼前的情景讓沙來感慨萬千,時間果然能夠塑造出很多奇跡。誰能想到當年那個頂著一頭紅發、烈馬般桀驁不馴的男孩會有如今這般光景呢?僅僅十年的時間,那個騎著摩托車在草山上挖藥、橫逛的男孩,那個抽煙、酗酒、打架斗毆的男孩,一次賭博就輸掉家里兩頭牦牛的男孩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呈現于人們眼前的竟然是一個俊美儒雅的“格薩爾王”,也是縣級刺繡非遺傳承人。如今,他不但野性盡收,全身心地投入到刺繡技藝,而且還戒煙、戒酒、戒葷,成為一個嚴格的素食者。
沙來似乎又悟出了某種人生的真諦,她悄悄回到了自己的畫位上,開始用舌尖洇開蘸筆尖上的顏料,一筆筆將顏色點到畫布上。一點點,一點點,摒除雜念,凝神靜氣,一絲不茍……仿佛時間、身心和整個世界都隨著那洇開的顏料一點點化開、消散,只有色彩在畫布上堆積、顯化,只有浩瀚如海的大愉悅在無邊際地漫延——
沙來發現,當一個畫師真正如上師要求的那樣,讓心靈“歸零”時,時間便失去了方向和邊際。似乎剛剛坐下,一天就過去了;似乎剛剛畫出個輪廓,一個季節就過去了;似乎剛剛有了一個完整的表達,一年就過去了。有時,幾年時光就如短暫一瞬,有時,短暫一瞬竟然漫長如永恒。
多年后,沙來的一幅“財寶天王”宣告完成。上師嘉陽樂住聞訊帶人前往欣賞、評鑒。
“這幅唐卡是同一個主題中極其獨特的一幅,構思巧妙,氣韻通透,特別是對線條的理解以及金線的運用,充分體現了畫師心性的成熟和技藝的高超……”當沙來的唐卡出現在眾人面前,就有專家忍不住搶先發言。
嘉陽樂住上師卻突然在兩米之外止步,靜觀,站在唐卡前良久無言。幾年來,他一直不太敢相信一個從山谷里走來的大齡女學員竟能把一幅唐卡畫得如此完美,更沒敢實實在在地指望有一天她能夠成為一位優秀的畫師。如今,這幅唐卡完美告成,儼然是一個小小的奇跡,帶給他的不僅是一個意外驚喜,還是一個深深的感動。
那天,他并沒有對那幅唐卡做任何評價,可是當他轉身離開時,人們卻從他眼中看到了閃動的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