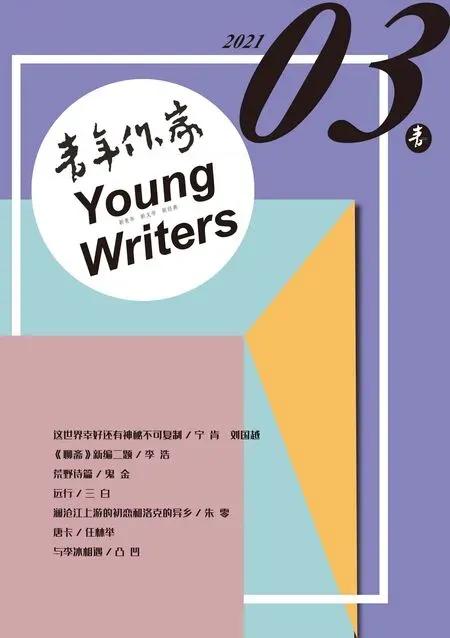橡皮擦
沙 爽
午夜失眠,隨手翻翻微博,見《科技日報》登出了一則簡短新聞,說北京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萬有與伊鳴團隊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可以精準“刪除”動物的特定記憶:
該研究在兩個不同的實驗箱里誘發大鼠對箱子的恐懼記憶,進而將基因編輯技術與神經元功能標記技術結合,通過對特定印記細胞群的基因編輯精確刪掉大鼠對其中一個箱子的記憶,而對另外一個箱子的記憶完好保留。
這一天是2020 年3 月24 日,日本正式宣布將東京奧運會推遲至一年后召開。意大利、美國和西班牙的新增病例持續攀升,中國大部分城市大中小學的開學日仍遙遙無期,整個世界淪陷于新冠病毒帶來的恐慌之中。微信朋友圈里,有人開玩笑說,應該把這一年從歷史紀元中刪除,這樣東京奧運會仍可以在2020 年如期召開,人們也不必為虛度的一歲而焦慮不安。短暫的莞爾之余,面前仍舊是陰沉凝滯的漫長時間。疫苗雖已進入實驗階段,但真正應用于臨床,至少要等到一年以后。兩三百年來,現代醫學原本一路突飛猛進,不僅放言要攻克癌癥和艾滋病,還要讓納米機器人深入人體,隨時修補所有被衰老和疾病損害的器官……誰能想到呢,小小的一個病毒,便狠狠擊中了現代醫學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這樣的日子里看到這樣一則新聞,真是讓人心頭五味雜陳——如果刪除記憶是獲得重生的唯一方案,當瘟疫結束,曾經在悲傷、恐懼和絕望中苦苦掙扎的幸存者,會不會寧愿刪除關于這場瘟疫的全部記憶?
如果我們的海馬體能夠自行辨識記憶的類別就好了——如果是愉快的記憶,就將它們輸送往大腦皮層進行備份;反之,與痛苦有關的記憶將被永遠封存在海馬體內,等待另一個新生事件取而代之。事實是,人體確實擁有類似機能,一只隱形的橡皮擦,早已被造物植入我們的體內,用以擦除所有痛苦和不堪的往昔。肉體經受的劇烈疼痛,在經年之后將會變得隔世一般模糊。但是,此類記憶一旦被輸送入大腦皮層,它就會變成一塊巨大的、吸飽了雨水的海綿,陰郁、沉重,不堪觸碰。當人們經歷戰爭、恐怖襲擊、強奸、重大交通事故等等事件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約七成的人會通過自身調節逐步恢復正常心理狀態;而余下的兩到三成人群,則墜入與此相關的漫長噩夢——醫學上稱之為創傷后應激障礙,簡稱PTSD。在美國“9·11”事件發生后,因之而罹患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病例,至少有萬人之巨。曾經遭遇過的災難畫面一遍遍在腦海中重演,使他們夜夜難以入睡,也無法集中注意力。一點點稍大的聲響,就足以讓他們受到驚嚇,甚至看到摩天大廈也會驚懼不已……記憶造就了一座人生煉獄,將許多人囚禁其間,而刑釋日遙遙無期。
怎樣才能讓大腦刪除苦痛,以補救被無形鬼魅所損毀的人生?
最早剪輯人腦的嘗試,大約發生在古埃及。在一小部分埃及木乃伊中,尸體頭蓋骨上鉆有奇怪的小洞。這種治療癲癇病的古老手術早已失傳,以致后來者不得不查閱大量資料,以了解這些小洞到底所為何來。
到了19 世紀末期,為了治療精神類疾病,醫生們開始嘗試對大腦進行手術。施術對象除了人類,還包括家犬和靈長類動物。1935 年,在倫敦舉行的第二屆神經精神學會上,約翰·富爾頓和卡羅爾·雅克布森發表報告,提到他們對黑猩猩實行兩側前連合切斷術后,黑猩猩的攻擊性行為減少了。在此基礎上,葡萄牙醫生安東尼奧·莫尼茲發明了腦葉白質切除術,用以治療包括精神分裂癥、抑郁癥、嚴重強迫癥以及一些被人們認為有精神疾病征象(如喜怒無常、具有暴力傾向)的人。經過手術,這些患者確實大都變得溫順馴良。莫尼茲因此獲得了1949 年度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腦葉白質切除術曾經風靡一時,從20 世紀30 年代到50 年代,短短二十年間,僅在美國,就實施了四萬到五萬例。但因之而起的質疑也從未止息。50 年代前后的一項調查表明,大約有三分之一做過腦葉白質切除術的病人,術后病情并沒有多少變化;另外的三分之一則比術前有所惡化,變得更為沖動,甚至喪失了部分人性和社會性。也有的病人在經過手術后失去了精神沖動,表現出類似弱智和癡呆的跡象。一些文藝作品也以此為題材,比如電影《飛越瘋人院》,影片的主角、熱愛自由且充滿反叛精神的邁克·墨菲,被強行施行了腦葉白質切除術,就此變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在邁克·墨菲的感召下重新喚醒了生之希望的“酋長”,忍痛殺死邁克,逃出瘋人院。
在日本,曾經發生過一樁轟動一時的“腦白質切除術謀殺事件”。
該事件的主角名叫櫻庭章司,出生于昭和四年(公元1929 年),是一位成績斐然的業余拳手,為人富有正義感。除了擅長運動,櫻庭章司還勤于學業,自學英語并考取了正式的翻譯資格,并立志要當一名作家。
年輕的時候,櫻庭章司曾經做過土木施工員,為了保護被欺辱的同伴,他痛打過小混混,也曾涉嫌以暴力手段抗議老板的不當行為。以上這些都構成了他的“前科”。后來他開始寫作,成了當紅的體育作家。有一次,在贍養母親的問題上,他與妹夫發生爭執,盛怒之下,他搗毀了妹夫用來展示玩具的玻璃櫥柜,因此再次被捕。醫院對他的易怒型性格進行了精神鑒定,隨后以檢查肝臟為名,對他實施了腦白質切除手術。作為出院的條件之一,他被迫在手術同意書上簽了字。
(4)熱量分配:三餐熱量分配一般為1/5,2/5,2/5或1/3,1/3,1/3或四餐1/7,2/7,2/7,2/7。三餐飲食內容要搭配均用,每餐均有糖類、脂肪和蛋白質,且要定時。可按病人生活習慣、病情及配合治療的需要來調整[3]。
術后的櫻庭章司,無緣無故出現了癲癇癥狀。而意欲的減退,使他的書寫能力陡降到了從前的五分之一。有一天,他在窗前眺望落日美景,卻發現自己的內心竟已不再為這世間的美好動情。自此他決意要殺死那位為他手術的醫生,再自殺謝世。某日他服下巴比妥,來到醫生家中,但碰巧醫生外出,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殺死了醫生的妻子和岳母。
櫻庭章司被捕之后,法庭對他進行了醫學鑒定,確認他患有腦萎縮和髓液循環障礙,同時還發現了當年手術時遺留在他腦子里的止血夾。
受到此案啟發,日本著名推理小說作家島田莊司創作了《溺水的人魚》,講述了天才的游泳選手阿蒂娜在脅迫和欺騙之下,被切除了腦葉白質,由此失去了運動能力,不得不在輪椅上度過了痛苦的后半生。促使櫻庭章司下定復仇決心的那個黃昏,也被島田莊司移植到了小說之中:
這是在歐洲大陸可以看到的最后夕陽,眼前是一片金光燦爛的大海,間或也能望見星星點點的漁火……可是,望著這一切,阿蒂娜全無賞景之心,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以前,每當她看到這種夕陽西下的美好光景,總是驚呼贊美,歡呼雀躍。眼前的阿蒂娜簡直成了一個木偶。
以腦葉白質切除術來改變某些人類天性的嘗試宣告失敗之后,醫生們轉而求助于藥物治療和其他更精確的腦外科手術。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人類對自我肉身的探究可謂巨細靡遺。科技的飛速進展也鼓勵了科學家的野心,他們所追求的目標也更為精細,對“記憶操縱”的研究,便是其中之一。
2014 年,荷蘭科學家宣布,他們成功采用電擊療法刪除了人類大腦里的指定記憶。醫生借助電休克機等特殊儀器和設施,在短時間內,以適量的弱電流刺激患者腦部,從而引起腦神經內部發生綜合作用,達到局部治療的目的。
從2016 年開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阿蘭·布魯奈特博士和他的搭檔們,則嘗試使用降壓藥普萘洛爾,為六十名受試者進行每周一次的治療,每次治療時間為十分鐘。在六次治療結束后,有三分之二的患者病情有所改善,雖然不能稱之為完全清除痛苦記憶,但病人此前的睡眠不良、過度警覺、記憶閃回等PTSD典型癥狀,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
在此之前,美國佐治亞醫學院研究小組曾經與中國華東師范大學的科學家共同合作,從小白鼠大腦中成功分離出記憶分子。他們在試驗中將小白鼠放到一個房間里,播放一段錄音,然后反復對小白鼠進行電擊,使之對這個房間和聲音產生痛苦的記憶。然后,他們將小白鼠再一次放到這個房間,并播放讓它感到恐懼的錄音,同時給它注射被稱為CamKII 的蛋白質。此后,當小白鼠被重新放回到同樣的環境中并播放同樣的錄音時,則不再因恐懼而顫抖。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如果我們試圖刪除一段不愉快的記憶,需要在同時回放痛苦的記憶或恐懼的情況下,注射這種CamKII 蛋白質。
當時出于好奇,我查閱了資料,了解到基因編輯的一些皮毛知識。當HIV 病毒攻擊人體時,它主要以CD4+T 細胞為目標,必須在細胞表面找到一個叫作CCR5 或CXCR4 的受體,這個受體相當于HIV 病毒進入人體的“入口”。但是對CXCR4 進行編輯可能影響到胚胎的發育,而且多數HIV 都是通過CCR5 受體進行入侵的,所以CCR5 受體就成為基因編輯的最佳選擇。賀建奎團隊正是敲掉了CCR5 基因的32個堿基,使其蛋白無法正常穿膜表達于細胞膜上,病毒也就無法找到這一“入口”進行入侵。不過,基因編輯存在出錯的可能,并由此引發基因突變,對新生嬰兒產生無法估量的傷害,也有可能產生新的疾病隱患。而且基因一旦被修改就無法恢復,這種隱患會伴隨人的一生,并被遺傳給子孫后代。
后來,坊間傳出賀建奎被捕的消息。南方科技大學也發表公告,解除了與賀建奎的勞動關系,并終止其在校內的一切教學和科研活動。一樁瘋狂的科學事件似乎就此畫上了句號。然而,作為一個懵懂的凡人,我始終沒有弄明白,應用于人體的基因編輯究竟在多大尺度上為法律所允許——如果將基因編輯作用于胎兒屬于非法行為,那么,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刪除特定記憶,其應用對象到底僅限于實驗室動物,還是終將在人類中推廣實施?
在一個文明社會里,出于對個人隱私的維護,我們不可能追蹤這對嬰兒的未來。基因編輯究竟給他們帶來了怎樣的傷害,以及如何確認其對艾滋病終身免疫,這一切都將成為懸念。半世紀前腦葉白質切除術留下的陰影并未散盡,考慮到人類記憶的復雜性質,實在遠非小白鼠可以比擬——以基因編輯技術操控記憶,將為人類帶來福祉還是災難,我們完全無從預知。
有幾次,朋友在網上向我借錢應急。第一個反應當然是擔心遇到了網絡騙子,于是請對方撥打我的電話,然后隨口問了兩個問題。這些問題不會見諸于任何正史和野史,也無法憑借搜索引擎找到答案。它們是在多年的交往中,我與友人共同經歷的細枝末節。如同在忘記某個密碼的時候,系統據以確認操作者系你本人的提示問題:“你最喜歡的老師的名字?”或者,“你小學同桌的名字?”它們是游離于公共記憶之外的私人印記,而只有這樣的印記,才可以證明你是你。這人世的深情,恰是建筑于我們彼此間共同擁有的點滴回憶。罹患阿爾茨海默病的人生之所以讓人哀憐,是因為先于肉體,他們與親人內心的環扣已經提前脫離。我們無法想象那是怎樣一個全然空白的世界,仿佛一切被強光飄過,回首時空茫一片,連腳下的路也接近虛無。
在韓國電影《我腦中的橡皮擦》里,當秀真的記憶力日漸衰退,那個隱形的橡皮擦不斷擦拭掉她腦中的一切印記,深愛著她的哲洙說:如果記憶離開了,還會剩下靈魂。秀真說:不,如果沒有了記憶,那么靈魂也就不存在了。
果真如此,當未來醫學真的可以刪去那部分痛苦的記憶,此后的人類,是否仍可以擁有屬于個人的完整靈魂?或者是,在完整與歡愉之間,我們將如何決定舍此取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