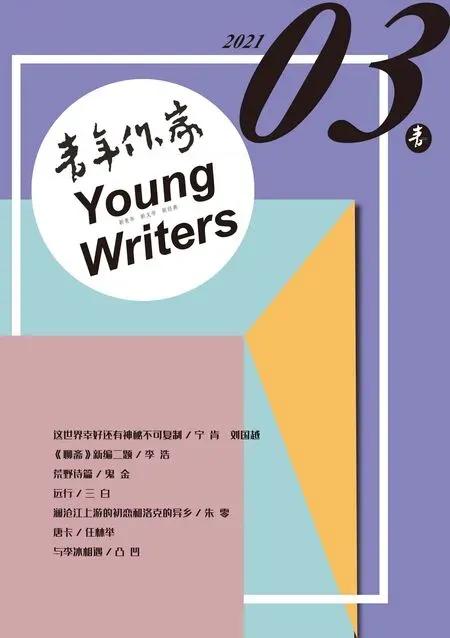與李冰相遇
凸 凹
一
還在一泓羊水里就與李冰相遇了。就是說,我是受著李冰加持的胎教而孕育而出生,及至而初成的。
當(dāng)然,當(dāng)時并不知道這一點。不知道都江堰是與李冰橫筋豎骨連在一起的生命共同體。甚至也不知道那密密麻麻不舍晝夜回響在我身體中的聲氣,是依然在被都江堰或者說依然在被李冰治理的岷江波濤翻卷出的生命顯影。李冰是一位年齡已達(dá)兩千多歲的年輕人——人類至今也沒發(fā)現(xiàn)他有任何一點衰老的跡象。
1962 年3 月10 日,二月初五,晚十點半,母親把我生在了都江堰。當(dāng)時都江堰叫灌縣,隸屬溫江專區(qū),1983 年3 月劃歸成都,1988 年5 月,灌縣撤縣設(shè)市更名都江堰。我出世的具體地點是縣人民醫(yī)院。
母親劉瑞芬,四川內(nèi)江人,父親魏玉階,湖北孝感人。母親說,懷上我的地方是四川萬源縣的茶埡鄉(xiāng)。但十月懷胎在都江堰,降生地在都江堰。還說什么呢,命數(shù)七不拐八不拐,總之是要把我拐到都江堰的懷抱。
對此,我是沒得選擇的。
這樣很好。若允我自選,選不到這么好。
是1965 年深冬離開都江堰的。因父親重慶農(nóng)校畢業(yè)后響應(yīng)號召,主動要求到萬源工作,母親內(nèi)江女中畢業(yè)后經(jīng)廣漢調(diào)到都江堰工作。這就有了困難,母親一人拖倆孩在一邊過活,父親打個甩手在另一邊過單身漢日子。組織上通過父母持之以恒鍥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請,由表及里逐漸知曉這一情況后,認(rèn)為應(yīng)該解決父母已然長達(dá)七年的兩地分居問題,只不過批定解決的前置條件是,母親調(diào)去位于川陜渝鄂交界處、坐落大巴山腹心、屬于老少偏窮地區(qū)的萬源,而不是父親調(diào)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迎面成都平原的灌縣。此與父母的申請初心背道而馳,但卻令你打不出噴嚏,不能不說這也是一種解決吧。
組織的決定鐵板釘釘,不能更易。這樣,母親帶著我和二弟,岔出岷水的方向,沿山脈向遠(yuǎn),落居萬源。
都說小孩要過三歲才有日后可以回望的記憶,這理兒,我信。但我更信,即便過了三歲,也不能記起哪怕是一些重大的憶。譬如我,對幼時都江堰的記憶,就只有少得可憐的三件記得。并且,這三件事是沒有時間次序的,他們是同時的、并置的一樁存在。
都江堰渠首,二王廟山下,著名的安瀾索橋上總有不少人。這座橋在搖晃,像鐘表的針擺動,橋的擺動,除了游人,還風(fēng)的緣故。即便成都平原一個游人也無,這座橋也有。即便全世界一絲風(fēng)也無,這座橋也有——因為永不停歇、生長過大禹、被李冰重塑過的岷江,總在奔騰,總在制造翻卷的、帶漩渦的、干凈的風(fēng)。母親一時大意,只顧風(fēng)景和肚里懷著二弟,忘了長子。當(dāng)她發(fā)現(xiàn)自己的長子離開自己的手,在幾米開外處的橋邊,扶著稀疏得可以掉下一頭牛犢的橋欄,埋著頭,癡迷地望著神秘的岷水,她嚇壞了。那時,我跟橋有等同的擺幅,但母親后來告訴我說,我比橋擺得厲害,如果說橋是篩子,我只是篩子上的一粒糠殼。不敢呼喊,怕自己的嚇壞通過聲音傳遞給我,于是乎,賊一樣,母親偷偷走到我身后,神不知鬼不覺,伸手抱住了我。我抱住了二弟。
這是第一件事。事的是水。
第二件事,事的是火。
那是一個下雪天,母親上班了,保姆不知在干啥,我一個人在火爐邊玩。玩著玩著,把夾炭用的火鉗當(dāng)作玩具,又把火鉗放爐中燒紅,又把燒紅的火鉗杵在自己的比巴掌還小的左腳背上。哧,一股青煙冒出,我好奇地看著,老人一樣麻木,直到灼痛終于翻過堤壩喚醒神經(jīng),驚天動地洪水滔滔的哭聲,才裹挾著廚間乃至刑訊室烙肉才有的焦煳味,突然炸響。直到今天,左腳背上,都有一塊五分硬幣大小的疤痕。疤痕不算大,我長它也長,我不長它也不長,但迄今,身上所有的疤痕加起來,都沒有這么大。手指撫它,滑滑的,沒有底紋,沒有毛孔,更沒有汗毛。平時一點不疼,但一看見它、想起它,就有一種隱痛,那種藏在骨子里的女人分娩一般的孤涼的痛、溫暖的痛。
都道水火不相容,上述記憶中,可以看出,我的身體內(nèi),二者是相容的。
第三件事,是對灌縣縣城的記憶。能記起的場景不多。記得我們家在老街上,出門就是窄窄的街巷,附近有間外國人的教堂,不遠(yuǎn)處是橫跨岷水的南橋。家、街巷、橋,是黑色的,只有教堂白得有些詭異,合在一起,又有黑白照片的協(xié)調(diào)。它們牢牢建筑在李冰的岷水上,又緊緊扎根在李冰的大地里。
葆有這仨記憶,還得感謝組織上對父母申請的延宕性處理,否則,若三歲前離開灌縣,我人生的源頭性記憶,就是滿世界的野山,而非李冰的家水了。二弟離開灌縣時一歲半,對自己的出生地,記憶一片空白。沒有記憶的存在,就是不存在,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有點殘忍。
對于幼時的灌縣記憶,我用散文《人之初:都江堰的烙印》進(jìn)行了筑堰壘堤式鎖定。文章特別提到:“吾國古代有‘三祭’,名:水祭、土祭、火祭。有‘三過’,曰:過水、過土、過火。”
線頭對針眼,棒杵對碓窩。這似乎是說,對都江堰,我短短的幾十年記憶,有著二千多年的古老、稚嫩和秘密。
二
得到通知,說四川十大歷史名人小說創(chuàng)作出版座談會本月26日在閬中古城舉行。通知我,是因為我與李冰有關(guān)。這是2017年12月的事。
不敢說全世界的人個個都知曉一項叫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一位叫李冰的古人。但稍稍有點識見的,乃至大多數(shù)中國人,是一定知曉的。知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堰首部分修在一個叫都江堰的地方。甚至也知道,這個工程不僅馴服了岷江的水災(zāi),還把水災(zāi)轉(zhuǎn)化成了二千多年來一刻不歇灌溉成都平原的渠水。李冰就是這個古老的浩大工程的主持人、總指揮。
但大多數(shù)人,對李冰及其功績的信息知曉量,恐怕僅此而已。
李冰長什么樣、性格、愛好、經(jīng)歷、哪里人、生死何處、父母是誰、夫人叫啥、膝下幾多子女、朋友圈情態(tài)、官場環(huán)境……這些問題,不僅我們茫然,連二千二百多年來的古籍遺跡也莫名所以,一字不留。
戰(zhàn)國末期,公元前277 年,秦昭襄王一紙任命,李冰走馬上任成為蜀郡新一任郡守(之前大多專家認(rèn)定為第三任,因前不久公布在陜西西咸又挖出“蜀守斯離”四字,現(xiàn)似為第四任)。作為地方主官,他與兒子二郎,在人影憧憧的蜀地治水工地上忙活,搞出了流芳百世的大動靜。除了理順蜀郡地盤上的岷江流域,還理順了沱江等流域——沱江的近一半水量引自都江堰。那時的水就像一團亂麻,理順了水,就理順了土地、豐收和人民的心思,導(dǎo)致經(jīng)濟、政治、文化、軍事、社會、生態(tài)等方方面面的美好與強大。
李冰的老板秦昭王要的就是這個強大,要的就是讓李冰治蜀治出這個強大。這個強大也讓生長它的土地獲得了巨大光榮,因此這片土地上,后來的人民就修祠建寺,把李冰供為神,尊為川主。
大搞治洪、灌溉、航行等水利工程,使李冰成為大國工匠。但他畢竟還是秦王治下的能臣干吏,所以,除了水利工程,李冰還做了其他一些事。
要得富,先修路。對于難于上青天的蜀道,李冰不滿足只浚通出川的水路,他還重修、疏通和新筑了一些出川的陸路,譬如,向北的金牛道達(dá)陜西,向南的西夷道去印度。正是這些主要用于戰(zhàn)爭的道路,順帶盤活了蜀地的商貿(mào),使成都成為南方絲綢之路的起始點。
蜀地的李冰時代,蜀人對牛的吆喝、使用,還局限在放牧、擠奶、吃肉、馱物和戰(zhàn)爭上。正是對中原耕田技術(shù)了然于心的李冰的返蜀,讓他們知道了牛還可以用它的蠻力為主人犁地。
很長一個時期,鹽鐵是國家的專控物資。
蜀地的李冰時代,對于門前就有河水流過的蜀人來說,打井還是個毫無意思的高尖技術(shù)活兒。正是隨李冰而來的中原打井技法,使廣都鹽井成為我國第一口鹽井。也使遍地的從地下鹵水中提純的川鹽,不僅可以自給自足,還可出口變現(xiàn)。
蜀地的李冰時代,地下有鐵礦,但卻沒有變礦為鐵的優(yōu)良技術(shù)。工具和武器所用之鐵,大多從鄰國進(jìn)口。正是秦移民的冶鐵手段,使臨邛地區(qū)成為秦國最重要的冶鐵業(yè)中心。
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雖然只是吉光片羽,雖然好些尚無定論。要知道,最先記錄“冰”的《史記》,只有60 個字:“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shù)也。”60個字中,有關(guān)他生平的,提煉出來,只5 字:蜀守冰,治水。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歷史留給我們的想象空間是,作為守土有責(zé)的地方主官,在位多年建大堰不可撼動,足以說明李冰在政治軍事、行政管理、制規(guī)執(zhí)法、維穩(wěn)安民、民族團結(jié)、文教衛(wèi)等諸方面的作為,也可圈可點。
好了,是時候了。“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在秦國統(tǒng)一全國征程中,來自蜀地的糧食、戰(zhàn)船和鐵,“浮江而下”,源源不斷支撐著秦軍攻城略地的骶骨。公元前223年,秦得楚,二年后并天下,中華自此成一統(tǒng)。
“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華陽國志》)這就是四川盆地底部、成都平原號為天府之國的硬理吧。那么,由此上溯,我們會發(fā)現(xiàn),李冰正是天府文化的源頭。
天府不僅為秦滅六國統(tǒng)一中國出了大力,建了奇功,兩千多年來,各個歷史時期,每當(dāng)國家危難,天府都在努力為國家造血、輸血。比如接納一茬又一茬來川的移民,劉邦時期、蜀漢時期、湖廣填川時期,莫不如此。比如抗戰(zhàn)期間出人槍、出財物,比如三年困難時期出救命糧。
這就是李冰及李冰的價值與意義。
突然發(fā)現(xiàn),李冰當(dāng)為詩人,不然,何以有如此夸張如此驚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李冰走了二兩多年了,尸骨不存,但他的作品至今都鋪開著,有力地流動,無聲地灌溉我們。
大禹、李冰、落下閎、揚雄、諸葛亮、武則天、李白、杜甫、蘇軾、楊慎,這是四川首批十大歷史名人,也是中國赫赫有名的人物。得到閬中會議通知前的上月中旬一天晚上,接到文友作平電話,告知有個選題,要求把十大名人用十本小說來表現(xiàn),作家在全國范圍薦選,一個作家對應(yīng)一位名人。在我強烈要求下,很慶幸,我最終對應(yīng)的是李冰——之前有過寫落下閎的念頭,但一覺醒來就放棄了。這是冬日里的一個消息。這個消息,讓慵懶了幾十個春秋的我,一下生發(fā)了洶涌的熱切。遂開始進(jìn)一步購買、閱讀史料,再次踏勘李冰治水蹤跡。
大約生于都江堰的原因吧,總感到血液和骨髓中敲打著岷江的響器。隨之而來的,是以岷江水系為基底、沱江水系為輔撐的成都平原自然和文化氣息洇染出來的天府文化,對我身心的設(shè)定。就是說,我的創(chuàng)作靈感與密碼,是都江堰給的,這也就給定了我的作品以方向。
怎么返家,李冰都在前邊,都在方向里。
但愿熱切與方向,能支持我開筆、寫好,直到殺青。畢竟,這是我第一次接手寫古代歷史小說的活兒,能否干好,多少有些忐忑。
但不管忐忑與否,書,終是成型了,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稿費也不低。謝謝!都是李冰給的,給液體的水,還給固體的資費。
三
少年時的記憶很好,不然不可以將《水滸》人物和故事倒背如流。后來不行了,猴子掰苞谷,一邊掰一邊丟。讀了很多書,讀過就忘,入了先甜后苦的道。
遷離都江堰后,記得1987 年底,冷得穿羽絨服的季節(jié),返回都江堰,但真不能確知這是不是離開出生地后的首返。如果是,第一次分離便長達(dá)22 年。
此次返鄉(xiāng),實際上是藏了私心,揩了公家的油。
當(dāng)時在一個密級頗高的“三線”軍工基地的一家下屬工廠混飯,工廠在崇山峻嶺中,距都江堰約八九百公里。獲知《星星》在辦“中國星星杯青年詩歌大賽”,中文系出身、時任廠團委書記的劉健同學(xué),便拉上業(yè)余寫詩、兼任廠團委文娛委員的我,出差成都,找葉延濱商談協(xié)辦事。
還真是協(xié)辦事,因為我將偷偷溜去看都江堰、登青城山變成了主辦事。久違了李冰先生!李冰當(dāng)然在,李冰一直在,不管這個世界在與不在。我的激動從岷山峽口噴涌而出,無以復(fù)加。
中篇小說《顏色》復(fù)盤了這一過程。
兩年后,春水泛起之際,又一次見到李冰。
這次是應(yīng)邀參加星星詩刊在都江堰舉辦的一個筆會。孫靜軒、楊遠(yuǎn)宏、石光華、程寶林、森子等詩壇先鋒人物,就是這次認(rèn)識的。幾十年來,我見證過無數(shù)次一眾詩人,集體與李冰的大河劈面相遇,久久感喟。但這次,是開先河的一次。
四
1992 年,大概夏秋季節(jié),終于回到遷離27 年之久的成都平原。只不過,是從成都之西離開的,返回的地方,卻是成都之東龍泉驛。難不成,一江春水向東流,也旨在說明我的人生命數(shù)歸向?而今,已客居龍泉驛28 年了。前年,我攛掇忽悠兒子去都江堰買了一幢100 多平方米的小別墅,難道是我私心作祟,妄圖得寸進(jìn)尺逆水而上落葉歸根?
調(diào)到龍泉驛工作后,去過多少次都江堰,真?zhèn)€是不計其數(shù)。先是沿老成灌公路去,后是沿成灌高速去。這不計其數(shù)的去,讓我的足跡幾乎寫滿都江堰山山水水旮旯角落,讓我自覺不自覺地為這片神奇土地留下了包括《大河》《出生地》等在內(nèi)的200 余首詩。人生多變,但千變?nèi)f變,我這一輩子,別的說不準(zhǔn),可以肯定的是,再不會為一個區(qū)縣級治地乃至地市級治地,寫多得如此恐怖的詩了。
更大密度去都江堰,是因為結(jié)識了年輕詩友王國平。記得1999 年夏天,我從詩刊社第15 屆青春詩會山東聊城現(xiàn)場回蓉,在寬窄巷子成都市文聯(lián)會議室,參加他的詩歌研討會,得以面晤。沒過幾年,又仿佛一夜之間,國平就從都機廠一名搬運工,蝶變成了都江堰文化界標(biāo)桿和權(quán)威發(fā)言人,文化活動策劃者和操盤手。因為都江堰地緣、李冰人緣這層關(guān)系,我倆結(jié)下了很好的友誼。我的好朋友中,不喝酒的堪稱稀罕,國平是其中之一。
在國平兄弟的誠邀下,我成了都江堰各種文化活動的常客。他把我和都江堰更緊密地綁在一起。對此,只說兩件事:一鎮(zhèn)事,一書事。
都江堰的青城山腳下有個鎮(zhèn),叫柳街。自2016年始,一年一屆的不可謂不盛大的中國(都江堰)田園詩歌節(jié)皆在柳街舉行。這個活動,本人幾乎都有參加,成為每年六月間的必修課。更有意思的是,還被柳街聘為了駐鎮(zhèn)詩人。
書事,發(fā)生在2009 年,秋天。國平策劃、中華文學(xué)基金會資助項目,一套十本“重建精神家園·都江堰作家書系”,獲公開出版發(fā)行。很榮幸,國平找到我,將批評札記集《字簍里的詞屑》納入其中,讓我這個祖籍不在、人也不在都江堰的都江堰人,獲得了無比權(quán)威的身份確認(rèn)。有了這個確認(rèn),跟著,都江堰地方志也收容了我。
再說一下他。《湯湯水命》面世后,讀者報和錦江區(qū)文化館的“錦江大講堂”,決定在布克書店搞一場名為“虛構(gòu)向真實的步步緊逼”分享會。我覺得需要一個人扎場子,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國平,他不僅是詩人、作家,還是四川省李冰研究會副會長。他當(dāng)然知道我是剮他這個副會長身份的油,但他不怕剮。打的,坐快鐵地鐵,再打的,穿過大半個成都準(zhǔn)點趕到了布克,誰讓我們是好兄弟呢。
不能不提到都江堰另一位年輕詩友文佳君。與國平相反,行過武的佳君特好酒。他的臉有姑娘家的白嫩,但幾兩酒一去,就紅得比都江堰著名的紅砂巖都紅都硬了。記得2005年夏天,他整合大觀鎮(zhèn)資源,策劃組織了一場川西壩子數(shù)十人參加的詩會。青城山中,味江邊,詩人們圍著篝火大碗喝酒的張狂,總讓人聯(lián)想到當(dāng)年茶農(nóng)王小波、李順在這里揭竿而起的山匪樣的霸道與豪邁。
佳君是位熱情的地主,前年初春,得知我要實地勘查李冰當(dāng)年筑渠首利用白沙河對出山岷江攔腰沖襲的情狀,就陪我去了。
都江堰還有很多朋友,男男女女,這里篇幅羞澀,只有酒上見了。
五
在蜀地生活,有事無事往都江堰走走;在蜀地寫文章,寫這寫那都寫寫李太守,已成習(xí)慣。
去了一趟都江堰的向峨鎮(zhèn),見到此地的水在這一坡流向岷江,另一坡流向沱江。而水爬上樹的樣子,是滿丘滿壑的讓果農(nóng)歡喜不盡的獼猴桃,于是寫了《獼猴桃的中庸江湖》。我想,寫水的目的地,是李冰高興的事。
不僅在都江堰境內(nèi)寫李冰,在都江堰境外也寫。都江堰灌區(qū)早已突破成都平原的范疇。
常被邀到這里那里采風(fēng),東道主接待又好,潤筆費不薄還預(yù)先支付,這就不好意思厚著臉皮不為當(dāng)?shù)赝瓿梢黄院炍兜淖鳂I(yè)了。邀去的作家往往創(chuàng)意非凡,悄悄咪咪秘而不宣各選一個方向進(jìn)行創(chuàng)作。而我,但凡在蜀地,絕不大費周章,基本上是讓筆尖朝著水的方向、李冰的方向。
寫賀麟故鄉(xiāng)金堂,沿著沱江兩岸找尋鱉靈鑿山開谷的銅錘和李冰的探水鐵杖,找到了寫出《一條河流的哲學(xué)算式》的感覺。寫崇州鄉(xiāng)村麗景,從李冰的羊摩河走到榿木河,終是走出了《逐水而居的榿木》。寫艾蕪故里清流鎮(zhèn),充滿我雙目的,只有引自都江堰的毗河,引自毗河又穿鎮(zhèn)而過的青白江,這樣被水完全遮蔽的眼界,除了以《一脈清流穿古今》交作業(yè),還有別的選擇嗎?寫簡陽變遷雄力,冒著盛夏太陽炙烤,順東風(fēng)渠干渠勘探,上山下山,揭秘龍泉山引水隧洞,用《上山的水》大贊了簡陽人民當(dāng)年的驚人干勁和李冰對簡陽的綿綿澆灌。
了解李冰,僅僅將都江堰渠首工程研究透,將都江堰灌區(qū)丈量完,甚至將岷江、沱江走通順,都是不夠的。我還去了兩匹山,章山和陽平山。
資料顯示,李冰晚年在治洛水、綿水時,累死在洛水邊。李冰陵矗立洛水邊的章山,而章山位于什邡市洛水鎮(zhèn)。到洛水鎮(zhèn)后,首先叩訪了位于街場中心的川主廟。
出洛水鎮(zhèn),不到兩公里,過李公湖,右拐一條鄉(xiāng)道,目的地到了。入李冰陵大門,抬頭,依山平臺上,矗立著一尊高大雄偉的李冰雕塑。踩著雕塑旁側(cè)陡且長的石階上山。山頂,見到了李冰陵,還有好些呈現(xiàn)李冰治水立下水功的壁畫。
按照著名歷史學(xué)家任乃強先生之李冰生長于蜀地陽平山地區(qū)的觀點,我驅(qū)車到了彭州陽平觀。陽平觀立于山頂,蜀地本土古樹虬髯密布,竹林嘩啦啦鋪開,湔江、海窩子一覽無余。
此行有彭州詩人舟歌導(dǎo)陪,方便了許多,他不光給我介紹了李冰與彭州有關(guān)的信息,還向我引薦了對陽平山地區(qū)歷史文化頗有研究與心得的魏新阜。在他開在海窩子古鎮(zhèn)的農(nóng)資鋪子里,他如湔江一般滔滔不絕地講述,道出了此處地脈堪與對李冰天人合一思想的肇啟與濫觴。他認(rèn)為古蜀國的文明中心,就在陽平山地區(qū),還特別指出此地的一些古蜀樹種,何以延續(xù)到今天。舟歌在一旁笑答,都江堰怎么延續(xù)到今天,古樹就怎么延續(xù)到今天。詩人的蹈空思維,雖說不算科學(xué),但從對萬物的推演看,似也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