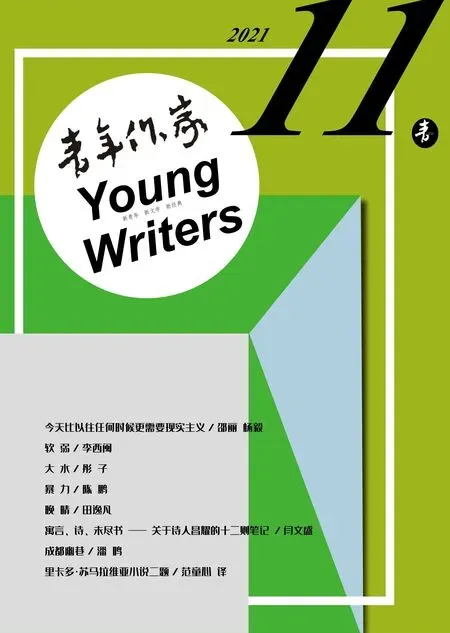評(píng)論者說(shuō) “零零后”田逸凡筆下的家庭生活
安 寧
確切地說(shuō),19歲的田逸凡并不是我的學(xué)生。雖然我所在的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也為文史哲基地班開(kāi)設(shè)寫(xiě)作課,但我恰好被安排到別的專(zhuān)業(yè)開(kāi)課。熱愛(ài)寫(xiě)作的田逸凡“慕名而來(lái)”,成為旁聽(tīng)生,而且是我教書(shū)十年來(lái),一年中旁聽(tīng)了我三門(mén)課的唯一一個(gè)學(xué)生。
我們是在2020年10月渡瀾的小說(shuō)研討會(huì)上相識(shí)的。那時(shí)田逸凡剛剛考入內(nèi)蒙古大學(xué)一個(gè)月,卻已對(duì)學(xué)校的風(fēng)云人物、在國(guó)內(nèi)文學(xué)圈嶄露頭角的大三學(xué)姐渡瀾了如指掌,在給學(xué)校新聞網(wǎng)所寫(xiě)的報(bào)道中,他還非常細(xì)心地為渡瀾做了一個(gè)刊發(fā)作品列表。我們熟識(shí)之后,他又告訴我,高三那年,他讀到渡瀾刊發(fā)在《收獲》上的短篇小說(shuō)《傻子烏尼戈消失了》,遠(yuǎn)在山東濰坊的他,就發(fā)誓要報(bào)考內(nèi)蒙古大學(xué)。當(dāng)然,來(lái)聽(tīng)我這“伯樂(lè)”的課,也在他的理想計(jì)劃之內(nèi)。
與沉默寡言、獨(dú)來(lái)獨(dú)往的師姐渡瀾,和能言善辯、熱愛(ài)社交的師兄蘇熱不同的是,田逸凡性格沉穩(wěn)內(nèi)斂,有著山東人普遍的穩(wěn)健中積極開(kāi)拓的個(gè)性。不管是在我給本科生開(kāi)設(shè)的寫(xiě)作課上,還是給研究生開(kāi)設(shè)的影視課、戲劇課上,但凡我提問(wèn)到田逸凡,他給出的答案,總是特別誠(chéng)懇、理性、客觀,不像與他同齡的年輕人,會(huì)因年輕氣盛而自負(fù)偏激。或許,他在《泥沼》和《晚晴》兩個(gè)短篇小說(shuō)中,傳遞出的人類(lèi)應(yīng)該在瑣碎、庸常、充滿(mǎn)泥沼的家庭生活中,努力尋求被時(shí)間磨損掉的愛(ài)與生命的意義,與他的個(gè)性有著隱秘的關(guān)聯(lián)。父母在,不遠(yuǎn)游,游必有方。孔子對(duì)于家庭生活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山東人的性格、家庭婚姻生活和職業(yè)選擇。如我這類(lèi)千里迢迢離開(kāi)故鄉(xiāng)、定居塞外邊疆的山東人,必然與父母的傳統(tǒng)觀念存在分歧,并背負(fù)著父母親朋眼中“不孝”的罪名,繼續(xù)我行我素地游蕩下去,甚至因?yàn)檫@樣的沖撞,時(shí)不時(shí)有徹底斷根、自由飛翔的偏執(zhí)。
但我在最初并未意識(shí)到田逸凡對(duì)于家庭婚姻主題的獨(dú)特關(guān)注,我想可能連他自己也沒(méi)有思考過(guò)這個(gè)問(wèn)題。我只是引導(dǎo)他多與渡瀾和蘇熱接觸,向他們討教一下寫(xiě)作的秘訣,尤其是如何建立一個(gè)適合自己的寫(xiě)作王國(guó),就像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和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鎮(zhèn)那樣。無(wú)疑,相比起生于2002年的田逸凡,1999年的渡瀾和1997年的蘇熱起步較早,在寫(xiě)作上也更為成熟。渡瀾的小說(shuō)游走于魔幻與童話(huà)之間,蘇熱則專(zhuān)注于以故鄉(xiāng)巴彥淖爾為原型的“黃鎮(zhèn)”系列。更為年輕的零零后田逸凡,則依然在不同主題之間試探猶疑。他最初提交給我的兩個(gè)短篇小說(shuō),一篇是高考后完成的《潮汐樹(shù)》,有青春文學(xué)特有的哀愁;一篇是完成于高二的處女作《求你們告訴我》(《草原》2021.1),主題聚焦于法律案件中的人性問(wèn)題。我因此鼓勵(lì)他去選修第二學(xué)位法學(xué),因?yàn)槲闯赡耆税讣絹?lái)越引起社會(huì)關(guān)注,他可以嘗試像臺(tái)灣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關(guān)注校園案件和未成年人心理問(wèn)題,同時(shí)將校園與家庭、社會(huì)連接,擴(kuò)大這一主題的內(nèi)涵。對(duì)于我的建議,田逸凡雖然答應(yīng)下來(lái),明顯還持有疑慮。但我并不擔(dān)心,就像渡瀾和蘇熱找到適合自己的寫(xiě)作方向也經(jīng)歷了一個(gè)過(guò)程;即便已經(jīng)找到,像蘇熱這樣,還會(huì)時(shí)不時(shí)因?yàn)槭艿骄庉嬘绊懚纳Щ蟆N抑回?fù)責(zé)指引,道路歸根結(jié)底要由他們自己選擇,我相信他們也終會(huì)尋到適合自己的方向。這是我在指導(dǎo)學(xué)生寫(xiě)作時(shí)一貫秉承的原則。
不過(guò)經(jīng)過(guò)我的牽線(xiàn)搭橋,田逸凡還是非常積極地開(kāi)始向渡瀾和蘇熱取經(jīng)。他曾請(qǐng)渡瀾去食堂吃飯,只是渡瀾問(wèn)一句“嗯”一句的寡淡交流方式,讓我很懷疑他們之間會(huì)碰撞出熱烈的火花。健談的蘇熱,倒肯定會(huì)喋喋不休地將自己的寫(xiě)作經(jīng)驗(yàn)傾囊相授;就像蘇熱領(lǐng)了稿費(fèi),請(qǐng)我們吃火鍋的時(shí)候,也算才思敏捷的我,常常在他漫長(zhǎng)無(wú)邊的講述中插不上嘴。火鍋熱氣騰騰,氤氳著四個(gè)人的臉,一旁的渡瀾,因?yàn)橐幌虻某聊瓌t,反而看上去有種氣定神閑的優(yōu)雅和自信。倒是對(duì)面的田逸凡,做足了大一小迷弟的謙卑姿態(tài),認(rèn)真傾聽(tīng),并時(shí)不時(shí)地附和著我和蘇熱點(diǎn)一下頭。
是的,田逸凡是謙卑的,謙卑到我在相識(shí)一年后才通過(guò)別人知道他還寫(xiě)詩(shī),而且詩(shī)歌與小說(shuō)寫(xiě)得一樣優(yōu)秀。這種謙卑跟渡瀾為掩蓋內(nèi)心對(duì)于人群的恐慌,而與整個(gè)世界都保持距離的姿態(tài)不同,也與蘇熱恨不能將所有文體都嘗試一遍的熱烈姿態(tài)不同,田逸凡有著山東人特有的柔順圓潤(rùn)的處世品格。這種端正敦厚的品質(zhì),在他的小說(shuō)中,也體現(xiàn)在他對(duì)家庭和婚姻生活矛盾的處理中,幾乎無(wú)一例外地選擇“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般的寬容與接納,并用這短暫的詩(shī)意,撫慰瑣碎人生的煩惱與憂(yōu)愁。
相比起田逸凡對(duì)人生困境的處理方式,我更好奇他為何會(huì)鐘情于家庭婚姻主題,這似乎不是他這個(gè)年齡的人關(guān)心的問(wèn)題。年輕的寫(xiě)作者會(huì)像渡瀾和蘇熱那樣,聚焦于魔幻、童話(huà)、科幻等等。至于家庭生活,我覺(jué)得或許人到中年,被雞零狗碎的現(xiàn)實(shí)擊打過(guò)后,才會(huì)生出書(shū)寫(xiě)它們的興趣。小說(shuō)《泥沼》中,中年女子朱葉因丈夫與兒子爭(zhēng)吵,一氣之下沖出家門(mén),去書(shū)店排隊(duì)“追星”,試圖用年輕時(shí)代殘存的對(duì)音樂(lè)的癡迷,平息現(xiàn)實(shí)的波瀾。小說(shuō)《晚晴》中,中學(xué)男老師與女強(qiáng)人妻子事業(yè)不合,婚姻冷淡,是兒子的一場(chǎng)意外事故,讓兩人最終達(dá)成與生活的和解。在《食鮮記》(《山東文學(xué)》)、《乃玉的暗色灘地》(《特區(qū)文學(xué)》)兩篇小說(shuō)中,關(guān)注的則是身患?xì)埣驳募彝コ蓡T,和一天天邁向死亡的老者。田逸凡對(duì)于偏好家庭這一主題給出的解釋是:“我猜測(cè)可能和我父母的工作有關(guān),他們都是老師,也自己創(chuàng)辦過(guò)學(xué)校,從小接觸到許多學(xué)生和家長(zhǎng)的故事。也或許和我母親的家族有關(guān),家族很大,成員之間又都親密團(tuán)結(jié),算是比較少見(jiàn)的聯(lián)系如此緊密的大家族,誰(shuí)家發(fā)生了事情,總是比較容易引起我的關(guān)注。長(zhǎng)久以來(lái),我也就習(xí)慣有意識(shí)地去思考家庭問(wèn)題。”
這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時(shí)光,也時(shí)常會(huì)被這種大的家族影響。只是我所經(jīng)歷的挑撥離間多于“親密團(tuán)結(jié)”,以至于我成為一個(gè)典型的悲觀主義者,并用了很長(zhǎng)的時(shí)間才祛除這種影響,讓自己的文字折射出寬容悲憫的色澤。在零零后田逸凡這一代人身上,良好的家庭教育讓他開(kāi)始思考家庭中更為深刻的問(wèn)題,比如《泥沼》中始于愛(ài)情的朱葉(朱麗葉)與羅歐(羅密歐),他們結(jié)婚后,生出的錦上添花般的兒子羅添,究竟真的給婚姻添了光彩,還是磨損著他們最初的浪漫愛(ài)情?為何一個(gè)曾經(jīng)有著理想追求的知識(shí)女性,在成為妻子和母親之后,慢慢丟掉了自我?這種詩(shī)意的短暫逃離,究竟能否真正恢復(fù)破損的家庭關(guān)系?
在對(duì)《晚晴》構(gòu)思的闡釋中,田逸凡說(shuō):“我試圖寫(xiě)出一種溫情,一種能給掙扎中的人們以撫慰的溫情。在人類(lèi)社會(huì)的家庭里,任何一位家庭成員的事業(yè),似乎都要取得其他家庭成員的基本認(rèn)可。自我實(shí)現(xiàn)渴望自由,家庭前進(jìn)要求整齊,社會(huì)群體統(tǒng)一理想,每個(gè)人都在為這歷史的調(diào)和做出犧牲和妥協(xié),而這一切并不容易。”在田逸凡的眼中,“家人之間的和解無(wú)須一紙協(xié)議,只需一個(gè)美麗的晚晴。人生的情節(jié)十分緊湊,人類(lèi)卻沒(méi)有忠實(shí)的觀眾。我們大概只能在某些人生的閑筆中為自己做觀眾。”他十分喜歡李商隱的詩(shī)歌,在某種意義上,他在向詩(shī)人的《晚晴》致敬,而動(dòng)筆的終極執(zhí)念,就是那句“人間重晚晴”。
或許,錯(cuò)綜復(fù)雜的大家族,成為田逸凡觀察家庭這一社會(huì)最小細(xì)胞的窗口和寫(xiě)作的不息源泉。只是他自己尚不清楚,這樣敏銳的觀察究竟從何時(shí)開(kāi)始。或許,當(dāng)他還是一個(gè)孩子的時(shí)候,他從自己同樣熱愛(ài)音樂(lè)卻在結(jié)婚生子后很少唱歌的母親那里,從熱愛(ài)體育卻最終當(dāng)了數(shù)學(xué)老師的父親那里,就已經(jīng)開(kāi)始了對(duì)于人應(yīng)該如何在家庭關(guān)系中協(xié)調(diào)個(gè)體自由的觀察。這是羅密歐與朱麗葉結(jié)婚之后的現(xiàn)實(shí)生活,是更為真實(shí)地落入吃喝拉撒層面的生命運(yùn)轉(zhuǎn)。他的小說(shuō)看似聚焦于世俗家庭圖景,卻試圖給予百折不撓活著的人類(lèi)一點(diǎn)星星一樣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