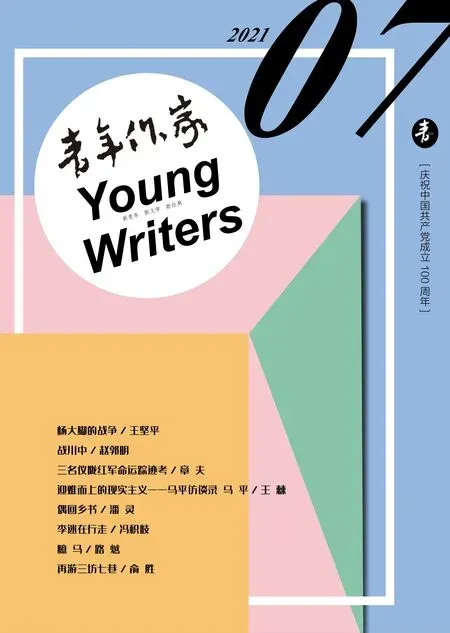臆馬
路 魆
大早起來,我就在擦拭花瓶,擦得锃亮。即使亮得像鏡子,我依然看不到自己的模樣。馬可也醒了。醒來第一句話,他就說,他想得到老虎身上的外套。我看著馬可在沙發(fā)上惺忪的樣子,打賭他肯定忘了自己剛在睡覺,于是說:“你在做夢,老虎身上的外套,不就是虎皮嗎?買賣虎皮是違法的。”
“波羅,你不記得了嗎?那只老虎穿了件外套,褐綠色的棉襖。”馬可說。
是昨日的馬戲團。那里有頭老虎因為怕冷穿了件棉襖,但馬戲團已經(jīng)離開。于是我告訴他,往日不可諫。馬可張著嘴,恍然大悟,但還是說:“我們還有彌補的機會。今天是周末,舊貨市場開了。”
“哎,這次你又想淘什么寶貝呢?”我很無奈,看看手里的花瓶,它也是我上次陪馬可逛舊貨市場時無意買回來的。舊貨市場的店主嘴巴很厲害,最會忽悠人去花那些不必要的錢,買些不必要的雜貨。唯獨馬可鐘愛舊貨市場,他生下來就是為了光顧那些店主,好讓他們賺錢似的。
馬可從沙發(fā)上滑下來,打開窗戶,看著霧氣蒙蒙的遠方。那是舊貨市場的方向。我看著他被迷霧削去形體的背影,等著他回答。略加思考,馬可回頭答道:“在舊貨市場里,有一匹一層樓高的銅馬,是拍攝《特洛伊》時制作的簡易模型,不過是銅質(zhì)的,被倒賣到了中國。嗯,我要得到它。”在他的眼神里,我又看到了偏執(zhí)狂般的渴望,太陽尚未升起,他那雙瞳里的光澤就足夠替代太陽。
老虎身上的外套,特洛伊電影的銅馬……
馬可總是想得到那些二手物品,生活不分主次,喜歡收集各種各樣的雜物,比如紀念品、舊家具、破花盆,或者一根被丟棄的鉛筆。要是他所淘到的恰好是自己那堆被妻子清理掉的雜物,那么就可以幫助他重拾丟失的記憶。要不是我適時制止,這個家早就成了流浪漢居所、垃圾堆填區(qū)、歷史陳列館……
馬可并沒有科利爾兄弟綜合征,也就是俗稱的收藏癖。至于更深層次的原因,用列維-布留爾的“存在即是互滲”概念來分析,他覺得自己不僅僅由這個身體構(gòu)成,所有構(gòu)成他記憶和生活歷史的物品,主要是指他房間里的那些書,盆栽、煙灰缸,甚至床單被褥,都是他的一部分。他把自己的人格或者肉體分配給那些物質(zhì),意味著妻子丟掉他的物品,就是把他從家里抹除。不過,這是列維-布留爾當初研究原始思維時使用的簡單概念。馬可他可是個現(xiàn)代人,總不會跟原始人一樣,認為用長矛插入動物的腳印,就能刺傷動物的腳吧?巫毒娃娃這種東西也體現(xiàn)了同樣的思維,施害者要相信巫毒娃娃跟受害者是等同的事物,才能在巫毒娃娃身上扎針,實現(xiàn)遠距離的精準打擊。
馬可的妻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有天趁他出門上班,把他房間里的東西全部扔掉賣掉。顯然他妻子跟使用巫毒娃娃的人一樣,知道只要對那些物品下毒手,就能施加迫害。果然,馬可回家后看見空蕩蕩的房間,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也認不出眼前的妻子,像個陌生人似的說走錯了家門……我覺得馬可在撒謊,他要是真的什么都忘了,我也不會從他嘴里聽到那么多細節(jié)。他只不過是為了維護作為男人的尊嚴,不愿意承認被掃地出門而已。我也不好意思問他夫妻倆存在什么矛盾,搞到要冷戰(zhàn)分居。可是照目前的狀況看,馬可好像是來真的……他非常執(zhí)著要找回被妻子處理掉的東西,否則那種被肢解的感覺將永遠無法消除。他在舊貨市場淘的貨,并不限于他丟失的那幾類,而是慢慢地轉(zhuǎn)變?yōu)橹灰莿e人用過的東西,他都特別感興趣。他說在二手物品里,殘留有人的氣味。
我不帶惡意地譏諷他:“你是一個二手的人。”
馬可有點生氣:“在鏡子里看不到自己樣子的人,連二手都不是!”
我一時語塞,不再辯駁。這是事實,我是無相之人,有段時間很害怕照鏡子。
我的故事跟馬可的有相似之處,但過程更為緩慢,像是沖蝕平原的產(chǎn)生一樣耗費了漫長的時間,一點一點地塑形,繼而形成新的生命地理,最終遺忘最初的模樣。
多年前我父母親結(jié)婚時,嫁妝里有一面巨大的古銅鏡,是我外祖父傳下來的藏品。外祖父特別珍視這件藏品,當母親出嫁時,要她把這份嫁妝帶進新組織的家庭里去。家里后來還遭了幾次盜竊,賊人都是奔著古銅鏡來的。我父親是學校里的歷史老師,第一眼看到古銅鏡就知道那不過是一件仿古的贗品,仿的是唐代海獸葡萄紋銅鏡,即使在這方面毫無研究,一般人只要看看那面銅鏡的尺寸,足足有半個人高,很難不對它的真實性存疑。父親至今沒有戳破這個事實,因為從擁有銅鏡的第一天開始,母親就歡天喜地地將銅鏡擺在臥室的窗邊,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完全沒有理會這面銅鏡跟其他銅鏡一樣,鏡面磨得并不清晰,只能依稀辨認出臉的輪廓,只有在太陽底下才勉強提高可見度。
母親不是個漂亮的女人,都說模糊的事物才具有美感,對于她這種并非天生麗質(zhì)的女人來說,也許模糊的視覺才能帶來美的想象。特別是在懷上我后,她對銅鏡的依賴上了一個高峰,因為在孕期,她的皮膚變得干燥,開始發(fā)炎,見鬼似的避開所有清晰的現(xiàn)代鍍層鏡子,甚至是清晨洗臉時水盆中水倒影。在我出生后,母親讓我遠離鏡子。當我長大些后,她把鏡子描述成一種危險的事物。
在十八歲前,我沒有使用過鍍層鏡子。唯一使用過的就是那面仿古銅鏡,在模糊暗黃的鏡面世界中,我是一個陰暗的人影。十八歲畢業(yè)典禮,我第一次拍了合照,在相片數(shù)十個人中,我沒有認出自己來。那面仿古銅鏡隨時間推移,年深月久,銹蝕得越發(fā)嚴重,銅綠逐漸覆蓋意識的平原,最初我還能在鏡面中辨認自己的輪廓,后來看到的是一層厚如苔蘚的銅綠。某天,我走進母親的臥室,發(fā)現(xiàn)她擁有了一面新的鍍層鏡子,端詳鏡中衰老殘損的自己,卻笑靨如花。我知道她最終接受了自己,然而當我第一次站在那面鍍層鏡子前時,看到的是一個滿臉長著銅綠色疙瘩的男人,嚇得跑出了房門。我的生物學得很好,要是進行戈登蓋洛普鏡子測試,我肯定無法通過,無法認出鏡中的自己,會被判定為沒有自我意識,連一只猿猴都比不過。
此前馬可說,他突然忘了自己是誰,那么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是誰,我目前擁有比他更多的物品,唯獨不想擁有的就是臉上厚厚的銅綠。馬可說,我臉上的不是銅綠,只是長滿青春痘,是年輕氣盛的標志。馬可的勸慰是無效的,而且我也并不覺得悲哀,反而一種空洞的、輕松的、有待被填滿的愉悅感,在我身體里聚積著。我等待自己重塑那天的來臨。母親說,我終于長大了。父親說,我需要一種歷史感。我?guī)е麄円笄械钠谕瑥募依锇崃顺鋈ァ?/p>
搬出去幾天后,我打電話回家,接電話的是父親。我馬上問他:
“爸,為什么我需要歷史感?”
“人是唯一具有歷史感的生物。”宣講教科書似的,他給了我一個回答。
我和馬可是鄰居,住得很近,從小是朋友,發(fā)現(xiàn)兩人的名字可以合成那位著名的歷史人物:馬可·波羅。在我們兩棟房子之間,有座觀賞用的噴水池,水池中央有塊會隨水流滾動的大圓石。大圓石就是“馬可·波羅”這個名字中間的那一點。我原本并不叫波羅,而是羅波。有些閑人經(jīng)常拿我名字開玩笑,說我是“蘿卜”。為了跟馬可組成“馬可·波羅”,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為波羅。到了后來我才再次意識到,自己逃不開變成植物的命運,因為波羅跟菠蘿兩者讀音沒差別。但我沒有繼續(xù)糾結(jié)下去,學會了當一棵植物。植物并不在意自己的長勢,所有為了美觀的綠植修剪,為了果實更甜美的養(yǎng)分控制,都不過是人為干預。
由于兩家太近,當時對方家里發(fā)生什么事,只要豎起耳朵聽,就能聽出個大概。但發(fā)生在彼此身上的事情——也就是我們離開家的原因——聽起來非比尋常,我們對彼此的遭遇也感到訝異,很快就開始計劃在外面找個房子共同生活。一開始,馬可是抗拒的:“要是所有像我們這樣的人,都自發(fā)住在一起,那個地方就成了集中營,很容易被一鍋端!”我努力打消馬可這種制造假想敵的恐怖念頭。雖然目前這個階段并不需要互相勸慰,但我還是耐心地跟馬可分析了起來:“這種遭遇實在太平常,是社會的縮影,沒什么值得互相勸慰。狀態(tài)只是暫時的,我相信,我們最終會各歸其位,你會找齊丟失的物品,我會除掉臉上的銅綠。唔,這么說,我們好像在做著相反的事呢。”最終,我們在一個單身公寓小區(qū)里租了套房子,住下來。
今天是周末,天氣晴朗,馬可·波羅什么也做不了,但可以去逛逛舊貨市場,把那匹銅馬買回來。我們坐地鐵到終點站,再換乘公交,耗費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才抵達位于郊外的周末舊貨市場。
舊貨市場有上萬個攤位,一個連一個,組成一片棚戶區(qū)似的龐大綜合體,只有在重新開發(fā)的荒涼郊外,才有足夠的土地面積建造這樣的綜合體。來逛舊貨市場的要么是懷舊的人,要么是獵奇的人,唯獨沒有為了淘便宜貨蜂擁而來的人,因為這里并不出售泛濫的工藝品和廉價的仿冒品,這里只有無數(shù)稀奇古怪的東西,而且市場營業(yè)方規(guī)定所有攤位不能出售同樣的商品。也就是說,我們在舊貨市場里看見的每一件商品,都是唯一的,而且價格有時候高得出奇。我上次買的花瓶,就足足花掉了我一個月辛苦賺來的薪水。
馬可有一筆非常可觀的積蓄,自從搬出來住后,他把積蓄主要花在舊貨市場里,他說存錢是一個騙局,只有揮霍錢財和不斷買進二手貨,才能擺脫他形同被肢解的焦慮。對這種思維,我敬而遠之,之所以跟他前來,不過是因為父親說過,我需要一種歷史感。舊貨市場在售的商品完全滿足我的需求,幸運的話,還能看到倒賣的恐龍化石還有古代青銅器,但絕不會出現(xiàn)像母親那面仿古銅鏡這樣的贗品。這里的店主雖然嘴巴油滑得很,可手中的商品卻絕對不摻假,只要出得起滿意的價格,就能擁有一件獨屬于你的寶物。舊貨市場的經(jīng)營理念跟我不謀而合,因為我那張被銅綠覆蓋的臉也絕對獨屬于我一人,慢慢地,我愛上了這個奇妙的地方。
我們規(guī)劃了幾條路線,路線將舊貨市場劃分為幾個部分,按著路線有順序地游覽,就能走遍舊貨市場。馬可在疾行,生怕銅馬被人早一步買走。我跟在他身后,被熙熙攘攘的人流擠迫著,步履維艱。來的次數(shù)越多,我就越發(fā)覺得舊貨市場跟人體有某種相似之處,那些曲折的、交叉的、或大或小的過道,不就是血管系統(tǒng)嗎?我們這些揣著錢,游走在過道上的游客就是運送氧氣的血紅細胞。那些攤位,是人體組織器官。攤位上的商品,無疑可以比作組織細胞。舊貨市場的商品像人體細胞一樣,有它特定的更新周期,在周末期間更新速度會加快,一天能賣掉三分之一。
走在舊貨市場的每一步,我都在過度消耗自己的視覺、聽覺、分辨能力以及金錢。但馬可天生為這種消耗而生,作為交換,他因此能得到組成身體和記憶的二手商品。只有我在進行一種沒有回流補充的消耗運動,因為我缺乏具有引導性的目標,只是隨意走動,享受這里散發(fā)出來的所謂歷史感,像植物徜徉在光線下,進行自養(yǎng)型的光合作用。然而,我終究不是一棵綠色植物,只是一片無機的銅綠,在不斷發(fā)生被動的銹蝕。每次來舊貨市場,馬可總會從第一個攤位開始他的尋寶之旅,但今天他目光灼灼,被牽引著似的,堅定地朝某個方向行走。那匹特洛伊的銅馬有什么神奇之處呢?既然馬可說,銅馬有一層樓那么高,那么馬頭肯定會高出舊貨市場的頂棚。但我剛從人行天橋走過時,并沒有發(fā)現(xiàn)銅馬的頭從頂棚上露出來,也許那匹銅馬是倒著放的。
馬可·波羅——看,馬可總是在波羅前面,這也難怪,走著走著,馬可很快就在我前面的人流中消失了。即使失散,我敢肯定馬可不會因為我走丟而放棄他繼續(xù)朝銅馬所在攤位前行的腳步,畢竟馬首是瞻嘛,跟在后面的人永遠是我。馬可的生活讓我嫉妒,他有錢,工作收入比我高,還有廣泛的社會人際關(guān)系。我提出和他合租,也是因為我知道馬可會主動提出承擔房租。哦,他還有一個合法的妻子,雖然不是賢妻,還把他掃地出門,讓他患上某種精神創(chuàng)傷。我唯一擁有過的優(yōu)越感,就是知道馬可的物質(zhì)生活被摧毀了,還被趕出家門,精神繼而受到了莫大折磨,我得以在他的生活里承擔一個給予安慰的重要角色——不,還有另一樣東西是我能夠以此自居的:我擁有更豐富的人文學識。盡管這些人文學識無法像馬可的經(jīng)濟學學識那樣,為我?guī)砜捎^且來源持續(xù)的金錢,但這偏偏是我能在這段時間為他進行生活指導分析的根本所在。我們擁有對方缺失的東西,這就是為什么我那么執(zhí)著要跟他生活在一起,組成“馬可·波羅”,一種共生關(guān)系。假如去做個街訪,單獨問市民是否知道“馬可”或者“波羅”是誰,他們會給出否定的答案。要是問他們是否知道“馬可·波羅”,我想,他們中大多數(shù)受過教育的人,都會想起那位撰寫了《馬可·波羅游記》的歷史人物。
臨近中午,天氣越來越熱,我在原地等待馬可,也沒等到他回來找我。我的額頭冒起了汗,于是走進舊貨市場的深處,開始自己的尋寶之旅。舊貨市場里并不比外面涼快,像烤爐似的,但我感覺自己的臉冷得像塊鐵。我用雙手摸索自己的臉,眼耳口鼻以及臉骨的形狀,都不能輪廓鮮明地被手指的神經(jīng)末梢感知,冰冷的鐵的質(zhì)感,全是銅綠疙瘩。如果我的臉真的如同我在鏡子前看到的,全是銅綠,那為什么父親會叫我去尋找歷史感呢?那些出土的青銅器文物,不都是覆蓋厚厚的銅綠嗎?我也是一件銅器,是歷史的代言者!……不,父親沒有錯,是母親把我的歷史剝奪了:我的童年沒有見過自己,我遠離一切能映出自己的,并以鏡子為代表的事物。我跟馬可說過:往日不可諫。這句話放在我身上同樣適用。但是,來者猶可追!
我正是抱著這種追尋未來的信念,在這個充滿歷史物品的市場里,開始一場尋寶之旅。
“老板,你好。請問你這里最古老的東西是什么?”來到每個攤檔前,我都這么開口問話。
“你才是最古老的東西。”突然有個聲音冒出來,但我找不到源頭,沒有繼續(xù)理會。
這些店主是一群熱愛攀比的家伙,他們明白這里只有最古老的商品,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顧客的眼球,歷史是具有金錢價值的。他們紛紛拿出鎮(zhèn)店之寶:猛犸象的毛發(fā),山頂洞人的頭蓋骨,法老帝王的裹布,外星人的指甲……當然,它們?nèi)純r值不菲,甚至有一位老朽的店主說他自己就是店里最古老的商品,已經(jīng)活了幾千載,如果我對他有興趣,可以將他買下來。他們在我面前列出來的藏品確實沒有重復,而且各自代表著某種生命階段和人類世界發(fā)展的進程。我仔細地撫摸所有鎮(zhèn)店之寶,表面覆蓋著一層細微如絨毛的灰塵,十指全部沾上古老商品的印記。
“買下猛犸象的毛發(fā),夜里會有冰河入夢來嗎?”
“山頂洞人的頭蓋骨,怕會招惹原始的幽靈吧?”
“法老帝王的裹布代表的難道是永生?”
“外星人的指甲能否挖開宇宙蟲洞呢?”
“買你回家,你能完整重述中華上下五千年嗎?”
我故作姿態(tài),裝作是個有錢人,趾高氣揚地不斷發(fā)問,也試圖搞清楚這些價值不菲的東西是否具有足夠的歷史感。對于我的連續(xù)發(fā)問,周圍的幾位店主都回答不上來,他們只保證這么一種商品是確確實實存在的,至于背后的意義,他們不負責解讀。另外,要是讓店主知道我口袋里其實沒幾個錢,他們是不會如此卑躬屈膝地向我兜售的,但為了慫恿我買,他們現(xiàn)在還要讓我逐一試用,有點賄賂的感覺。人被捧得越高,被伺候得越周到,就越不敢說任何忤逆的話,我又想起了一句古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我注意到近段時間,古詩詞、諺語還有古人面孔常常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遇到某些適用的情況,它們就會被不自覺地引用,作為現(xiàn)實的批注。
“先生,請你試戴一下。”售賣外星人指甲的店主說,“不是誰都能體驗當一個外星人的滋味。”
外星人的指甲,是個黑乎乎的片狀物,做成了帶指套的用具,可以固定在指甲上。店主幫我戴上外星人的指甲后,其他店主緊接著依次將一塊蓬松的猛犸象毛發(fā)貼在我的手背上,用法老帝王那段長長的、似乎沾著干尸皮膚組織的緞帶,在我手臂上捆了一圈,最后還把山頂洞人的頭骨蓋在我頭上。
舊貨市場內(nèi)部越來越熱,氣溫在不斷攀升,我身體被覆蓋的部分,特別是被所謂最古老的商品覆蓋的皮膚,開始局部出汗,癢癢的,帶著刺痛,那底下似乎有什么蟲子在爬行,企圖刺破我的皮膚進入血管。他們期待我給出一個正面的回答,在這幾種商品中分出個高下,可我依然沒有被任何能稱作歷史感的情緒充盈。我仿佛被控制了,站在原地無法動彈,只要稍微一動,山頂洞人的頭蓋骨就會摔碎,小小的指甲掉進下水道如同墜入宇宙深空般無法尋回,而手臂上的裹布和毛發(fā)會被汗水浸爛,那時候我就百口莫辯,只能自掏腰包。我把目光轉(zhuǎn)向那位自稱活了幾千載的老者,他還沒作出表示呢,不妨先等他發(fā)表一下高見。
“夢境,記憶。”他在我耳邊呼了最后一道氣,那道氣里包含這兩個虛無縹緲的詞語。然后,他就倒地身亡了。周圍的人紛紛跑過來幫忙搶救,我趁機把身上的行頭全部卸下來,匆匆逃離了現(xiàn)場。
老者死亡的消息,在舊貨市場這具異常活躍的軀體里,沿著神經(jīng)快速傳播開來。所經(jīng)之處,我都被其他店主以懷疑并帶著惡意的目光打量著,明明那是一分鐘前發(fā)生的事,可是如今已經(jīng)眾人皆知似的。我低著頭,行色匆匆,穿行在無法找到出口的舊貨市場內(nèi)部,每個與我摩肩接踵的人都在給我的身體施加一種擠壓,不知是錯覺,抑或是真的在受到攻擊呢。對這種輕微的冷暴力,我找不到確切理由,畢竟老者的死與我無關(guān)。有個人從我離開現(xiàn)場后,就一直尾隨而來,腳步比其他人都要急迫,明顯是奔著我來的。是警察,還是企圖報復的人?我不敢回頭看清他的模樣。
這種被迫害妄想的公共氛圍,在我突然撞上馬可時,減弱了。也許其他店主盯著我,純粹是因為我自己過于心虛,腳步蹣跚,像極了畏罪潛逃的人?馬可在我臉上輕輕拍了兩下,我才回到現(xiàn)實中來。
“波羅,我找你找了很久。你去哪兒了?”馬可問我,“馬可·波羅不應該分開。分開了,就是有名無姓、有姓無名。”
我現(xiàn)在沒空跟他玩文字游戲,因為尾隨而來的人還沒有放棄跟蹤。我機警地注意四周人群中那些閃爍的眼神。這時,下起暴雨來,頂棚被機關(guān)槍掃射似的雨點敲得作響,說話的聲音都聽不到,攤位跟攤位之間的頂棚連接處,還偏偏漏雨,地面排水溝很快就漫溢了,整個舊貨市場成了威尼斯水城。
“趕快走吧。”我拉著馬可混入人群中。
“現(xiàn)在走不了,下雨。”馬可說,猛地停住腳步,“還有,我找到那匹銅馬了。”
“那就兜兜圈子,總不能傻站著。”我提出一個愚蠢的建議,既然走不了,就跟敵人周旋,甩掉他。
“不如我?guī)闳タ纯茨瞧ャ~馬。”馬可拉著我朝相反方向走。在被馬可拉走的某個瞬間,我相信自己跟尾隨而來的那個人進行了一次眼神對視。我知道他要找的人是我,那種眼神絕對不是久別重逢的熟人或者陌生人之間會出現(xiàn)的,而是在傳達一個信息:“我要找的就是你!”
本來是我拉著馬可,要他跟著我的方向前進。現(xiàn)在形勢反轉(zhuǎn)了,我被他牽著走,而且他率先找到此次尋寶之旅的終極目標,特洛伊電影的銅馬道具,一件可觸可感的東西。而我一無所獲,即使尋獲了,也是無法具體拿出來的“歷史感”,恐怕還惹來一次殺身之禍,甚至一場官非。我總是滯后,正如馬可·波羅這個名字所展示的:馬可在波羅的前面,才構(gòu)成有源可溯的歷史人物;波羅·馬可,不可以;單獨抽出來的馬可,或者波羅,也不可以。終究,需要歷史感的人是我,而不是馬可。馬可只是弄丟了一點點私人物品,暫時迷失了自己。這么說,我總有一天要擺脫馬可,若要擺脫他,就不能僅僅從名字層面上進行。本來給“馬可·波羅”這個名字捏造一種含義,添加批注,就是件荒唐的事。
“但那匹銅馬出了點意外……”馬可說,“它還沒有成形。”
“什么意思?難道它還沒有出生?”我開了個玩笑。
“去了你就明白了。這也是我們進行創(chuàng)造的一個機會。”馬可回答。他加快了腳步。我被拽得踉蹌起來,試圖掙脫他的手,但失敗了。
來到舊貨市場最深處,這里的環(huán)境比前面陰暗得多,在售的商品也古怪得多,很多游走在違法邊緣的貨物都在這里出售。這里是地下市場般的存在,燈光亮度刻意調(diào)低了,鋪面還加了很多花邊裝飾,能在執(zhí)法人員進行例行檢查時,實施障眼法。要是我剛才試用的幾件藏品出現(xiàn)在這里,那么它們的可信度會大大提高,畢竟真實的東西從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看來銅馬就在這里,它的價值也是毋庸置疑的。
突然,一個戴著頭巾、中東商人模樣的人攔在我們面前,跟馬可對視一眼后,馬上轉(zhuǎn)入一條用帳幕遮蓋起來的過道。我還以為過道里會有另一番奇異的風景,但過道里沒人,只見一大堆厚厚的銅片摞在一旁。我無言等待著,覺得中東商人的手里應該會有各種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珍稀寶藏。然而,他卻說: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銅馬呢?”我問,“先驗貨。”
“這就是銅馬。”馬可指著地上的銅片說。
“我怎么知道拼起來是匹馬呢?萬一是頭驢……”我不服氣。
“舊貨市場的買賣守則,是從不弄虛作假。”中東商人說,他沒有生氣,但嚴肅的神情讓人害怕。
“波羅,沒事的,這肯定能拼起來。”馬可說。
馬可從口袋里掏出一筆厚厚的現(xiàn)金,“這匹馬會幫助我回家。”他補充,然后把現(xiàn)金遞給中東商人。連數(shù)目都沒有點,這位神秘的賣家就把錢塞進布袋里。這里的另一個買賣守則就是只收現(xiàn)金,所有電子支付以及信用卡都行不通。剛才馬可說,這匹馬可以幫助他回家,到底是回哪個家,是我們合租的公寓,還是他妻子那兒?
“這匹馬拼起來后,會很高,特別占地方。”中東商人臨走時說,“要把它藏在舊貨市場非常困難,我只能拆開存放。麻煩兩位把部件全部搬回家后再組裝,以免暴露這個地方。”中東商人一轉(zhuǎn)身,就消失在帳幕后面。過道里的氣味有點像香料,過于濃郁,有那么一刻,我覺得舊貨市場外是黃沙滾滾的埃及大地,頭頂上是暴曬金字塔的烈日,而我們是異國他鄉(xiāng)的盜墓者。
我們無法帶著這堆沉重的鋼鐵原路返回舊貨市場入口,也搬不動。但這趟交易非常人性化地配備了后續(xù)服務(wù),馬可走到過道的盡頭,破解機關(guān)似的打開一堵看起來密封的隔墻,一輛小型搬運貨車就停在外面的馬路邊上。原來我們離路邊這么近,不過那里沒什么人活動,是未經(jīng)開發(fā)的荒野,通常人們從我們剛才來的那個入口進舊貨市場。出口的高度不足以允許貨車倒車進來,我們只能將銅片一塊塊地從過道的這頭搬到另一頭。
即使銅馬被拆成了部件,在搬運過程中,也不難分辨哪些部件屬于馬的哪個部位。另外,從銅片的弧度判斷,正如特洛伊的木馬那樣,這匹銅馬也是中空的,但腹部的空間至多只能藏下一個人。銅片與銅片之間本來用鉚釘銜接,被拆開后,鉚釘松松垮垮地掛在孔上,因此,在搬完銅片后,我們還在地上的沙土里赤手摸索檢查了一遍,確保沒有遺漏任何一顆鉚釘,那種細致活像真正的盜墓者。
馬可先上了車。我剛走出過道,準備把隔墻重新封起來時,就看見那個尾隨而來的男人突然闖進巷子,沖我跑過來。情急之下,我沒來得及封好墻,就跳上車,叫司機趕緊離開。
“慌慌張張的,你干什么呢?”馬可問我。
“有人要追殺我。”我說。
“是特洛伊人的亡魂嗎?”馬可開玩笑道。
“不見得是……”我爬起來,透過貨車尾窗望出去。車輪濺起了泥濘。那個男人手里舉著什么東西,說不定是一把刀,跑了一段距離,但很快他就被貨車遠遠甩在后頭。我有種劫后余生的舒暢感,但我想起過道的入口忘了重新密封,就像我的身體也有個口子沒關(guān)上,一種裸露的、被入侵的危機,油然而起。
顯然,單身公寓里放不下這堆部件,更別說拼起來后足足一層樓高的銅馬。卸貨后,馬可在部件四周走了一圈,目測這匹銅馬沒有一層樓那么高,可要把它塞進房子依然是件難事。附近有一條廢棄的隧道,于是我們重新把貨車司機叫了回來,把部件運到隧道里頭去。運貨完畢后,司機從駕駛室伸出頭來,告誡說:“希望你們不是在搞什么殺人越貨的行當。”馬可拍拍胸口,發(fā)誓說我們只是收藏愛好者。但司機這句話讓我一下子頭腦發(fā)熱,好像瞬間感染了風寒,再看著幽深的隧道,加重了我頭暈目眩的病態(tài)感。
只要對動物身體結(jié)構(gòu)足夠熟悉,用鉚釘將部件逐一銜接,完成拼接銅馬的工作,不是件難事。但廢棄隧道非常黑暗,僅能依靠隧道上方高速公路投下的燈光,而且部件的大小和比例關(guān)系總是難以分辨,這項本來簡單得跟兒童手工活差不多的工作,一直持續(xù)到第二天凌晨才結(jié)束。我們?yōu)楹文敲磮?zhí)著要在當晚把銅馬拼接出來?我們沒有需要快馬加鞭執(zhí)行的任務(wù),沒有日行千里的計劃,而且這只是一匹不會走動的馬。但馬可發(fā)現(xiàn)銅馬的馬蹄底下安裝有輪子,只要翻出來,這匹馬就能輕易地被推動。晨光熹微時,我們合力把這匹在黑暗中誕生的銅馬,推到隧道外的陽光底下,馬大概有兩米高,散發(fā)著銅金色的光澤,馬頭昂揚向前,連接處的鉚釘閃閃發(fā)亮如鉆石,遍布馬軀的接縫線讓它看起來像古代征戰(zhàn)時身披護甲的戰(zhàn)馬。
我不敢說馬可完成了他的愿望,會馬上停止無休止收集二手物品的沖動,至少他現(xiàn)在神情安寧,把手放在馬背上,頭貼住馬軀,似乎在感受它的生命,“聽,它在呼吸。”我猜他聽到的是中空的馬腹里的氣流聲。還有一點要加以說明,拼接完畢的銅馬不是完全封閉的,腹部底下有一道可以推拉的活動門,還有一個鎖扣,只要打開鎖扣,推開活動門,人就能藏在里頭,跟特洛伊木馬有同樣的作用。
“我歸家的日子指日可待。”馬可給我一個眼神的暗示。
“難道你是想……”我一下子明白他買這匹銅馬的意義所在,“木馬計?”
“嗯,前提是我妻子能接受這份禮物的驚喜。”馬可說。他指的是把自己藏在銅馬里,像特洛伊木馬攻城戰(zhàn)那樣,將銅馬連同藏在里頭的自己,一并送給他妻子。那個女人會覺得這樣的舉動是浪漫的、是驚喜的嗎?我看并不然,他們之間的矛盾也根本不能靠這種噱頭來化解。
“好吧,請進。”我拉開銅馬腹部的活動門,示意馬可鉆進去。
但馬可把活動門關(guān)上了,用手掌在銅馬身上拍打,發(fā)出厚實的金屬哐哐聲,“我的問題不急著解決。這匹馬尚且是鋼鐵之軀,人又怎么能甘愿當一棵植物?”他突然改變了話題。
“這話何解?”
“無論蘿卜,還是菠蘿,”馬可說,“都是植物。”
“對。”
“但你終究是個人類。”
“對,我是。”
“不,你身體有一部分是柔弱的植物,你一直以來都沒有正視這個問題,因為你連鏡子都不敢照。為了報答你幫我買到這匹漂亮的銅馬,我要帶你去醫(yī)院。我的存款足夠你完成這個手術(shù),給你全新的人生。”
“我才不需要你的施舍,也不必你來插手我的人生。”說著,我就向前走,要離開,“我之所以看不見自己的樣子,是因為我母親。我的生活里沒有鏡子。父親說,我需要一點點歷史感來彌補這個缺陷——”
“這就是癥結(jié)所在,生理造就你的心理,諱疾忌醫(yī)。”馬可打斷我的解釋,“走吧,不必為我省錢。”
馬可居高臨下地對我進行分析的姿態(tài),讓我感到非常不愉快,那話也聽著很刺耳,讓我意識到自己處境的窘迫。這事兒本來不是我在做嗎?我才是那個為他進行生活分析的好朋友,而他要做的,是從那筆巨額存款里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來維持我們的物質(zhì)生活罷了。馬可沒有理會我此刻的內(nèi)心是在受辱,獨自把銅馬推入隧道深處藏起來,然后堅持把我?guī)У搅酸t(yī)院。
值班護士為我辦理掛號,把單子推到我面前,讓我填寫資料。她坐在分診臺,翻起眼睛打量我,眼珠子在抹有眼影的眼眶里,上下轉(zhuǎn)動,保持醫(yī)務(wù)人員一貫的冷靜克制。但我能從她的眼里看到一絲好奇,她對我臉上的某種東西進行考量。在此之前,似乎沒有人這么觀察過我,包括我的父母,或許是我從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這個護士眼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帶著目的性的觀察。我填完單子后,她也不問我詳細情況,指著某條通道,要我?guī)е鴨巫拥侥莾喝ィ乙晃恍掌さ闹髟\醫(yī)生。
我按她指示走過去,看見科室的名稱是皮膚科。
“這位姓皮的醫(yī)生,肯定是個專業(yè)的皮膚科醫(yī)生。”馬可說,指著醫(yī)生診室,要我進去。
“是呢,人的名字總是有意義的。”我回答。
見我猶豫不決,馬可直接拉著我走進診室,要我在醫(yī)生面前坐下。這位姓皮的男醫(yī)生,皮膚光滑可鑒,似乎連毛孔都被磨平了,對著我露出微笑時,臉上沒有任何一條小小的皺紋。我僵直坐在那兒,一聲不吭,凝視醫(yī)生的皮膚,固執(zhí)地要在上面找出一個瑕疵。但他的皮膚如此無瑕,令我莫名羞愧。馬可從我手里抽出單子,遞給醫(yī)生。醫(yī)生用剛才護士的那種眼神觀察我的臉,說道: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你的樹木,跟你同齡。”
醫(yī)生的這句話,有點一語雙關(guān)的味道。當時突然在舊貨市場里冒出來的那句話,此刻在我耳邊回響:你才是最古老的東西。確實,植物比人類還要古老得多。我身體里肯定也有一棵在人類出現(xiàn)之前,至少在我存在之前,就已經(jīng)在生長的植物。
“我的眼睛有問題,”我跟醫(yī)生解釋,“我看到自己滿臉銅綠。跟鏡子有關(guān)。”
“鏡子是無辜的。醫(yī)生,別聽他的,他病了。”馬可插嘴。
“鏡子只是在告訴你真實,信不信由你。”醫(yī)生用手指在我臉上進行檢查,指尖一起一伏,好像游走在凹凸不平的丘陵上。“你母親跟你一樣嗎?我是說,你臉上的這些褐綠色肉瘤。”
“她是個丑女人,當然我從不嫌棄她。”我回答。
“嗯。你又不是青銅器,哪來銅綠呢?你只是個樹人。”醫(yī)生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又重復一遍這句話,還有點沾沾自喜的感覺。
樹人,醫(yī)生說的是樹人。醫(yī)生把頭轉(zhuǎn)向馬可,解釋說,我臉上的這些褐綠色疣狀肉瘤,是人類乳頭瘤病毒引起的,雖然幾乎覆蓋了整個面部,但所幸沒有蔓延至身體其他部位,也沒有過度增厚,有望手術(shù)切除,再通過植皮來修復。
醫(yī)生跟馬可只用了幾句簡短快速的對話,就輕易地概括了我過去被一種朦朧黏稠、揮之不去的陰影所覆蓋的歲月,揪出了根本源頭。他們以科學的分析斷定我看到自己滿臉銅綠,其實是看到了臉上褐綠色的疣狀肉瘤,因心生恐懼,將其視為一種來自銅鏡表面的銅綠,是身體對現(xiàn)實作出的負反饋,以及不愿意接受自我而帶來的自我欺瞞。要是真的如此簡單,那就最好了。
由于馬可拿出金錢上的承諾,院方很快為我安排了治療方案,首先切除臉上的肉瘤,后來僅通過一次植皮手術(shù),就聲稱為我恢復了接近原貌的臉。在接受藥物控制和手術(shù)治療期間,我渾渾噩噩,感覺自己比任何時候都沒有自我意識。他們一步一步地移除我身上本該有的那種如同銹蝕銅綠般的歷史感。我像根木頭似的任由木雕師改造自己的身體。我并不是有所妥協(xié),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自己被掩蓋多年的模樣。
馬可每天都來醫(yī)院看望我,盼望我早日出院,和他一起執(zhí)行特洛伊木馬攻城計劃。我每天接受他的關(guān)心,消耗他的錢財,我的新人生全部建立在他的施舍和付出之上。也許跟我走在一起,我的模樣曾令他在別人面前覺得難堪吧?我并非不懂得感恩,只是恐怕這樣下去,馬可·波羅將永遠維持它原有的順序,馬可永遠在波羅前面,永遠牽制著波羅,馬可的二手歷史,他走過的路,就是波羅的未來之路。可是,這本來不就是我自己一手打造的組合嗎?解鈴還須系鈴人。
我出院那天,馬可在醫(yī)院外的長椅上等我,像等待出獄的親友,而他就是把我送進監(jiān)獄的人。我被改造一新,但時至今日仍未看過鏡中全新的自己,每次醫(yī)生要我看看自己臉上的治療效果,都被我拒絕了。理由是,我還沒準備好接受一個陌生的模樣,盡管那或許是我本來的模樣。我已經(jīng)習慣了在一團褐綠色的濃霧中摸索生活,清晰可鑒反而令人不適,如同在戰(zhàn)火里幸存的士兵,無法在歸鄉(xiāng)后接受一種恍如隔世的安寧歲月。
我接受治療的過程長達半年,但回想起去舊貨市場的事情,仿佛是在昨日。一次日常的出門購物,怎么會演變成一次漫長的治療呢?那天清晨,馬可曾對我說過一句話:那只老虎穿了件外套,褐綠色的棉襖——我忽然意識到,他所說的老虎就是我,褐綠色的棉襖就是我臉上的肉瘤。
威武殘暴的老虎,怎能屈尊穿上褐綠色的棉襖,擋住身上醒目的條紋?
像我早已預料的那樣,事實證明,過去生活的陰影要比想象的埋得更深,蔓延得更廣。我離開醫(yī)院沒幾步,被跟蹤的感覺再次出現(xiàn),這種感覺是從舊貨市場里被我?guī)С鰜淼摹T诮纸牵袀€人影正朝我奔來,自從上一次他沒追上貨車后,給了我一個喘息治療的空窗期,如今卷土重來,想必是為了那個老者的死而來。令我訝異的是,我已經(jīng)改頭換面,那個人仍然認出了我,還追到這里來。復仇自然不必說,但我的死不能為老者帶來任何安慰,因為死者是不需要安慰的。在城市里甩掉一個人容易得多,我們很快就回到了家。
這個小小的單身公寓,比以往更干凈整潔,我還以為自己在醫(yī)院待了半年,沒有我的勸阻,這個家肯定會被馬可的二手貨塞得滿滿當當。
“想不到吧,自從得到那匹銅馬,我再也沒有購物的欲望了。”馬可為自己擺脫了一種思維的惡疾,感到很自豪,“我現(xiàn)在每天都住在銅馬里面,把電影《特洛伊》看了一遍又一遍。”
“這……”我無法相信他的狂言妄語。
“我把銅馬搬到公寓后方的那座廢棄工廠里了,還請附近的一個流浪漢替我看守。”
“你要在那兒住到什么時候?”
“到今天為止。”
“哦?為什么?”
“你回來了嘛。我今晚也會搬回來。”馬可走到窗邊,好像看著舊貨市場的方向,但其實他看的是同一條軸線上的那座廢棄工廠,“若不是銅馬只住得下一個人,我們兩人都應該一起住進去。”
“你要是喜歡,你可以繼續(xù)住下去。我們都應該有各自的生活。”
“可是馬可·波羅永遠不會分開。別忘了,你的臉是我花錢給你治好的,你別想就這么消失。”馬可的語氣很冷靜,“也別忘了特洛伊木馬攻城計劃。”
“你跟妻子重歸于好后,我們終究會分開,不會一直住在單身公寓里。”
“你知道狐猴的尾巴有什么用嗎?”
“保持平衡。”
“沒錯,你看出來了。你在我身后,我的生活才能保持平衡。”
“我不是你的尾巴……”
“你的臉,是我花錢治好的。”
馬可總是提起他花錢為我恢復容顏的事情,以此來要挾我。可是我連自己的臉都沒看過一眼,也沒有用手指碰過它一下,是誰當初強行要我接受治療的呢?我從肉瘤的控制中奪回自己的臉,卻又一下子成了另一個人要挾我的籌碼……
“那你把我的臉拿走吧。”
“我只要你幫我把銅馬送到我妻子那兒。”馬可聳聳肩。
他這個滿不在乎的聳肩動作,把我激怒了。我所珍視的東西,是他從不或缺的啊,而且自從有了銅馬,他的生活踏上正軌,大可以拿出這種態(tài)度來,以彰顯他的超然。
晚上我睡得并不安寧,連廁所也不敢去,因為里面掛了一面巨大的鏡子。馬可說是為了慶祝我出院,在前幾天特意買的。我憋尿了,只好到樓下的公共衛(wèi)生間解決。回來路上,追殺我的人再次從暗中蹦出來。褲子都沒來得及整理好,我就匆忙跑上樓。在我要把門關(guān)緊時,情急之中,一個想法控制了我。
我只虛掩了門,抄起旁邊那柄馬可從舊貨市場買來的聽說是古代盜墓賊使用的洛陽鏟,在那個追殺者推門探進頭來時,重重敲了過去。洛陽鏟敲在那人的腦袋上,鏟頭發(fā)出嗡嗡的顫動聲,把睡夢中的馬可驚醒了。他跑出臥室,看到此情此景,在昏暗的客廳里僵直了身體。我仍舉著洛陽鏟,從鏟頭傳來的震顫把手指都震到發(fā)麻。倒在地上的是一個男人,頭顱底下洇開一片暗紅的鮮血,在那片鮮血準備朝門外的樓梯倒流出去時,馬可抄起沙發(fā)墊子,把血流擋在屋內(nèi)。他把那個估計已經(jīng)死掉的男人拽進家里,關(guān)上了門。
“馬可……這人……半年來一直在追殺我……”我解釋,“我換了張臉,他都對我窮追不舍!”
“波羅,看你干了什么?你病了!”馬可努力壓低聲音斥責我。
“我這不是……那個老頭的死與我無關(guān)。”我把半年前在舊貨市場的遭遇告訴馬可。
“肯定有什么誤會。”馬可蹲下來檢查男人的情況,“你看,這是什么啊?”
男人手中拿著一張卷起來的紙,還有一張便簽似的東西,用橡皮筋捆在一起。馬可抽出那張便簽,默讀完畢,用比剛才更為堅定的眼神怒視我,把便簽塞進我手中。便簽寫有留言,字跡老舊而潦草,看完內(nèi)容后,我猜這是那位暴斃的老者——不,他當時還沒有死透,是他在臨死前匆忙寫給我的。便簽中寫道:
“最古老的肖像。夢境。記憶。我一直在等你出現(xiàn),現(xiàn)在把它送給你。”
“這人是替那老頭來給你送東西的!”馬可說,“你怎么可以那么沖動,把他打死?!”
“不可能……我記得他當場暴斃,怎么可能寫字留言?他還說自己活了幾千年,誰信呢?況且這男人一直跟蹤我,這幅肖像和這張便簽,不過是他追殺報復我的事情暴露后,拿來做借口打掩護的啊!你想想,誰會半夜跑到別人家里送東西?”
“總之,你殺了人……”
我們爭執(zhí)不下。這時樓道里響起一絲聲音,我們馬上噤若寒蟬。正當我要去看那幅肖像畫是為何物時,馬可卻拽著我,催促我處理現(xiàn)場。
“他死了,必須處理掉……波羅,要不然,你的麻煩大了。”
“哦,銅馬!銅馬在哪兒?”
“在對面工廠——你要干什么?!”
馬可很快意識到我的計劃,就像我當初意識到他購買銅馬的目的一樣,兩者都如此荒謬。但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明天物業(yè)管理人員還會上門,征詢附近那個垃圾焚燒場掩埋工作的意見。現(xiàn)在天也將亮,我們沒有多少時間。馬可拉開棉被的鏈子,把男人尸體裝進去,棉花剛好能吸收那些還未流盡的血,以防搬運的時候滴下來。我們抬著這團古怪沉重的東西,一路走下樓梯,穿過單身公寓樓下清冷的小道。保安亭里的保安睡著了,我們悄無聲息地走出小區(qū)門口,朝著工廠方向走去。
我感覺手熱乎乎的,看來棉被已無法再吸收從尸體頭顱涌出來的無盡鮮血了。我們走過的道路會不會出現(xiàn)四個沾血的凌亂腳印,從上面可以判斷有兩個人曾抬著重物,一具尸體,艱難跋涉,冒險拋尸?這具尸體,已經(jīng)代替我們家之間那座水池中的大圓石,成為“馬可·波羅”中間那一點。因為這件事,我們更加無法分開,兩條鮮活的生命被一樁死亡事件永遠綁在一起……
我這么憂心忡忡地想著,終于熬到工廠出現(xiàn)在不遠處。其實,我們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距離,死亡、尸體以及鮮血,無限拉長了感受的界限。那匹銅馬放在空置的廠房中央,遠遠看著,甚至會以為那是一匹真馬,但在我看來,那更接近一匹幽靈戰(zhàn)馬,等待騎士亡魂的回歸。這個死掉的男人將成為它的新主人,這兩者都是舊貨市場的產(chǎn)物。
我和馬可全程沒有用語言交流,極其默契地完成了拉開銅馬腹部的活動門,將尸體塞進去,關(guān)上活動門,檢查四周是否殘留血跡等一系列工作。這種默契更加讓他相信,我們是一體的,無法分割,因為他接下來這么說道:“波羅,我又替你除掉了一個麻煩。我們在同一條船上。”聽起來更像殺人的是他,而我不過是他拉來墊背的,于是在這樁命案上誰也脫不了干系。但尸體不能這么擱著。這匹銅馬也不能將尸體消化成能量,形成廢物,變成馬糞排出來,以毀尸滅跡。
“明天,垃圾焚燒場會進行掩埋。”我說。
“現(xiàn)在它還在燒嗎?”馬可走到廠房窗前,四處看看。
“是的。”
在離廠房約兩公里的河邊,有一個臨時垃圾焚燒場。由于燃燒廢氣持續(xù)擾民,今晚它的火種最后一次升起,明天中午就會有市政府安排的挖掘機過來進行沙土掩埋。在遙遠的天際之下,垃圾焚燒場升起橘紅色和藍綠色混合的火焰,我瞬間誤以為那是極光,煙霧籠罩在兇殺的平原,迷惑心智。
晨曦似要破壁而出,我們推著這尊背部位置就高達兩米、無比沉重的銅馬,艱難離開工廠,朝熊熊烈火那邊前進。馬可·波羅當年真的來過中國大地嗎?奧德修斯和他的航船如何穿越海妖的海域?鄭和七次航行虛耗了多少生命?歷史上所有前進的艱辛、謎團和死亡,抵達的渴望,這種種歷史感,在我們推動銅馬時,全部變成手掌在銅器身上摩擦時生出的熱量,燒紅了銅馬,炙烤十指和掌心,如同承受炮烙之刑。
正在焚燒的垃圾堆,足足有一層樓那么高,橫跨幾十米,躥起的火焰形似噴發(fā)的火山。我們二人和銅馬站在高高的火墻前,被映紅了臉。馬可打開銅馬腹部的活動門,死去的男人墜落地面的聲音被火焰聲蓋過了。我們一前一后抓住尸體,將他扔進了火里,垃圾堆被砸中的位置黯淡了幾秒,很快又重新燃起不熄的毒火。
凌晨,將銅馬推回工廠,清洗所有血跡,再用漂白液除掉公寓門前的血味;第二天,物業(yè)管理人員要我們在垃圾焚燒場掩埋同意單上簽名;中午,幾輛挖掘機開始掩埋焚燒場。經(jīng)過幾個小時的焚燒,死亡都燒成了灰燼。我和馬可站在陽臺,看著挖掘機如火如荼地進行掩埋工作。
“那位東方旅行者,再次安全抵達中國。”馬可打了個比喻。我沒有回答他。
我們沒有馬上執(zhí)行特洛伊木馬攻城計劃,因為誤殺事件制造出來的冰冷氣氛,那幾天還困擾著我們的情緒和夢境。我們還互相恫嚇,說死者的陰魂還藏在銅馬的身體里,搞到最后兩人都對鬧鬼的事信以為真,睡不著,只好睡在一起。我和馬可的夢境有相似之處,可謂同床又同夢。
我夢見自己成了古代的帝王,至于是哪個朝代的哪個帝王,便不好分清了,也許帝王常常忘記自己的身份吧。接下來的情節(jié)是,我麾下有一名大將,他跟我的妃子私通,被我處以極刑。我跟馬可說起這個夢境,里面的情節(jié)感覺非常熟悉,仿佛是被掩埋的記憶,如果哪天垃圾焚燒場被挖開,那具塵封的焦尸就會重現(xiàn)人世,記憶大概也是這個道理。馬可睜大眼睛,迫不及待地要說什么,被自己的唾液嗆到了。他說夢見自己是一名元朝騎兵,沒有光榮戰(zhàn)死沙場,而是被打入大牢,最后被處死了。
“啊,你就是被處以極刑的大將?”我問,“我就是夢中的忽必烈大汗?”
“不見得。我在銅馬里住了很久,夢見騎兵很正常。”馬可否定我的猜想,“至于你成了夢中的大帝……暗示的是,你渴望成為領(lǐng)袖呢。”
“嗯,我只是希望未來可以獨當一面。”“你現(xiàn)在就可以。你的臉比以前英俊多了。”“閉嘴吧。”
“我們做這種夢,好像是從那個男人死了之后開始的。”
“我的手還在發(fā)麻。他的頭骨很硬,敲下去,手止不住地發(fā)麻……”我在黑暗中舉起雙手,還原當時的動作,“但卻像打通了經(jīng)絡(luò)似的,很爽朗……”
“你也閉嘴吧,聽得我頭皮發(fā)麻。”
當焦灼情緒的回落,也不再噩夢纏身時,我和馬可分開房間睡覺。新聞、報紙和社交平臺上,都沒有流傳關(guān)于失蹤人口或者無名尸的案件信息。馬可每天敦促我,要鼓起勇氣去看看鏡中的自己,還信誓旦旦地說,我現(xiàn)在是個帥氣的男人,只要我去照照鏡子,也會驚嘆自己的容顏。我告訴他,我一直以來想搞清楚自己是誰,要得到的結(jié)果并不是一副完整可辨的五官,而是一種認同感,如我父親所言的歷史感。
“為什么不從認同自己的五官開始?”馬可勸道,“前三十年,你沒有面相可言,但肉身是個起點。”
“嗯,所言極是。”我回答。
不久后的一個清晨,這個肉身的起點出現(xiàn)了。
我毫無防備地看見了鏡中的自己:胡子茂密,植皮手術(shù)后留下的皺紋,如漣漪在臉上蕩開,不過那更像衰老的皺紋,下巴肥厚,眼神凌厲,看起來殘暴陰險,卻透露睿智,還穿著跟我身上不一樣的古代服裝。我懷疑自己的眼睛再次出了問題。眼前這個陌生的男人,是我此生第一次見到他,好比在街上遇到一個陌生人,第一眼就認出了他就是自己的雙胞胎兄弟,那種熟悉感是一道洪流,倒灌進我意識的平原。“這就是我的臉啊……”有幾分丑陋,但不會比我手術(shù)前更丑,更難以接受。
“馬可!快出來!”我朝衛(wèi)生間喊道,“我做到了!”
“你說什么呢?”馬可刷著牙匆忙走出來。
“你什么時候在這里掛了一面鏡子?”
“哪有什么鏡子?”
我指了指墻上,一面矩形的鏡子。馬可跑進衛(wèi)生間把嘴里的牙膏洗干凈,再跑出來,把客廳的燈點亮。變魔術(shù)似的,那面鏡子不見了,水中月,鏡中花,幻影消失在烈日下。墻上只有一幅掛畫,一位帝王的肖像。
“那是什么?”
“還記得那個男人手里的肖像畫嗎?”
“最古老的肖像畫。夢境,記憶……?”
“今早起床時我把它掛起來了。這算是悼念吧?這段日子我總是很內(nèi)疚。我才找回自己的身體歸屬感不久,又被內(nèi)疚感占去了一部分,都是你惹的禍,波羅。”馬可走到肖像畫前,仔細端詳,“哎,你說你看到了什么?一面鏡子?你看到的只是這幅肖像。帝王!對了,你夢見了帝王!你知道這畫中人是誰嗎?”
這幅泛黃殘損、邊角起毛的肖像畫的右上角,有一個毛筆字落款:
“帝辛。”——帝辛,世稱商紂王。
馬可把我推進衛(wèi)生間,要我站在鏡子前,“好好看清楚,這才是你的樣子。”
“馬可,我看到了,這就是我的樣子,跟外面的肖像畫一樣。不是嗎?你看,這濃密的胡子。下巴這么肥,我肯定太少運動了。我今年多少歲?才三十,就滿臉皺紋。眼睛看起來有點嚇人呢,像老虎的眼睛。說起老虎,我身上這套衣服跟虎紋有點相似……”
“波羅,你又病了!”馬可沖出衛(wèi)生間,拿起打火機,要燒掉帝辛的肖像。
“別妄想。”我伸出腿,把他絆倒了。他撞在門框上,疼得直叫。
“波羅,我花錢為你做手術(shù),你竟然這么對我——”
我抄起鐵盆敲了過去。鐵盆的震顫,再一次把我的手指震得發(fā)麻。
我把肖像畫從墻上拿下來,對著窗外升起的太陽端詳。溫熱的太陽從紙背透過來,把帝辛肖像的每一條古老的筆觸,都照得發(fā)紅發(fā)燙,被畫紙過濾后的陽光鋪灑在我臉上,來自公元前的千年。我感覺到,肖像的陰影覆蓋在我臉上,線條跟我的臉形完全重疊。歷史的圓環(huán)運行一周后,已回到原點。舊貨市場那位老者,確實活了幾千載,也許正是來自商朝的臣民,在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認出我是帝辛,是他的帝王。他的存在意義就是為了喚醒我,先是夢境,后來是記憶,也就是現(xiàn)世人津津樂道的酒池肉林,炮烙之刑,比干那顆七竅之心,我的妲己……一部分現(xiàn)實,一部分神話,交相輝映。世人對我的爭議,就像對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的爭議一樣,歷史的根源無從用肉眼認證,只不過是尋章摘句,文物考察,子嗣流傳,但結(jié)果與經(jīng)驗是唯一的定論: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無關(guān)緊要,因為《馬可·波羅游記》是那段歷史的唯一遺產(chǎn),是可觸摸、可閱讀的遺產(chǎn),即使那是想象的遺產(chǎn)。因為想象就是真實的另一面。
我給父親打了個電話:“爸,我不再需要歷史感了。我就是歷史本身。我經(jīng)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的歷史。我還有一段漫長的空白,尚未從記憶里被喚醒,還沒有被填滿。作為代替,你給我讀讀你上課用的那些歷史資料吧。”
“你先聽我說。有一件事,我查清楚了。”父親回答。
“我是帝辛。你是說這件事嗎?”
“你外祖父的那件仿古銅鏡,那件可笑的贗品,原來是從舊貨市場淘來的。”
“不,舊貨市場里的東西,都是真的。”我立刻把電話掛了。
馬可躺在衛(wèi)生間的門邊,一動不動,血洇開了一片,就像那個死去的男人。他還有呼吸,一旦呼吸停止,他的歷史便會停止延伸。我像處理那個死去的男人那樣,處理了馬可。
第二天,夜晚降臨后,我給馬可的妻子打了電話,說馬可有一份禮物要送給她。馬可的妻子似乎等這個破鏡重圓的電話很久了,馬上答應前來。我跟她約定在附近的廢棄工廠里見面。見到我后,她露出滿臉難以置信的驚喜,說我宛若新生。我很高興她看出了我的變化。我昂首挺胸,充滿自信地走在她前面,引領(lǐng)她走去放置銅馬的廠房。銅馬依舊在夜色中沉默著,馬首朝著鼎盛的國都的無垠未來,發(fā)出嘶鳴。看見龐大肅穆的銅馬,馬可的妻子發(fā)出了她今晚的第二次驚嘆聲。
“看,這就是馬可送給你這個影迷的禮物,是電影《特洛伊》的道具。”
“肯定很貴!”她繞著銅馬走了一圈,輕輕地拍打馬軀,發(fā)出厚重的哐哐聲。但她似乎不怎么喜歡這件東西,“可惜,這不過是一堆廢鐵。”
“就是啊,一點都不懂浪漫。”
“馬可他人呢?他怎么不親自出來送給我?”
“不急,他會出現(xiàn)的。我們坐下來吧。”
我和馬可的妻子在銅馬底下坐著。天氣有點轉(zhuǎn)涼,她縮著脖子。我用汽油點燃了面前的柴火,橘紅色的溫暖火焰映紅了我們的臉。她的臉在火焰的映照下,如此嫵媚,嬌若九重天仙子。
“你跟某個人很像。”“誰?”“妲己。”“哈哈,狐貍精?”“那是世人抹黑。”“哦,你這是夸我漂亮?”“正是。”“你這話說得不得體,我可是你的朋友妻。”“記得商紂王和妲己發(fā)明了一種炮烙之刑嗎?”“當然。殘忍得很。”“不,那是商紂王和妲己兩人的浪漫愛情。”
此時,柴火燒到最旺盛的階段,火焰有半個馬身之高。我用鐵棒把柴火推到銅馬的腹部底下。
“你這是干嗎?燒壞了,馬可會不高興的。”她雖然有點緊張,但其實不在乎這尊銅馬被燒壞。
“與此相似的,西方還有一種銅牛的刑法。”
“這個我也知道。把人放在銅牛里,在下面燒火,人在里面慘叫,發(fā)出牛一樣的哞哞聲——”
“你跟妲己一樣聰慧。但你當年選了馬可,沒選我,我真的……難以釋懷啊。”
“……你剛才說,這是電影《特洛伊》的道具?是木馬計?!”
這個聰慧的女人馬上跳起來,拍打銅馬,但她嬌嫩的手立即被燙掉一層皮。炮烙熔骨鍛赤練。銅馬被燒得通紅,宛若一匹赤兔馬,而它英勇無畏的將士,在它的身體里發(fā)出沉痛的哞哞聲,正從昨日的昏迷中醒過來。我緩緩走上天臺,背手遙望。星空無比廓落,此時的國都大地,一片蕭蕭風聲,一望無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