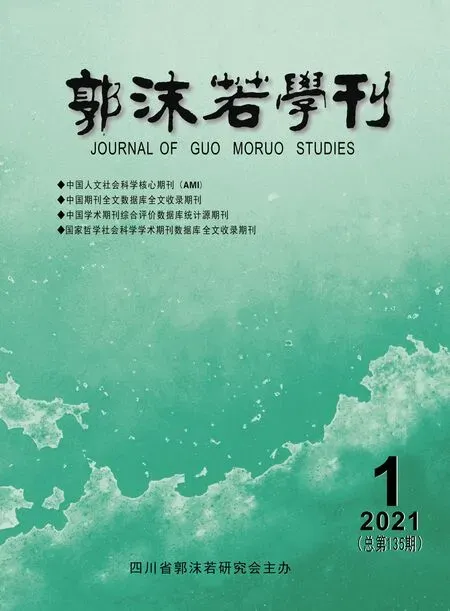《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底地得”的使用與郭沫若文學語言的現代性想象
咸立強
(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在文學漢語現代化的想象及其建構過程中,翻譯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胡適說:“創造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剛才說了。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著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創造新文學的“工具”便是語言,這是第一步的工作。西洋文學名著的翻譯對現代漢語的最大影響,便是歐化語法的確立,這也是文學漢語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并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歐化文法的侵入”的一個重要表現,便是現代漢語中語助詞“的底地得”的區別性使用。“的底地得”區別性使用是社會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最為普遍地存在于現代文學翻譯和創作中的歐化語法,譯(作)者對其區別使用的嚴格程度也就標志著自身語言表達的歐化程度。
能夠分明清晰地使用“的”“底”“地”等語助詞,是作家的創作有Grammar 的表現,而有Grammar 則是邏輯嚴密和現代的典型表征。語法使用的歐化并不必然等同于現代化,卻是文學漢語現代化想象最重要的途徑和方式。東聲在《讀書隨筆:巴金家底“的”“底”“地”》中說:“他底著作到現在要以膾炙人口的《家》為最有名,除了內容富有不滿意舊家庭和革命的氣氛外,國語文法方面,我注意到了他辭句底分明清晰;這分明清晰,多少也是由于他不亂用‘的’‘底’‘地’三個字。”在文章的結尾,東聲感慨“我國文字歷來沒有所謂Grammar之說”,雖然有語言學家已經規定了“的”“底”“地”的用途,“各著作家未必全按著實用”,巴金的可貴不在于完全按照語法學家的規定使用“的”“底”“地”,而是能夠“在他一部整個的作品中保守著個人用字的習慣”。高植《與從文論標點與“之底地的”》中也談到了巴金創作中的這一語法特點,例證是巴金自己的話:“前一時期的白話文中還常見到‘之’字,近來是漸漸少用了,而代替‘之’字的是‘的’字。不過有的時候為著方便及習慣起見,還有用‘之’字的地方。‘底,地,的’是很有人用得很嚴格的。巴金有一次在夫子廟吃茶,他說他用這三個助詞是有分別的,凡是形容詞下都用的,副詞下都用地,領屬詞下都用底。施蟄存也這樣用。有一次和郁達夫說到這事,他說他只用‘的’字,別的都不用。這都可以從各人的文章中看出的。”曾和郁達夫同學的徐志摩也是只用“的”字,耳熟能詳的詩句如“翩翩的在半空里瀟灑”、“輕輕的我走了”等,都是在該用“地”的地方用了“的”字。無論是區別使用“的底地得”,還是單用“的”字,現代漢語中的許多相關用法都是歐化的結果,只是區別使用的歐化色彩更為明顯,相對來說也更吻合漢語表達現代化的趨勢和想象。
郁達夫和徐志摩都曾長期留學國外,深受外國文化與文學的影響,他們的翻譯和創作卻都不區分“的底地得”。郭沫若與郁達夫一樣長期留學日本,所接受的日本“大高”系統的外語學習應該相似,他們后來又一起組織了創造社,文學上的興趣愛好很接近,但是郭沫若的翻譯和創作卻與郁達夫不同,很注意區分“的底地得”。郭沫若、巴金、徐志摩、郁達夫都是熱情洋溢的現代作家,個性與筆觸都帶有浪漫的色彩,但是在“的底地得”的區別使用上卻是截然不同的兩派。但是文學史論著的簡略敘述遮蔽了風格相似的作家們語言使用上的細微差異,使得像郭沫若這樣的作家最容易被誤讀錯讀。顧彬指出郭沫若可能是“通過翻譯找到自己的話語”,例證是人們熟知的《天狗》中的句型“我是……”顧彬的思路并無特別之處,早就有人談到過翻譯與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關系。從翻譯的角度審視郭沫若文學語言的生成問題這一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僅從“我是……”這樣的句型對照入手,不過是重復強化人們已有的對郭沫若單調夸張的表現手法的認知,若是研究者們能夠更多地從“的底地得”分用等方面思考翻譯之于郭沫若文學語言的生成,挖掘郭沫若文學語言使用上細膩嚴謹的一面,才能真正全面地認識郭沫若文學語言的生成及使用問題。
郭沫若的新詩創作以“亂寫”聞名,但那是“很不易得”的“亂寫”,屬于天才的亂蹈。亂蹈往往給人以粗枝大葉的印象,實則有細膩嚴謹的底色,嚴謹細膩最為重要的一個表現,便是“的底地得”的區別性使用。聞一多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這“新”不僅表現在詩的意象上,也表現在文字語法上,如“的底地得”的區別性使用在《女神》中就已經相當“分明清晰”。《天狗》一詩使用了“底”、“地”、“的”三種語助詞,“底”用于領屬詞下,“地”用在副詞下,“的”用于所有格,區別非常清晰。《筆立山頭展望》中對“底”、“的”的區別性使用也很嚴格。當然,也有些詩篇全部都用“的”字,極少數詩篇語助詞的區別性使用有些亂,如《雪朝》中的詩句:“大自然的雄渾喲!/大自然底symphony 喲!”“雄渾”與“symphony”雖有不同,但以“的”與“底”的分用顯示其間的差異,語法區分度有些勉強,類似這種因對象本身的區別度不明顯帶來的亂用問題,嚴格來說并不能夠視為使用者無標準亂用語助詞。
不可否認,《女神》集中不同篇目之間的使用規則還不能做到完全統一,這可能是郭沫若尚在區別使用與合用之間搖擺的表現。與《女神》中的詩篇相比,《少年維特之煩惱》譯文中的區別性使用相當規范,“的底地得”的區別性使用表明郭沫若的新詩語言有著嚴謹細膩的內在追求。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于1922 年,巴金的小說《家》1931 年連載于《時報》,1933 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前者比后者早問世十年左右。就“的底地得”區別性使用而言,郭沫若是一位先行者;當人們將巴金的《家》作為語法分明的典范時,也應該知道更早問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表現出同樣嚴格的語法規范。以“亂寫”聞名于世的郭沫若,也是創造和遵循現代Grammar 的作家,他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實踐在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豐
⑥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創造周報》1923 年6 月3 日第4 號。富和推動著文學漢語的現代性想象。
一、《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地、底、得
巴金的小說《家》嚴格地區分使用語助詞的、地、底,而郭沫若在《少年維特之煩惱》譯文中區別使用的語助詞不僅有的、地、底,還有得、之兩個語助詞。在現代中國文壇上,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在的、地、底、得等語助詞的使用方面,比一些討論“的”“底”“地”用法的專門的文字還要豐富和明晰。
1943 年,呂湘著文指出了語助詞t?使用的五種類型:
a.連接表領屬的名詞或代詞于名詞;作用類似歐洲語言的名詞及代詞的領格尾變及某一類介詞。例如“我的書”,“我哥哥的書”。
b.連接形容詞于名詞;作用類似歐語的形容詞尾及某一類介詞。例如“淺近的書”,“薄薄的書”。
c.連接由動詞或連帶其起詞及止詞組成的形容詞于名詞;作用類似歐語的分詞尾變及接續代詞。例如“我看的書”。
d.連接前置副詞于動詞或形容詞;作用類似歐語的副詞語尾。例如“慢慢的讀”,“用心的讀”。
e.連接(1)后置副詞或(2)表程度與效果的小句于動詞或形容詞;后者與歐語的某一類連詞相似,前者常無相當的語法機構。例如“好的很”,“讀的慢”。
上述五種類型,是語法學家做出的區分,在現代文學發生期的文學創作中,人們對語助詞的使用千差萬別。“在‘的’字還沒有通行的時期,除e項作‘得’外,其余分用‘底’‘地’二字。”呂湘認為,20 世紀40 年代已經是“的”字通行的時期,而在之前則有一個“分用”語助詞的、地、底、得的時期。“分用”起于何時?何晚成認為:“‘的底地’的劃分,大約是在五四時代由《學燈》諸先生提了出來的罷。”語助詞“地”、“的”、“底”區別使用的提出,與新式標點符號的規范使用,都是在“五四時代”,但是新式標點很快由教育部頒布命令要求統一規范使用。朱實說:“新式標點符號,自從民國八年由胡博士等六人具名呈請教育部頒行全國以來,久矣通行四海之內。”語助詞的區別使用雖然提了出來,卻一直沒有成為強制規范使用的對象,雖然“久矣通行四海之內”,卻并沒有成為作家們共同遵循的語言標準。
唐宋時期“底”“地”已出現在漢語表達中:“現在拿加詞的等級來區分的,加詞加于或可加于名詞之上,我們就說他本身是形容詞,后面用‘的’;加詞不加于或不能加于名詞之上,我們就說他是副詞,后面用‘地’,但在唐宋時代,‘地’字也用于第一類加詞之后。”也就是說,唐宋時期雖然也區別使用語助詞“底”“地”,但是區別使用的方式與現代漢語不同,現代漢語中語助詞的、地、底、得的區別使用嚴格來說始于“五四時代”。“五四”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語助詞的、地、底、得的使用又經歷了區別使用與合用等不同的“時期”。從語助詞的、地、底、得使用的歷史進程來看,郭沫若《女神》中詩篇的創作及《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翻譯皆在“五四時代”,這些作品都清晰地區分使用語助詞的、地、底、得,是“五四時代”漢語現代性想象最理想的實踐的產物。
《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書信有長有短,有的長于敘事,有的長于寫景,在語助詞的、地、底、得的區別使用方面各有不同。其中,最為密集且變化多樣地使用語助詞的、地、底、得的,是1771 年5月10 日的書信:
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支配了我全部的靈魂,就好像我所專心一意領略著的這甘美的春晨一樣。我在此獨樂我生,此地正是為我這樣的靈魂造下的。我真幸福,我友,我全然忘機于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我現在不能畫,不能畫一筆,但我的畫家的生涯從來不會有這一刻的偉大。當那秀美的山谷在我周圍蒸騰,杲杲的太陽照在濃蔭沒破的森林上,只有二三光線偷入林內的圣地來時,我便睡在溪旁的深草中,地上千萬種的細草更貼近地為我所注意;我的心上更貼切地感覺著草間小世界的嗡營,那不可數,不可窮狀的種種昆蟲蚊蚋,而我便感覺著那全能者底存在,他依著他的形態造成了我們的,我便感覺著那全仁者底呼息,他支持著我們漂浮在這永恒底歡樂之中的;啊,我的朋友。眼之周遭如昏黃時,世界環擁著我,天宇全入我心,如像畫中愛寵;我便常常焦心著想到:啊!我心中這么豐滿,這么溫慰地生動著的,我愿能把他再現出來,吹噓在紙上呀!我的心如像永遠之神底明鏡,畫紙也愿能如我的心之明鏡呀!——朋友!——但是我終不成功,我降服在這種風物底威嚴下了。
在上述這段譯文中,副詞下用“地”共有三處,它們分別是:
(1)更貼近地為我所注意
(2)更貼切地感覺著
(3)這么溫慰地生動著
習慣使用“之”,五處譯文分別是:
(1)我全然忘機于幽居底情趣之中
(2)眼之周遭如昏黃時
(3)他支持著我們漂浮在這永恒底歡樂之中的
(4)我的心如像永遠之神底明鏡
(5)畫紙也愿能如我的心之明鏡呀
凡是形容詞下都用“的”,但是“的”字在《少年維特之煩惱》譯文中的使用卻不僅限于形容詞下,如呂湘所說的a 類,即連接表領屬的名詞或代詞于名詞;作用類似歐洲語言的名詞及代詞的領格尾變及某一類介詞。c 類,即連接由動詞或連帶其起詞及止詞組成的形容詞于名詞,作用類似歐語的分詞尾變及接續代詞。A 類例子有:“我的藝術”、“我的心”、“我的朋友”、“他的形態”、“我們的”。C 類例子有:“領略著的這甘美的春晨”,第一個“的”字便是。
上述語助詞的區別性使用在其他作家筆下也較為常見,郭沫若的用法符合語法要求。但是,郭沫若對“底”的使用卻較為獨特。巴金自言他是在領屬詞下都用“底”,以小說《家》為例,東聲將其分為兩種情況:(A)凡是介詞,巴金都用“底”字,如“讀《托爾斯泰》底小說”。(B)用在人稱代詞名下,如“我有我底愛”、“你底英文說得很自然!”《少年維特之煩惱》中“底”字的使用顯然與巴金不同,郭沫若在人稱代詞名下一般都用“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用“底”的六處譯文分別是:
(1)我全然忘機于幽居底情趣之中
(2)我便感覺著那全能者底存在
(3)我便感覺著那全仁者底呼息
(4)我的心如像永遠之神底明鏡
(5)他支持著我們漂浮在這永恒底歡樂之中的
(6)我降服在這種風物底威嚴下了
六處譯文,(1)(4)(5)(6)大致可以視為一類,類似于東聲所說的介詞下使用“底”的情況。(2)和(3)可歸為一類,是所有格的標志,表示領屬關系。但是,郭沫若也用“我的”、“他的”表達所有格與領屬關系,并不像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的’字與‘底’字雖都是形容名詞的,‘底’字卻只限定用于所有格……‘底’字除了所有格以外,絕不能用,這是‘的’字與‘底’字的區別。”上面第五例句中的“底”字顯然不是用于所有格,“永恒”是形容詞,現在一般說“永恒的歡樂”,如果說“底”連接的是前面的“這永恒”,“這永恒”固然不是形容詞,但是“這永恒”與“歡樂”之間仍不宜理解為領屬關系。概言之,便是郭沫若在譯文中有意區別使用了幾個語助詞,這種區別性使用大部分都有語法依據,也有一些用法只有相對意義上的區別,并不吻合一般的語法規定性。如果說郭沫若譯文中“之”字的使用源自習慣,“底”字的使用表現的則是譯者的語感,雖然其中有語法上區別使用的考慮,但是這種區別使用的判斷標準更多地是語感,而不是明確的語法規則。
二、語助詞的區別使用與文學漢語的現代想象
翻譯應求信達雅,就語言本身來說,求信就必然要求語助詞的區分使用,不分的、底、地、得,原文中的一些語感和關系就沒有辦法恰到好處地呈現出來,所以呂湘指出,“比較歐化的語體文,尤其是翻譯文中,‘的’‘底’之分很有用處。”從翻譯到創作,語助詞區別使用的源頭是西方語言。對于的、底、地、得的區別使用,何晚成說:“在文學界,多數作家們往往有意識的不愿意去區別它。”這是因為,“把‘的’當作形容詞的語尾,拿‘底’字來與介詞of 或所有格相配,把‘地’字當作副詞語尾,這完全出于西洋文法的摹仿,一點也不合于中國文法構造的。”嚴格地區別使用的、底、地、得等語助詞,就意味著摹仿西洋文法,也就是歐化;不主張區別使用的、底、地、得等語助詞,往往就是堅持中國文法,或者說不愿意改變已經習慣了的舊有的中國文法。因此,語助詞的區別使用問題也就直接影響到文學漢語的現代性想象。
“的”“底”“地”“得”應該區別使用還是應該合用,在現代中國曾一度引發熱議。“大凡主張分的,理由是為了精密;主張合的,是為了簡便和易學。”許欽文在《“的”“底”“地”和“得”用法簡說》中指出:“文言文固然不用說,的,底,地和得這四個字,如今一般通俗的白話文,總只泥用一個的字;實在也沒有詳細區別的必要。可是討論高深的學術,需要精密的語體文,如果不分用,就要弄不清楚了。”傅斯年說:“語言是表現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現語言的器具。惟其都是器具,所以都要求個方便。”若只是為了“求個方便”,自然是一“的”到底更方便。簡單易學是大眾化的需要,精密卻是科學與民主的需要,漢語的現代化進程緣于啟蒙的需要,啟蒙需要大眾化,而啟蒙的理想便是實現科學與民主。因此,語助詞的區別使用所呈現的文學漢語的現代想象,不僅是選擇西洋文法還是中國文法的問題,也隱含著現代化想象及其實踐過程內在的矛盾性。
中國文法也區別使用語助詞,但是現代文法與古代文法并不相同。“古代以后面有無名詞來分別‘之’和‘者’,中世以前面的詞為區別性抑描寫性分別‘底’和‘地’,現代的人又拿前面的詞為形容詞性(可加于名詞者)抑副詞性(不可加于名詞者)來分別‘的’和‘地’。”嚴格地區別使用語助詞是現代語法的追求,其動因則是為了追求表達上的精密。精密被認為是西方語言的特性,正是中國古文應該學習的地方。胡適認為傳統漢語“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復雜的關系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歐洲各種文字之嚴整和細密,是我們的白話文和文言都望塵莫及的”,因此歐化是“洗練我們幾千年來一貫相承的籠統模糊的頭腦”的捷徑。徐志摩在《征譯詩啟》中呼吁:“我們所期望的是要認真的翻譯研究中國文字解放后表現細密的思想與有法度的聲調與音節之可能,研究這些新發現的、達意的工具究竟有什么程度的彈力性與柔韌性與一般的應變性,究竟比我們舊有方式是如何的各別,如其較為優勝,優勝在哪里?”署名“某某”的《的底地三字的用法》一文指出,許多努力于新文學的人都很輕易用錯這三個字,“以致影響了更多的文字的完整”。“文字的完整”,這是在現代邏輯基礎上對現代漢語提出的要求。錫朋在《“的”“底”“地”底用法》中說:“分化有一種好處,就是一望‘的’‘底’‘地’,就知道形容詞介詞副詞的區別。分化也有一種壞處,就是不懂文法的人,根本形容詞介詞副詞都不懂,還談得上‘的’‘底’‘地’么?假如替三四年級小學生講這種分化‘的’‘底’‘地’的文章,豈不冤哉枉也?”看似分說了分化的好處和壞處,實際上卻是將壞處歸因于用者的水平低,其實還是強調分化好。
伯攸在《編輯室談話》中說:“‘的’‘底’‘地’三字,我們本來只用一個‘的’字的;后來因為在句子底構造上,往往發生了困難,所以自今年起,才完全采用了。”這就從實踐的角度為語助詞的區別使用提供了佐證。郭沫若說:“‘五四’運動以后,產生了白話文。現在白話文的力量站在主流。檢查社會上一切的文字,文言文雖然還存在著,不過白話文的勢力是蓬蓬勃勃的。怎么會發生這種變革?社會使然。中國社會到近代來,已由封建制度逐漸蛻變。封建時代表示生活情形的文言文不適用于現在了。文言文不能用來作為表示現在生活上的工具了。其原因是固定的文言文,不能把活鮮鮮的生活描寫出來。生活與文學是不能分開的。‘五四’運動的主因,就在這個地方。”語言是表現生活的工具,文言文不能描寫“活鮮鮮”的生活,白話文的產生乃是因為生活的需要,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表達精密的要求。
文學創作的語言追求的精密更準確地來說應該是精微。為了能夠更貼切地表達心靈和思想細微的顫動,作家需要不停地微調語言以便能夠突破詞不達意的問題,這就需要精微地運用語詞。精微,也就意味著選擇恰當的字詞使之出現在恰當的位置上。在不同的位置上使用不同的語詞,當這些位置關系相近,字詞的選擇也就較為相似,相似而不同的字詞出現的頻率高,也就意味著作家在語言的運用方面較為豐富。就語助詞的使用而言,區別性地使用的、底、地、得就比單一使用“的”給人語言運用更復雜和豐富的感覺。當然,復雜與變化不是區別使用語助詞的、底、地、得的目的,而是語言表達清晰明確追求的外在表現。形式上的清晰明確并不等同于思想情感上的清晰明確,但是復雜的思想情感一般來說不能通過簡單的句子傳達出來。
將表達的精密與語言的歐化聯系起來,而將傳統漢語判斷為不精密,這一現代性想象的產生自然是外來影響的結果,正如何晚成指出的那樣:“在人們的頭腦已經受西洋文法浸蝕的非常利害的時候,如果主張把‘的’字分成‘的底地’,只要一說,就有許多讀了三天半洋文的聞聲響應。”“許多讀了三天半洋文的”自然是夸張的說法,事實是現代文壇的形成有賴于外國留學生群體,留日群體形成的創造社、英美留學生形成的新月社等都是現代文壇重鎮,他們中大多數成員都有十年以上的海外留學體驗。就他們海外接受的教育而言,把“的”字分成“的底地”更多地是出于洋文學習的自然影響,若說有“聞聲響應”的情況,大多也都是自己想到卻沒有說出,等到有人倡導時自然也就同聲相和。何晚成秉承漢語本位主義,不贊成區別使用“的”“底”“地”,“我主張在翻譯社會科學的時候也只用一個‘的’字。至多再添上一個‘地’字。照我的經驗,如果一個句子太長,里面包含‘的’字到三四個以上的時候,縱然把‘的’字分做‘的底地’幾樣寫法,也不見得會使句子更容易了解一點。我希望從事翻譯的人們要根本了解中國語的構造和西洋話的構造不同,不能逐字直譯;必須把長的句子設法截斷,譯成普通的中國話。”
對于何晚成秉持的那種觀念,郭沫若自然不贊成。郭沫若在《怎樣運用文學的語言》中說:“語言除掉意義之外,應該要追求它的色彩,聲調,感觸。同意的語言或字面有陰暗、硬軟、響亮與沉抑的區別。要在適當的地方用有適當感觸的字……形容詞宜少用,的的的一長串的句法最宜忌避。句調不宜太長,太長了使人的注意力分散,得不出鮮明的印象。”也就是說,語言的使用除了固定的語法外,還要追求語感,不能一刀切地追求語法使用自始至終不變,若是“的的的一長串”,讀起來便少了許多色彩和感觸。這一點也早已被人指出。“在中文里,副詞下可以不加字。我們可以寫‘慢慢地走’,也說‘慢慢走’。形容詞有時加‘的’反不好,‘紅花’便比‘紅的花’好。但有時為了音和氣的關系,還是要加‘的’。‘淡紅的花’便比‘淡紅花’好聽一點,舒服一點。”用不用“的”,有時候并不是為了語法上的需要,而是為了照顧語感,為了“好聽一點,舒服一點”,而“好聽”與“舒服”是沒有確切的標準的,需要使用者自身能夠感知語詞的色彩與聲調。高植在文章中寫到“……在形容詞和領屬詞之下”時,對“之下”二字做了說明:“這里‘之下’似乎比‘的下面’好一點,這是習慣上用‘之’的地方。”“習慣”,也就是索緒爾所說的語言的約定俗成性,我們習慣了說“在……之上”、“在……之中”、“在……之下”,這里的“之”并不需要用現代漢語里的“的”替代。
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靈活地運用的、底、地等語助詞,與其他譯者相比,語助詞的使用顯得較為豐富,“的的的一長串的句法”也較少。
郭沫若和楊武能兩位譯者翻譯的1771 年5月10 日信簡所用語助詞數據如下:

郭沫若譯文運用了“的”“底”“之”“地”四種語助詞,共計40 次。其中,“的”字的數量約占機統總字數的5.9%,四種語助詞約占機統總字數的9.09%。楊武能譯文運用了“的”“得”“之”“地”四種語助詞,共計42 次。其中,“的”字的數量約占機統總字數的7.14%,約占機統總字數的8.333%。從語助詞使用總量及種類上來看,兩位譯者非常接近,郭沫若為四種40 次,楊武能為四種42 次。差異主要出現在“的”的使用頻次,以及“底”和“之”兩個詞的使用。由統計數據可知,郭沫若有意減少了“的”字的使用頻率,在一些可以使用“的”的地方,使用了“底”與“之”。
1771 年5 月4 日信簡所用語助詞數據如下:

1771 年8 月15 日信簡所用語助詞數據如下:

觀察上述三個表格,通過對譯文進行分段統計,可以發現以下幾個事實:
1.郭沫若譯文用字較少,但并不總是比楊武能的譯文所用字數少,如《少年維特之煩惱》的開篇即1771 年5 月4 日信簡。
2.郭沫若譯文所用語助詞總數量與楊武能譯文大體持平。
3.郭沫若譯文所用語助詞類別比楊武能多,楊武能譯文中出現的四種語助詞的、之、地、得,郭沫若譯文中都用到過,而郭沫若譯文中使用的“底”字在楊武能譯文中卻沒有。
4.郭沫若譯文使用“的”的總體頻率低于楊武能譯文,有些文段兩位譯者的譯文大體持平;郭沫若譯文使用“之”的頻率明顯高于楊武能譯文。
5.郭沫若譯文顯然區分使用了的、底、地、得等語助詞,與晚幾十年出現的楊武能譯文中語助詞的區別使用相比,在區別使用的嚴格程度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文所統計的只是《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三段譯文,以三段文字概言整部譯作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筆者在隨機抽樣之外也觀察了其他譯文段落,大體都符合通過上述三個表格得出來的結論。如果有學者以大數據分析的方式對郭沫若的譯文進行更科學的徹底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不會有異。郭沫若在翻譯實踐中的確貫徹了他不連續使用“的”的觀念,有意識地通過“底”、“之”的使用分擔“的”字的功能。當然,這種分擔不是通過譯者自己獨斷式的語法規定實現的,而是將傳統漢語的語法與西洋語法有機結合起來,具體地來說便是郭沫若用“底”和“之”字分擔“的”字的功能時,主要表現在譯文中的長句/復雜句里,例如下面幾句譯文:
1.我全然忘機于幽居底情趣之中
2.地上千萬種的細草更貼近地為我所注意
3.他支持著我們漂浮在這永恒底歡樂之中的
4.我的心如像永遠之神底明鏡
5.畫紙也愿能如我的心之明鏡呀
“之”字的運用,是文言語法的遺留,郭沫若在譯文中的運用自然如意,渾然沒有李金發詩歌創作中“之”字給人的那種生硬感。歐化趨新的同時也能有機地汲取傳統文化的因素,這正是郭沫若球形天才的典型特征之一。
三、保存中國文化的精粹
郭沫若將人們與新文字的關系分為三類:已經懂得新文字的人、對新文字有理解實際卻不懂也不能純熟運用的人、根本不懂新文字的人,將自己定位為第二類,即“贊成新文字而又不能運用新文字的”,認為這一類人“在目前應該放下苦工去加緊學習。要使自己成為一個運動專家,擔負得起推行新文字的任務。”此外,“每一個懂得新文字的人”都要“利用一切的時機,利用一切的地點”,進行“新文字的創生和推行運動”。在郭沫若看來,懂得新文字和純熟運用新文字是兩回事,新文字的真正成功既需要人們懂又需要人們能夠純熟地運用,同時還要改變對舊文字的看法,應該研究舊文字,“有舊文字的原封,還有新文字的改裝”,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地保存中國文化的精髓。郭沫若說他自己“對于新文字有理解,然而實際上并不懂,不能純熟運用”,這是自謙。郭沫若并不是研究新文字的專家,僅就新文學創作與文學翻譯而言,郭沫若對新文字運用之純熟,不輸任何現代作家和翻譯家。僅就“的”“底”“地”“得”幾個語助詞的使用而言,郭沫若在《少年維特之煩惱》譯文中使用之分明清晰,與巴金小說《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何看待郭沫若譯文中語助詞使用中表現出來的“原封”與“改裝”?如果說“改裝”表現出來的是現代性,是“五四時代”的新的精神追求,“原封”是否便體現了郭沫若譯文中傳統的一面,是舊文化的遺留?“原封”與“改裝”的碰撞,呈現出來的實際是過渡時代新舊兩種文化兩種語言的碰撞。郭沫若的文學翻譯是在“五四時代”的大背景下進行的,自然不能擺脫大的時代背景的影響,但是郭沫若并不像其他一些新知識分子那樣強調與傳統的斷裂,郭沫若強調中國文化原本充滿了“動”的精神,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恢復被遮蔽了的“動”的傳統文化精神。郭沫若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漢語有自身的理解,他的譯文表現出來的“原封”與“改裝”,便是郭沫若對文學漢語的現代想象。
如果說區別使用的、底、地、得等語助詞是《少年維特之煩惱》譯文語言“改裝”的表現,從傳統文學作品中選擇譯詞就是譯文語言“原裝”的最好明證。為了討論的方便起見,以本文前面引用的1771 年5 月10 日信簡中的文字為例,粗略統計其中使用的“原裝”譯詞如下:
1.“昆蟲蚊蚋”:清李漁《閑情偶寄·頤養·行樂》:“時蚊蚋之繁,倍于今夕,聽其自嚙,欲稍稍規避而不能。”
2.“忘機”:唐朝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3.“幽居”:唐代韋應物《幽居》:“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
4.“杲杲”:《詩經·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5.“環擁”:蘇軾《神女廟》:“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奸。”
6.“愛寵”:《漢書·杜欽傳》:“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于一人。”
7.“溫慰”:《二刻拍案驚奇》卷五:“那時留了真珠姬,好言溫慰得熟分。”
8.“吹噓”:比喻用力極小而成大事。明朝張四維《雙烈記·虜驕》:“吹噓定魯齊,談笑平吳楚。”
9.“明鏡”:唐李白《將進酒》:“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
10.“風物”:晉代陶潛《游斜川》詩序:“天氣澄和,風物閑美。”
上述十個“原裝”譯詞,在傳統文學中并不罕見,筆者隨手給的出處也都不偏僻。有些“原裝”語詞也出現在同時代其他作家的筆下,如冰心在《寄小讀者·通訊六》中寫道:“愿上帝無私照臨的愛光,永遠包圍著我們,永遠溫慰著我們。”冰心將舊語詞恰到好處融入白話文的創作中,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也是如此,“《離騷》的句子可以寫在郭沫若氏的新詩里,蘇東坡的詞句自然也可以寫在冰心女士的新詩里了。”廢名談的是冰心和郭沫若的新詩創作,用之于郭沫若的文學翻譯也很恰切。在郭沫若的文學翻譯中,傳統文學中的“原裝”詞句隨處可見。《少年維特之煩惱》中1771 年5 月10 日信簡的機統字數為440 字,上述十個“原裝”詞共計22 個字,所占比例為5%。這個比例似乎并不很高,若是考慮到這些語詞在譯文表述中的中心地位,這些“原裝”語詞在譯文中的地位和作用遠超出5%的占比。“原裝”語詞并非生硬地鑲嵌在《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譯文中,而是與歐化語法等水乳交融,表現了譯者融匯中西駕馭新舊的超強語言能力。總的來說,《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翻譯完美地體現了郭沫若對文學語言“原封”與“改裝”的追求,簡單地來說,便是傳統文學語詞的選擇體現的是“原封”,的、地、底等語助詞的區別使用體現的則是“改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