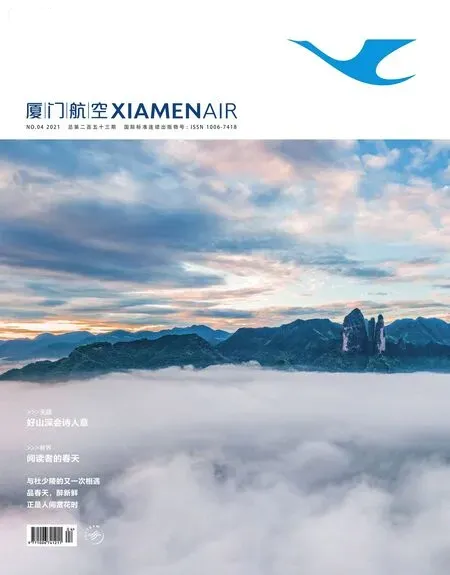悅心之“讀”
撰文_呂慈航
我讀故我在
欠伸展肢體,吟詠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愿為世儒。
——唐·柳宗元《讀書》
猶記得高中時代,在寄宿制的重點高中里日復一日地重復著教室、食堂與宿舍三點一線的日常,書架里大部分是做完或沒做完的習題和教輔材料,對于文科生來說,唯一的“小確幸”,大概就是這些沒什么溫度與趣味的教材里,能有那么一點空間藏進幾本真心想讀的“閑書”。
所謂“閑書”,不知對如今的青少年來說是否聽來陌生。
他們中間的相當一部分人至少從小學開始就精通各項流行電子商品的“十八般武藝”,襯得我這“老阿姨”十足落伍,像是活該被拍死的“前浪”,畢竟我在他們這個歲數(shù),實在沒這福氣。雖說家境不差,但彼時網(wǎng)絡的各方面水平實在與今時盛況不可同日而語,能購置電腦的家庭也不多,手機不過滿足通話與短信需要,去網(wǎng)吧就更是奢求,于是相對而言,最能讓我舒心愉悅的享受,便是閱讀。因為形成了習慣,甚至比較早地就實現(xiàn)了不用看注音版讀物,并且用勝過身邊同齡人的知識面實現(xiàn)一定程度上的優(yōu)越感。
說是有優(yōu)越感,倒也不是為了這點優(yōu)越感才去閱讀,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不復雜,所以感情也往往純粹,因為喜歡,因為想讀,所以就持之以恒了,就像吃飯喝水一樣自然。
不少的同齡人跟我所見略同,不過閱讀是一種無法不產(chǎn)生評價與接受評價的行為,因此也就有了一個常見的“罪名”——看“閑書”。
既不是習題教材,也不是必讀書目,那自然就是“閑書”了。如果把攻讀課業(yè)的時間拿來看“閑書”,哪怕不是顯而易見的漫畫或小人書,只是某些不被認為對學業(yè)有益的作者,自然問題就大了,隨之而來的就是沒收、銷毀與責罰。但是,“閑書”真的就有原罪嗎?
“看了之后會不會很想去墨脫?”在我借閱了舍友的《蓮花》后,她笑著這么問我。重點高中繁重的作業(yè)與強大的升學壓力之下,難得的喘息之機就是與好友共享愛好上的心得,而閱讀體驗無疑是最快捷且有效的方式。當然不管是主觀還是客觀原因,我都不可能真的去墨脫,尤其是像書中所寫,背上厚重的行李,穿過螞蟥的包圍,忍受著夜里的低溫,但投入身心地閱讀時,就仿佛身臨其境,于是就能知曉,視野里其實并不是漫無邊際的題海。
因此受到影響,開始搜集安妮寶貝的其他作品,珍而重之地放在枕下,睡前必須讀上幾頁。即便是面對關(guān)系并不好的同學,看到她書架上也有一排的安妮寶貝,再怎么緊張的關(guān)系下也會不由自主地想,原來她與我并非真的水火不容。偶爾觀察,發(fā)現(xiàn)其他人的書架上還藏有落落、七堇年甚至如今被各路群嘲的郭敬明,當然少不了被有所察覺的老師耳提面命——“不要學那種寫法!作文分數(shù)不會提高的!”
可是看這樣的書,本就不是為了作文分數(shù),依然只是喜歡,只是想讀,讀后身心舒暢,精神煥發(fā),才有余力繼續(xù)面對現(xiàn)實的壓力。
如今我以文字為業(yè),為了工作的閱讀其實也不能隨心所欲,曾經(jīng)想都沒想過的工具書和論文集反而成了閱讀的常態(tài)。見識與閱歷雖有限,但也確實在不斷積累充實,于是回看過去,就會看到當年的自己其實對著不少矯情套路的文字“為賦新詞強說愁”,自覺驚天動地般感動只因沒見過世面。
然而,不成熟有成熟的必要,不合理的觀念也需要糾正,但閱讀時發(fā)自內(nèi)心的喜悅,卻很難說什么對錯。

如果閱讀觸動了內(nèi)心,讓人真切地為獲得認知而欣喜,不管是對世界,對他人還是對自己,那么我認為這就是閱讀的意義所在——閱讀,只是悅心之“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