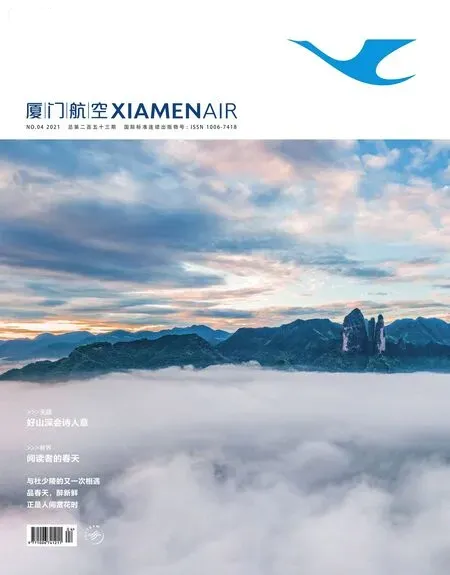天心波遠付瑤琴
撰文_曹放

宋 歐陽修《集古錄跋》(局部)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關山排闥,白云漸遠,天地同流……春夜,又一次品讀《歐陽文忠公文集》,我的腦海里星光無際……梁漱溟先生認為:世界有三大文化體系,一是西洋文化體系,二是印度與伊斯蘭文化體系,三是中華文化體系。陳寅恪先生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蘇東坡是中華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林語堂先生評價:這樣的人物“不可無一,難能有二”……是誰扛鼎起了中華文化的造極大宋?是誰聚匯起了北宋一代的文化精英?是誰托舉起了蘇東坡的光耀千古?哦,歐陽修!
毫無疑問,歐陽修的詩詞文章,堪稱一代宗師。他的散文《朋黨論》《醉翁亭記》,他的史著《新唐書》《新五代史》,他的詩詞“庭院深深深幾許”“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他的書法《灼艾帖》《夜宿中書東閣》,都千古流芳。然而,對于整個中華文化體系的貢獻來說,我以為,歐陽修最大的功績就是:以目光如炬的慧眼發現人才,以云水滔滔的襟懷涵養人才。由此,中華文化才得以造極于趙宋之世;由此,才有了蘇東坡的脫穎而出光照千古。
公元1057年,時年五十歲的歐陽修被提拔為禮部貢舉的主考官,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這開始了他伯樂生涯的黃金時期。“哇,好!”一份試卷,歐陽修擊節贊賞。寫得灑脫豪放,他準備報送皇帝點其為狀元。哎,會不會是弟子曾鞏所寫呢?他反復看了幾遍這份密封了姓名的試卷,生怕真的是曾鞏所寫,點為狀元,別人會說自己徇私,想來想去,就給了個第二名。欽定,啟封,唱名,哈哈,原來是眉山蘇軾!歐陽修極為振奮,同時又為沒有點他為狀元而大為后悔。“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這是歐陽修對老友梅堯臣所述。他這“放他出一頭地”,是為中華文化群星璀璨的星空,放射出了一顆北斗巨星……
早在公元1044年,歐陽修就通過弟子曾鞏知道了王安石,知道他才華橫溢,“古今不常有”。怎奈當時的歐陽修被貶滁州,呈遞朝廷的幾次推薦信都石沉大海。公元1051年,歐陽修起復回朝,隨即力薦王安石,清高的王安石卻以祖母年高為由推辭不受。歐陽修親自找到王安石,反復勸說,王安石這才答應出仕為官,由此開始了他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
唐宋八大家,除唐代韓愈、柳宗元和他歐陽修本人外,另外五位,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都是歐陽修發現舉薦的千里馬。由此,稱歐陽修是古今第一伯樂,可謂實至名歸。這也不妨反向推論,如果沒有歐陽修,中華文化的星空,就未必會有蘇軾的光耀千秋,就未必會有趙宋之世的登峰造極。“器質之高遠,智識之深厚,而輔學術之精微……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這是王安石對歐陽修的稱贊。“歐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云馭風、歷五岳而跨滄海也。”這是蘇軾拜會西湖高僧惠勤時對歐陽修的共同禮贊。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必須衷心地拜謝歐陽修。可以說,是歐陽修,鋪展開了大宋一代中華文化的云蒸霞蔚。
多少回,中夜里,我回味著歐陽修的風儀行止,那一份仗義直行、剛勁自若,那一份知進知退、寬簡自持,那一份不慕榮華、清正自守。歐陽修,真個是俗世中的圣賢!他最打動我的,是他人格的剛正與中道。
范仲淹正直敢言,但官場的命運卻因此跌宕迂回。每到險要處,并無權勢的歐陽修都不計利害,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公元1036年,范仲淹就朝廷怎樣公正用人直陳己見,開罪了當朝權貴,被貶官外放。身為諫官的高若訥,非但不據實進諫,反而落井下石。歐陽修怒發沖冠,慷慨激昂寫下了著名的《與高司諫書》,怒斥其為“君子之賊”,諷刺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時年29 歲的歐陽修因此被加上“顯露朋黨之跡”的罪名,也被逐出京城,貶官外放為今湖北宜昌的“夷陵令”。公元1045年,厲行變法的范仲淹受到保守派政敵的誣陷,被罷免相位,新法也隨之廢止。這時,歐陽修又挺身而出,他“慨言上書”,為范仲淹辯護論理。由此,他再一次觸怒了當朝權貴,被借故下獄,接著又貶為滁州知州。歐陽修這樣的不計利害、匡扶正義,怎樣地令我敬重呀。然而,不止于此,更超乎其上的,是他既果敢同赴生死,更不求共享榮華。他與范仲淹之間“同其退,而不同其進”,就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道奪目高光。范仲淹年長歐陽修十八歲,他的仕宧生涯雖有多次跌宕迂回,也有多次春風得意。“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受命經略西北,抵御西夏外敵,范仲淹一時重權在握,他準備舉薦曾經患難相助的歐陽修同擔大任。歐陽修卻笑而推辭:“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歐陽修這段話語,閃耀著清正人格的光輝,這人情之間的淳厚與寬簡,是怎樣的山高水長呀!公元1046年,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或許是一個不應當被忽略的年份,因為,正是在這一年,一對肝膽相照的知已分別寫出了一篇光耀千古的散文:范仲淹,《岳陽樓記》;歐陽修,《醉翁亭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寫下這散文名篇的時刻,他倆正遭遇貶謫,但此心光明,憂樂同懷。
洞見人格的光輝,不僅是看他怎樣對待同道,而且也要看他怎樣對待曾有過結的同僚。歐陽修與陳執中的交集,將我對歐陽修人格的敬意引向了云水泱泱。陳執中,北宋一代名臣,他“事方嚴,少和裕,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而,他的從政觀念一直是維持祖制,反對變法,“尤惡士大夫之急進”。這樣,他與具有變法思想的歐陽修就一直格格不入。他在任陳州知州時,歐陽修自潁州往南京途徑陳州,曾欲往一會,陳執中卻拒而不見。當政敵操弄起歐陽修所謂的緋聞案時,身為宰相的陳執中也參與了火上澆油,巴不得審問出什么事端,好一舉擊垮歐陽修。然而宦海風波無定,許多年之后,在朝廷官員的彈劾與市井鄉野的責罵聲中,陳執中失勢了,皇上只好將他貶官外放。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回,自己落到了歐陽修手里。作為翰林學士的歐陽修,要為他擬定一份“制文”,這也就是對他的鑒定。令陳執中更加萬萬沒想到的是,歐陽修絲毫也沒有對他落井下石,而是秉持公正,給了他一通明快的贊美:“杜門卻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意思是說,陳執中關門閉戶,不喜應酬,善于避開權勢,遠離是非;處理事務專心致志,不因外界毀譽而更改主張。據《言行龜鑒》卷二記載:陳大驚喜,曰:與我相知甚深者,都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他馬上抄錄下來寄贈其門生,并感慨萬千:“吾恨不早識此人。”讀到這里,禁不住,我掩上書卷,抬眼眺望窗外,心中一片澄澈。一個古代士大夫,能夠讓與他有過過節的同僚乃至政敵,都心懷感恩地驚喜,“恨不早識此人”,那是懷有了怎樣的涵養與氣度啊!
春夜涳濛,歐陽修引領著我心神悠游:一千年過去了,中華文化,還能有那英才蔚起、俊采星馳的宏大氣象嗎?文人士子,還能有那剛勁自若、凜然挺挺的曠達瀟灑嗎?書林叢刊,還能有那吞吐萬象、獨抒性靈的錦繡文章嗎?
詩書輕掩駐光陰,
微火烹茶聽鳥吟。
一任年華隨逝水,
天心波遠付瑤琴。
辛丑春日,我寫下了這首小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