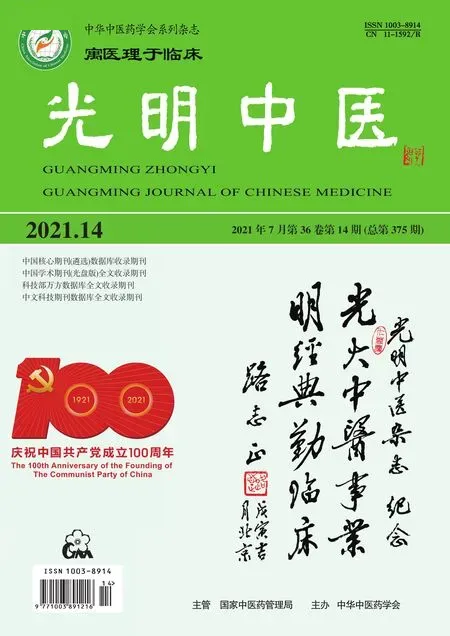益氣升陷法治療心律失常探究及臨床應用舉隅*
吳欣芳 許國磊
心律失常是臨床常見的心血管疾病并發(fā)癥,癥狀較輕者可感覺到胸悶、心悸,嚴重者可出現(xiàn)惡性心律失常甚至危及生命,現(xiàn)代醫(yī)學主張必要時可予抗心律失常藥物治療,但抗心律失常藥物存在諸多不良反應,臨床獲益非常有限,中醫(yī)無心律失常的記載,根據(jù)患者的癥狀,歸屬于“心悸”范疇,心悸病機復雜,中醫(yī)對于心悸的病因病機有著深刻的認識,目前認為其發(fā)病與心陽不振、心血虧虛、瘀血內(nèi)阻及陰陽失調(diào)等諸多因素有關,我們在臨床工作中發(fā)現(xiàn),部分心律失常患者在心律失常發(fā)作時常伴有胸悶、氣短等氣虛下陷的癥狀,對這部分患者采用益氣升陷法治療,能夠明顯地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臨床療效較好,本文對益氣升陷法的理論溯源進行梳理,對其在心律失常中的臨床應用及現(xiàn)代研究做了詳細論述,并列舉治療驗案1則,探討益氣升陷法臨床應用的可行性。
1 益氣升陷法理論溯源
益氣升陷法源自《黃帝內(nèi)經(jīng)》的氣機升降理論,是指應用補氣和升提的藥物,治療氣虛下陷證。金元時期,張元素在《黃帝內(nèi)經(jīng)》的基礎上,對益氣升陷理論做了進一步發(fā)展,并在治療上提出了“風升生”的理論,即應用風藥如防風、升麻、柴胡等起到升陽舉陷的作用。李東垣在繼承張元素的學術思想的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脾胃學說,在其論著《脾胃論》[1]中提出“大抵脾胃虛弱,陽氣不能生長”,主張“內(nèi)傷脾胃,百病由生”,治療“當升,當浮,使生長之氣旺”,首創(chuàng)了升陽舉陷法,并創(chuàng)制了一套補益脾胃、益氣升陽的方劑,方中善用升發(fā)脾陽的藥物以升舉中陽。清末民初著名醫(yī)家張錫純進一步發(fā)展了李東垣的益氣升陽舉陷理論,在《黃帝內(nèi)經(jīng)》的宗氣理論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充實與發(fā)展,在《醫(yī)學衷中參西錄》[2]中提出了大氣下陷理論,不僅描述了 “其病之現(xiàn)狀,有呼吸短氣者,有心中怔忡者……脈沉遲微弱,或參伍不調(diào)等大氣下陷證的臨床表現(xiàn),同時也創(chuàng)制了具有補益宗氣、升陽舉陷作用的升陷湯,治療“氣短不足以息,或努力呼吸時或氣息將停危在頃刻”的大氣下陷證,書中除了對大氣理論及升陷湯進行論述,同時也附有升陷湯治療大氣下陷證的醫(yī)案。以上為益氣升陷法的形成、發(fā)展過程,為其現(xiàn)代臨床應用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2 益氣升陷法在心律失常中的應用
臨床工作中發(fā)現(xiàn),氣虛下陷是心律失常的重要病機,脾氣虧虛,氣虛下陷,無力行血,血脈運行不暢而為此病,因此,益氣升陷法是治療氣虛下陷型心律失常的常用方法,而臨床常用的具有益氣升陷作用的方藥,根據(jù)其作用部位的不同,分為升舉中氣及升舉大氣藥物,分別用于中氣下陷證及大氣下陷證。
2.1 中氣下陷證患者有心悸的癥狀,常常同時伴有中氣下陷的癥狀:氣血生化乏源所致的氣短懶言、神疲乏力、四肢倦怠,重者出現(xiàn)頭暈目眩;脾失健運,完谷不化而出現(xiàn)的腹瀉、帶下病癥;脾虛升舉無力,內(nèi)臟不能得以升舉,出現(xiàn)脘腹墜脹,甚或脫肛、內(nèi)臟下垂等病癥,常見舌淡苔白雙寸脈弱。對這部分患者,臨床常用方劑包括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這2個方藥為李東垣所創(chuàng),均為治療氣虛下陷證方藥,補中益氣湯具有補益中氣、升陽舉陷的作用,臨床以少氣懶言、體倦乏力、脈虛弱無力為辨證要點。而升陽益胃湯具有益氣升陽,清熱除濕的作用,以肢體酸重、倦怠嗜臥、口干口苦及二便不調(diào)為辨證要點,臨床中又當加以甄別。
2.2 大氣下陷證心悸常常伴有呼吸氣短,上下之氣不相續(xù)接,胸悶、憋氣,甚者胸前有下墜感,窒悶似喘等大氣下陷的癥狀,脈象多為沉遲無力。臨床常用方劑為升陷湯。升陷湯出自《醫(yī)學衷中參西錄》,為張錫純基于“大氣下陷”理論所創(chuàng),方中重用生黃芪補氣,輔以桔梗、升麻、柴胡等風藥升陽舉陷,配知母涼潤,使升補而不偏于溫,是治療大氣下陷證的常用方劑,臨床應用以氣促急短,呼吸困難及脈象沉遲無力為辨證要點。
2.3 隨證加減方藥在臨床工作中,應用益氣升陷法治療心律失常,又應根據(jù)患者的癥狀,隨證加減,如患者合并痰濁閉阻而見形體肥胖、胸悶氣短且痰多者常配伍瓜蔞薤白半夏湯,以祛痰寬胸;如合并陰虛火旺而見五心煩熱、失眠者常常隨證配伍桂枝加龍骨牡蠣湯、黃連阿膠湯、交泰丸等交通心腎方藥;如合并心血瘀阻而見胸悶、胸痛,痛如針刺者常配伍血府逐瘀湯或丹參飲等活血化瘀方藥,如合并心陽虧虛而見面色蒼白,形寒肢冷者,常配伍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以振奮心陽,鎮(zhèn)驚安神;如合并水飲重而見頭暈、胸悶、痞滿或下肢浮腫者常配伍五苓散,以溫陽化氣,利濕行水。總之,臨床應根據(jù)患者的合并癥的不同而靈活加減應用。
3 益氣升陷法治療心律失常的現(xiàn)代研究
現(xiàn)代醫(yī)家亦重視氣虛下陷在疾病發(fā)病中的作用,關于“益氣升陷”法治療心律失常有較多的臨床研究,研究較多的方藥包括補中益氣湯及升陷湯。有研究表明補中益氣湯[3-5]治療竇性心動過緩,能夠提高心率,改善臨床癥狀,療效肯定。而孫曉等[6]通過臨床研究發(fā)現(xiàn),補中益氣湯治療房性早搏、室性早搏及房室交界性早搏有較好的臨床療效。升陷湯廣泛應用于各種心律失常的治療,臨床研究表明,升陷湯[7-10]治療陣發(fā)性室上性心動過速、病態(tài)竇房結綜合征、竇性心動過緩、室上性早搏以及心房顫動具有較好的臨床療效。而對于升陷湯治療心律失常的機制研究也有報道,張華敏等[10]通過動物實驗發(fā)現(xiàn)益氣升陷復方(升陷湯加味)能夠明顯縮短大鼠心律失常的持續(xù)時間,從而對室性早博、室性心動過速及心室顫動有抑制作用。
4 驗案舉隅
魏某,女,36歲,2018年4月3日初診。患者心悸反復發(fā)作2年,近1個月,因事務繁忙,心悸發(fā)作頻繁,且明顯較前加重,嚴重影響工作,曾于某醫(yī)院做心電圖提示頻發(fā)室性早搏,患者平素心悸,胸悶、氣短,困倦乏力,便溏,腰膝酸軟,易緊張,且手心多汗,失眠多夢,就診時,舌淡紅、苔薄白、脈浮緩無力,雙寸脈弱,辨證屬氣虛下陷,心腎不交,擬從補益中氣,交通心腎法治療。方藥:補中益氣湯合桂枝龍骨牡蠣湯加減:炙黃芪20 g,黨參20 g,炒白術15 g,陳皮10 g,升麻10 g,當歸10 g,柴胡15 g,桂枝10 g,白芍15 g,大棗20 g,生龍骨15 g,生牡蠣15 g,巴戟天15 g,山萸肉10 g,炙甘草 10 g。7劑,日1劑,水煎服。2018年4月12日二診,患者訴服藥后心悸好轉(zhuǎn),每日發(fā)作次數(shù)較前減少,偶有勞累后發(fā)作,汗出明顯減少,胸悶、憋氣好轉(zhuǎn),仍覺易疲勞,腰膝酸軟,睡眠欠佳,舌淡紅、苔薄白、脈沉細無力,守前方,加入酸棗仁20 g,五味子6 g,杜仲15 g。繼續(xù)服用14劑。2018年4月27日三診,患者心悸發(fā)作次數(shù)減少,睡眠改善,諸癥好轉(zhuǎn),繼續(xù)服用前方,2個月后隨訪,患者病情平穩(wěn),早搏偶有發(fā)作,生活及工作恢復正常。
按:本案患者為頻發(fā)室性早搏的青年女性,平素工作事務繁忙,思慮過度,憂思傷脾,脾虛運化不健,清陽不升,故平素易倦怠乏力,便溏腰墜,舌淡紅、苔薄白、脈沉細無力,考慮為氣虛下陷證,同時該患者易緊張,手心多汗,失眠多夢,為心腎不交所致,據(jù)癥舌脈,辨證為中氣不足,心腎不交,故給予補益中氣湯升舉中氣,同時配伍桂枝龍骨牡蠣湯以交通心腎,收斂固攝,服藥后患者癥狀明顯改善,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
5 小結
通過對文獻記載及臨床研究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益氣升陷法源于《黃帝內(nèi)經(jīng)》中相關理論,經(jīng)過后世醫(yī)家的發(fā)展,臨床應用范圍不斷擴大。氣虛下陷是心律失常的重要病機之一,益氣升陷法在心律失常的治療中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廣泛的臨床證據(jù),療效確切,廣泛應用于各種心律失常的治療,在臨床工作中,應用益氣升陷法治療心律失常,又應結合患者的伴隨癥狀的不同,辨為中氣下陷證和大氣下陷證,而分別采用升舉中氣及升舉大氣法進行治療,而對于合并其他證候者,又應隨證加減,靈活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