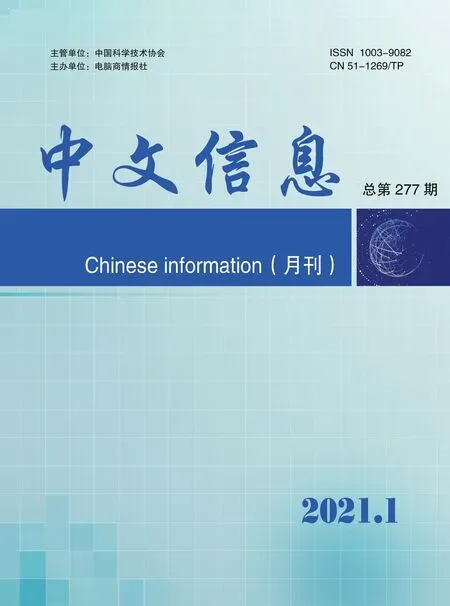隋朝印式對當代篆刻的啟示
(淄博啟夢苑教育培訓學校,山東 淄博 250301)
隋朝官印的形式不僅是對秦漢官印的延續,更是一種變革。它的出現和各個方面制度有關,也是由于前期已出現的印制形式遞變所引導出來的結果。雖然立國短暫,僅三十余年,所留印章不多。但是,其獨特的印學范式,在整個印學史中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一直影響后世。
一、印形的突變
隋朝官印在制度上承襲了北周制度,借助大一統的有利形勢,使印式趨于統一。秦、漢的官印,大小均在2.3——2.5厘米之間,并且都是陰文,主要是因為封泥的需要。北周官印大小方面一般比漢魏時偏大一些,“天元皇太后璽”金質,印高4.70厘米、長4.55厘米、寬4.45厘米,鑄于大象元年(579)。該璽對隋印印式有明顯的直接影響。我們可以注意到,“天元皇太后璽”與秦漢印制的區別:一是有陰文變為陽文,二是印面成倍的增大,這也是隋朝印制所具有的特征[1]。
隋朝官印百官皆用,促使了文武百官不再佩印、印歸官府保存的制度。為表明身份、昭示權威,隋開皇年間很快找到了替代物,起初用綬,以金、銀、綖絲織成以區別。不久即為木、銅魚符所替代,它們在區別等級,表明身份等方面與以前在佩印的功能上是一致的。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在隋朝時期紙張的大量普及,在印章的實用上,使用功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開始使用封泥到后來轉變成鈐蓋在紙上,由白文小印轉化成朱文大印,大小上由兩三厘米擴大到六七厘米。印邊邊框逐漸增寬和印文形成強烈的對比。
二、印文的排列格式
官印形式排列格式,南朝為一個系統,基本上是實行晉的模式,即:官印四字等分;五字印作三行,最后一字獨占一行;六字印作三行并且等分。隋朝官印上承北朝官印制度,并發生了變化,五、六字均作兩行排列格式。如隋印“右武衛右十八車騎印”雖作九字,也是排作兩行。由此可見,印文的排列純粹是因文相宜的布局形式,而不是等級制度的體現了。印文與官名稱相同,也就是說官印中所體現的官名是完整的,而不像晉只是為了滿足印文字數的格式而對官名作出簡縮。這一體制的歷史變革,一直影響到宋元明清[2]。
三、印章中技法剖析
印面的增大,留下更多空白和發揮的余地。朱文印印式的早期特征,漸漸脫離繆篆之法,采用難度較大的小篆篆法,在結體方面重視單個字的變化,為了布滿整個印面,有意壓扁或放寬字形,甚至改變筆畫的走勢。采用“蟠條印”的焊接工藝制作,字口深,經久耐用[3]。
如“桑乾鎮印”筆畫雖然斷殘嚴重,卻絲毫沒有影響整個印章氣韻的流暢,反而更加鮮活。筆斷處大空間的留白,和排疊均勻形成整塊“留紅”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鎮”字左上部的殘缺留白、幾乎不能辨別的“印”字留白和“乾”的右邊留白,典型的“三疏一密”章法,在平實中見奇趣。
如“觀陽縣印”四字結體靈活,篆法多取圓勢,很少有直筆或方筆的筆畫,以弧線加強閑適之趣。“觀”字左邊的結構上松下緊,拙樸富有趣味。如“觀”字的“目”“陽”字的“日”,以及“縣”字中的“且”等,遙相呼應。
如“右武衛右十八車騎印”整體取橫勢。結構壓扁,橫畫的排疊在其中增添分量。“右武”兩字與右下角的“右”字和“單”字,都是橫線的排疊幾乎不破損,基本上決定了整個印章的形式,在平正中有奇思。“印”字比較松闊,“騎”字中“奇”的上面幾乎全部破掉留下的大塊空白,整體看上去比較透氣。
四、對當代篆刻創作的啟示
隋朝官印以特有的鑄造方式和入印文字所呈現出的線條表現形式,更為直觀表達筆意的形式,為當代篆刻創作提供了更優化的范式。
自明代文彭始,石材的大量使用,在刀石之間去體現筆墨意蘊,流露出清雅而有筆意的氣息,是印人所不斷追求的意境。清代印學家趙之謙在論印詩中說:“古人有筆尤有墨,今人但有刀與石”。從中可以看出他對當時印人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刀石之味而對筆墨意味不太講究的創作現象所做的針砭。筆意在印章中表現流動、韻律、趣味、自然等審美意蘊。
用刀“簡”“潔”遂使線條比較流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線條相對光潔,極易匠氣。韓登安《容琪樓印話》中:“刀法最忌刮垢磨光,違之必成謝滑纖弱,毫無韻味可言”。筆意之言,并不是單純的線條流暢,有時也需要抑揚頓挫。筆斷處,其筆勢健在,氣脈猶能貫通,有時因為是筆斷反而增加了局部的變化,讓線條更加鮮活、生動。殘缺生韻律,和筆意說并不相矛盾,反而確有互補的作用。創作中,落刀成勢不受細小處束縛,筆意自然流露在外,在刀石之間,用刀軌跡清晰,創作者情感起伏,自得其趣。
隋朝官印式的形式直接推動了整個印學史的發展,給篆刻藝術增添了新的元素。歷史的變化錯綜復雜,隋式官印是印學發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引領了后世,也昭示了其時代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