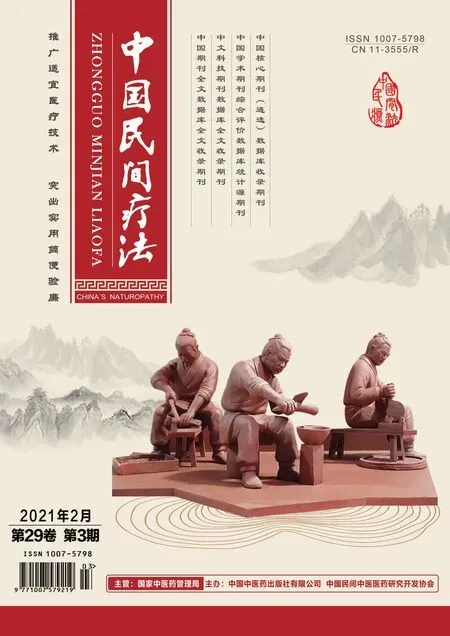潰瘍性結腸炎的針灸治療思路探析※
曾 超,梁俊斌,張 悅,賀香毓,鐘秋蘭,邸安琪,丘明旺,許少綿
(1.廣東省東莞道滘醫院,廣東 東莞523176;2.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510006)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種結腸和直腸慢性非特異性炎癥性疾病,病變局限于大腸黏膜及黏膜下層,多位于乙狀結腸和直腸,也可延伸至降結腸,甚至整個結腸,病程漫長,常反復發作[1]。目前該病發病機制尚不明確,可因直腸順應性降低而引起易怒、失禁、體質量減輕和全身不適等[2]。UC屬于中醫“泄瀉”“久痢”“腸澼”等范疇,病機多為脾腎兩虛、肝脾失調、濕熱阻滯大腸,為本虛標實之證,本虛為脾腎虧虛,標實為濕、熱、瘀、毒壅滯大腸[3]。針灸作為重要的中醫治療手段,治療UC效果較好[4-6],且無明顯不良反應。各代醫家對UC病因病機的認識各異,當今臨床醫生對該病的治療思路也有較大差異。結合已有文獻與臨床實踐,本文探析針灸治療UC的治療思路。
1 中西醫理論分析
1.1 從中醫角度探析UC 十二經脈與其所屬臟腑存在直接聯系,《靈樞·逆順肥瘦》曰:“手之三陰,從臟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十二經脈通過氣血運行,溝通體表與五臟六腑,構成了一個如環無端的網狀結構[7]。手陽明大腸經與足陽明胃經相接相通,故氣血循行從手陽明大腸經流入足陽明胃經,病邪亦可據此傳變,由此表明該病有可能并發潰瘍性胃炎[8]。
UC與其他臟腑、經絡的關系同樣密切。如手太陰經別散布于大腸,足太陰經別絡于大腸,此外腧穴是各臟腑經絡氣血輸注于體表的位置,也是疾病的病理反應點。研究表明,UC與脾經、肺經、大腸經、肝經、腎經存在特異性聯系,與足三里、上巨虛、大橫等穴位的關系也較密切[9],這些經脈具有多氣多血的特點,說明UC病因與氣血的變化關系密切,這是臨床選穴的重要基礎。
1.2 從現代醫學角度探析UC 現代研究表明,UC可能是由遺傳易感性、環境因素、腸道免疫紊亂、神經內分泌失調引起[10]。該病發病存在種族差異性,常見于白種人,不同人種病變程度不同。有學者研究發現,UC患者在環境刺激下CD+4和糖皮質激素調節蛋白激酶1(SGK1)過表達,導致炎癥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IL)-17和IL-13分泌失衡,進而導致慢性疾病[11]。結腸由腸系膜上、下神經叢支配,神經內分泌細胞分泌的腦腸肽激素可以維持機體穩態。UC患者血清中腦腸肽分泌紊亂,使腸道平滑肌收縮,產生不合適的免疫反應,促進炎性因子釋放,形成局部炎癥[12]。因此從現代醫學角度可以認為,UC發病機制與腸黏膜免疫反應及神經內分泌密切相關。
2 針灸治療思路
UC大多為本虛標實之證,其治則宜標本兼顧,同時應以急則治其標、損其偏盛為原則,常用扶正固本、補益脾腎、疏肝健脾、清熱祛濕等治療方法。UC的治療思路為針灸并用,標本兼治。治療策略重視標本情況,或先針去標實、后灸補其本,或先治其本虛、后治其標實,遵循調脾腎以補益本虛、調腸道以祛除標實的原則,選穴以任脈的關元和胃經的合穴、下合穴為主,以脾經、肝經及膀胱經的穴位為輔。
2.1 針灸并用,標本兼治 中醫認為,UC患者多素體脾虛或脾胃受損,易感濕熱之邪,而濕熱邪氣是導致UC發病及病情進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認清標本輕重緩急,若體質虛弱者,應先艾灸補益脾腎以固本,再行清熱祛濕之法以祛邪;若體質強壯者,則可先行瀉法。《靈樞·經脈》曰:“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說明應根據標本具體情況實施恰當的治療方法。《素問·異法方宜論》曰:“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闡明臨證可使用多種方法,按照標本輕重進行綜合治療。鄭麗紅等[13]采用溫針灸配合愈腸栓治療寒熱錯雜型潰瘍性結腸炎,標本兼治,有良好的臨床療效。
2.2 經絡和穴位選擇的治療策略 ①經絡選擇方面,針灸治療UC多取足陽明胃經、任脈及足太陽膀胱經穴位[14-16]。脾胃乃氣血生化之源,且足陽明胃經多氣多血,屬胃絡脾,循腹里,該經穴位可健脾益氣除濕。任脈循腹而上,行經中焦,鄰近脾胃,該經穴具有健脾和胃、理氣寬中之功效;經脈所過,主治所及,通過刺激任脈可對足陽明胃經產生一定作用,達到行氣活血、疏經止痛之功效。足太陽膀胱經的背俞穴為臟腑之氣輸注于背部的穴位,該經穴位與臟腑功能具有密切的聯系。②穴位選擇方面,針灸治療UC常取足三里、天樞、關元、上巨虛、長強等[17-18]。足三里為足陽明胃經合穴,胃的下合穴,“合治內腑”,《四總穴歌》有“肚腹三里留”之說,均表明足三里為治療腸腑疾病的要穴。募穴是臟腑經氣在胸腹部聚集之處,腑病取募穴,天樞是大腸經募穴,是陽明脈氣所發,為腹部要穴;關元為小腸經募穴,既可調理臟腑氣機,又可扶正培元。三陰交為足太陰脾經穴位,治療腹痛、腹瀉、便溏等腸道疾病。陰陵泉為脾經合穴,乃利濕要穴。上巨虛乃大腸經下合穴,可疏通大腸經氣,取“合治內腑”之義。脾俞、腎俞補益脾腎。長強為督脈絡穴,位于會陰區,局部取穴可以斂腸止瀉。諸穴合用,具有調理腸腑氣機、健脾益腎之效。
2.3 針灸治療的作用機制 現代醫學關于UC的病因與發病機制未完全闡明。目前普遍認為,其發病與免疫調節紊亂、遺傳易感性、感染及環境等因素有關[19]。現階段的研究表明,針灸對UC具有針對性治療作用,主要通過調節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腸動力等體內多個靶點的生理平衡,進而有效控制腸道炎癥,其治療機制與發病機制相關[20]。①在臨床研究方面,張博等[21]研究發現,自擬扶正平潰湯聯合針灸能顯著緩解慢性UC患者的臨床癥狀、體征,抑制患者腸道黏膜炎性損害,機制可能與改善腸道菌群失調,促進輔助性Th17細胞和調節性T細胞(Th17/Treg細胞)免疫平衡,從而抑制炎性反應有關。②在動物研究方面,陳艷萍[22]研究發現,針灸能通過下調UC模型大鼠結腸組織中γ-干擾素和IL-12水平,上調IL-4和IL-10水平,從而保持Th1/Th2細胞間平衡,進而改善免疫功能,達到治療UC的作用。王程玉林等[23]研究發現,電針足三里、關元可以治療UC模型小鼠,其機制可能與調節UC小鼠Treg/Th17細胞免疫平衡相關,針灸可通過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RH)、皮質酮(CORT)和5-羥吲哚乙酸(5-HIAA)調節腦-腸軸,這可能是其緩解UC焦慮樣行為的重要機制[24]。綜上研究,針灸治療UC是通過抑制炎癥、調節免疫平衡、調節腸道菌群等多水平、多靶點方式進行調節。
3 病案舉隅
患者,女,35歲,2019年3月3日初診。主訴:間斷性腹痛、腹瀉、黏液膿血便2年。外院電子結腸鏡示UC。經口服美沙拉嗪腸溶片腹痛減輕,但腹瀉、黏液膿血便仍纏綿不愈。刻下癥:間斷性腹痛,腹瀉、黏液膿血便,每日4~5次,口干口苦,心煩不安,納呆,眠可,小便黃,舌暗紅、苔黃厚,脈弦細數,余未見明顯異常。西醫診斷:UC。中醫診斷:泄瀉。證型:濕熱內蘊,脾胃虧虛。治法:祛濕化濁,健運脾胃。治療方法:針刺雙側足三里、上巨虛、水道、公孫、合谷、曲池,得氣后行捻轉瀉法,然后在天樞(雙)、關元、氣海行艾灸補法,長強斜刺行補法,可加灸行溫針灸,時間均為30 min。1個療程(6 d)后復診,患者腹痛、腹瀉減輕。繼續維持原方案治療,2個療程后患者腹痛、腹瀉癥狀基本消失。患者繼續針刺治療,調節飲食,保持心情愉悅,隨訪半年,未復發。
按語:患者間斷腹痛伴黏液膿血便為典型UC癥狀,兼見心煩,納呆,小便黃,舌紅,苔黃,脈數,可診斷為濕熱內蘊、脾胃虧虛型UC。針刺瀉法,取足三里、上巨虛、水道等調理臟腑氣機、泄腸腑濕熱,后灸天樞、關元、氣海培元固本、補脾養胃,長強針刺或溫針灸斂腸止瀉、扶陽固本,同時配合情志調節,保持心情愉悅,病乃除。
4 小結
UC的治療重在增強免疫功能,維持免疫平衡,針灸可以對免疫系統相關因子起到針對性的作用。針灸治療該病采用針灸并用、標本兼治的治療方法。UC病機多為本虛標實,治療需做到辨清標本、輕重、緩急、虛實,結合針刺和灸法,視輕重、緩急而采取先去其標實再補其本虛,或標本同治,或先治本虛后去標實,才能達到補益氣血、調理腸腑氣機、補脾益腎的目的,因此辨清疾病標本、虛實極為重要。針刺可調理臟腑、祛除病邪,艾灸可補脾益腎、扶正培元,兩法相合,療效更佳。因此,辨清基本標本、虛實是治療疾病的首要任務,再以針灸并用,方可標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