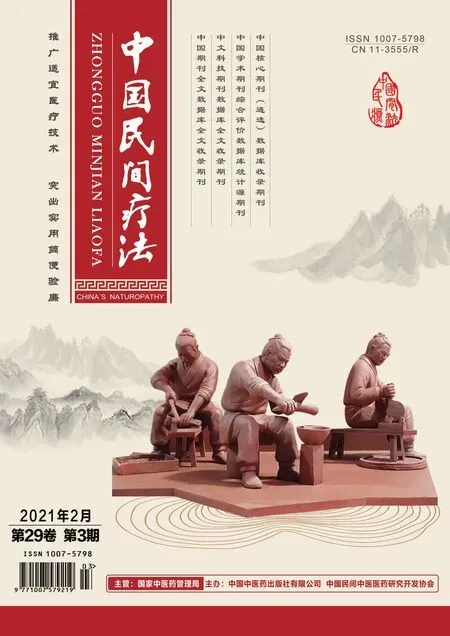賈躍進從肝論治不寐經驗※
劉 毅,何曉瑜,李 菲,賈躍進,郝世飛
(1.山西中醫藥大學,山西 晉中030619;2.山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山西 太原030024;3.山西省人民醫院,山西 太原030012)
不寐是以頻繁而持續的入睡困難或睡眠維持困難并導致睡眠滿意度不足為特征的睡眠障礙[1]。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復雜的人際關系使人們壓力不斷增大,因此由肝氣郁結導致的不寐日益成為臨床的常見類型[2]。目前西醫治療不寐主要采用苯二氮類藥物,但可能會引起疲乏、嗜睡、頭昏和頭痛等不良反應,也可能引起成癮性或依賴性。中醫治療疾病注重整體,針對不寐審證求因,辨證論治,調節睡眠節律的同時未見相關的不良反應,因此治療不寐具有一定的優勢。賈躍進老中醫從醫40余年,擅于應用中醫藥治療各種神經內科疾病,其以營衛、陰陽為立足點,從氣的角度從肝論治不寐,每獲良效。現闡述如下。
1 從肝論治不寐的理論淵源
中醫認為心主神明,故歷來眾多醫家主張從心論治不寐,但肝與不寐亦密切相關。肝主疏泄,藏血,藏魂。《素問·五臟生成》載:“人臥血歸于肝。”[3]《血證論》亦提出:“肝藏魂……人寐則魂返于肝。”[4]分別從肝藏血和藏魂的角度闡述了肝對睡眠的影響,睡覺時血歸于肝、魂返于肝,若肝疏泄異常則可導致血不歸肝、魂不返肝而引發不寐。此外,肝或肝經受邪,多為肝郁或火熱為患,易致肝疏泄失常,氣機不暢,從而使神魂受擾,眠臥不寧。如《素問·刺熱》載:“肝熱病者……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3]《癥因脈治》述:“肝主藏血,陽火擾動血室,則夜臥不寧矣。”[5]從上可得,肝體不足和肝用失常均會引起不寐。
2 賈躍進對不寐的認識
賈師通過臨床觀察及研究資料文獻,并結合目前不寐的發病原因和規律,形成了對不寐的體系認識。
天人相應是中醫認識、解釋生命現象的基本思想之一,大自然有晝夜節律,與之對應,人體有寤寐節律。如《靈樞·口問》云:“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6]從生理上闡述了寤寐的發生機制,即寤寐是一個依賴營衛之氣推動的節律周期,衛氣白晝循行于陽經,目開而寤,夜晚循行于陰經,闔而寐。反之,“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蹺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不目瞑”[6]。此為病理狀態不寐的產生機制,即營衛運行失常,正常節律周期紊亂,導致不寐,故賈師認為不寐的總病機是“營衛失和,陰陽不交”[7],治療重點在于“調節律”。《丹溪心法·六郁》曰:“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于郁。”[8]說明氣血運行不暢,氣機郁滯可發為各種疾病,因此賈師認為“百病皆生于郁”,調氣可治百病。不寐更是如此,營衛之氣運行正常與否直接決定因素即為氣機,故不寐的治療也當從調氣論。中醫有“凡郁皆肝病也”[7]之說,可見“肝病”是“郁”的主要發病因素。而肝與氣機運行密切相關,氣的正常運行依賴于肝主疏泄的功能。肝病則失疏泄,分為疏泄太過和疏泄不及。疏泄太過,則機體處于亢奮狀態,容易肝郁化火、木旺乘土;疏泄不及,則會造成氣機運行不暢,產生各種病理產物,如痰、濕、瘀等,且肝郁癥狀較著。因此調節律實則為調氣,調氣實則為調肝。
總體來說,賈師認為現代人常處于競爭及人際交往壓力之下,導致情志不遂,氣機不暢,影響肝的疏泄功能,發展為疏泄失常,從而導致不寐。《普濟本事方》提出:“肝有邪,魂不得歸,是以臥則魂飛揚若離體也。”[9]可見肝作為全身氣機升降的樞紐,若疏泄失職,則會導致全身代謝失常,引起營衛失和,陰陽不交,節律紊亂,發為不寐,故賈師常調理氣機從肝論治不寐。“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旺不受邪。”[10]治療不寐時也要注重治未病,顧護后天之本,且諸醫家歷來重視“胃不和則臥不安”[11],同時現代醫學認為腦-腸軸是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及腸神經系統的雙向通信系統[12],因此,治療肝病的同時須兼顧脾胃。綜上,賈師從肝論治不寐的診療體系符合中醫傳統理論與現代醫學相關研究,也更符合目前不寐的發病規律。
3 賈躍進臨床診治經驗
3.1 肝郁化火證 情志不遂,肝失條達,氣機郁滯,郁而化火,肝火擾心而發為肝郁化火型不寐。該型不寐具體表現有入睡困難,烘熱汗出,急躁易怒,舌紅脈弦等。賈師臨證常投丹梔逍遙散加減,其指征為患者年齡較大,起病較緩,兼見氣血不足之癥。丹梔逍遙散可疏肝健脾,清熱養血,另常與香附、合歡皮、玫瑰花、首烏藤等配合使用,加強其疏肝安神之功,若脾胃虛弱較著則易梔子為知母,加大白術、茯苓等藥物劑量,以麥芽佐之。
3.2 樞機不利證 情志失調,肝氣郁滯,樞機不利,營衛運行失常,致陰陽不交而為樞機不利型不寐。該型不寐具體表現特點有精神癥狀多,如睡前多慮,心煩,壓抑等;軀體癥狀多,如胸脅苦滿,頭、少腹、乳房或全身脹痛等;自覺癥狀多,如不思飲食,對溫度變化敏感等;有胃腸癥狀,情緒可影響飲食或致腹痛等。對于該證的治療,賈師常采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化裁以和解樞機,重鎮安神,因鉛丹有毒,賈師以珍珠母代之,另常與遠志、合歡皮、白芍、牡丹皮配合應用,加強其疏肝清熱安神之功,該方中重鎮安神之品較多,恐礙胃氣,故常佐麥芽。
3.3 肝郁痰熱證 情緒抑郁,抑郁動肝,肝郁化熱,氣郁生痰,痰熱搏結擾亂心神,發為肝郁痰熱型不寐。該型不寐具體表現為在肝郁癥狀的基礎上出現口干苦,喜涼飲,頭面油膩,大便不暢,苔黃膩等癥狀。賈師常選柴芩溫膽湯,其中小柴胡湯和解少陽,運轉樞機,兼以化痰,溫膽湯治痰濕蘊熱,另常予以合歡皮、遠志、炒薏苡仁等解郁安神利濕。
3.4 肝郁脾虛證 情志不舒,肝氣郁結,木旺乘土,“胃不和則臥不安”而發為肝郁脾虛型不寐。該型不寐具體表現為肝郁,多慮,納差,胃脹,大便黏,舌有齒痕等脾虛癥狀。賈師常選香砂六君子湯治療該證,方中四君子益氣健脾,二陳燥濕化痰,香、砂疏肝理氣化濕,半夏“引陽入陰”,茯苓安神,另常以合歡皮、合歡花、酸棗仁等安神之品配合。
綜上,賈師以調理氣機、疏肝解郁、引陽入陰為基本治法,臨床予以丹梔逍遙散、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柴芩溫膽湯及香砂六君子湯等加減治療不寐,常取得較好療效。
4 驗案舉隅
患者,女,53歲,2019年10月10日初診。主訴:持續性失眠2個月余。刻下癥:入睡困難,睡前烘熱汗出,多慮,心煩,早醒難再眠,次日疲乏,頭蒙,頭重,下午加重,怕熱,胃怕涼,口瘡,咽痛,性急,納可,大便日一行,不成形,小便正常,舌有齒痕,脈沉弦。既往史:2016年行子宮切除術。西醫診斷:失眠障礙。中醫診斷:不寐,肝郁化火證。治療予以丹梔逍遙散加減。組成:牡丹皮12 g,梔子8 g,當歸10 g,白芍15 g,麩炒白術20 g,茯苓30 g,香附10 g,柴胡10 g,合歡皮20 g,遠志10 g,麩炒薏苡仁30 g,麥芽30 g。顆粒劑,7劑,水沖,早晚分服。2019年10月17日二診:不寐好轉,入睡難,但半夜醒后未興奮,心煩好轉,次日疲憊、頭蒙均好轉,納可,二便正常,烘熱汗出不甚,舌有齒痕,脈弦。上方加首烏藤20 g,龍骨30 g(先煎),服法同前。2019年10月24日三診:不寐明顯好轉,入睡可,醒后可再眠,納可,心煩好轉,不早醒,二便正常,烘熱汗出好轉。守上方。
按語:中西醫對于不寐(或失眠障礙)的診斷主要包括以失眠的基礎癥狀為主癥及持續時間在1個月以上兩個要點[13]。此案患者失眠兩個月,入睡困難,次日不適,故可診為不寐;由烘熱汗出、心煩、口瘡、性急、脈弦等可辨證為肝郁化火證,另外其亦有胃怕涼、大便不成形等脾虛之象,且其屬中老年女性,子宮切除,存在氣血不足,故此處選用丹梔逍遙散加減以疏肝健脾、清熱養血。因其脾虛,梔子減量;肝郁易致脾虛不運,故投以較大量白術、茯苓以防木旺乘土,同時使氣血生化有源;另加香附、合歡皮、遠志以加強解郁安神之功;大便不成形,予以麩炒薏苡仁健脾除濕;麥芽稟受春生之氣,脾胃藥善疏肝,佐以顧護脾胃并疏肝氣。二診時仍有入睡困難、汗出,因其肝血素虛,血不養心,故投龍骨以重鎮安神、斂汗,首烏藤以養心安神。三診時諸癥悉除,故守上方鞏固療效。
5 小結
賈躍進老中醫臨證主要將不寐分為肝郁化火、樞機不利、肝郁痰熱及肝郁脾虛等證型,在采用疏肝、柔肝、清肝之法調暢氣機的同時,強調肝脾同治,著重后天之本;選方重視方證相應,以法系方而不拘泥,根據患者情況針對性選方。總之,賈師以從肝論治思想為核心治療不寐值得學習、繼承與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