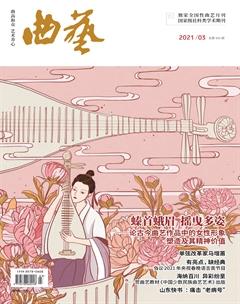由評彈劇《醫圣》試論傳統曲藝的創新性傳承
周勝南
2020年8月,評彈劇《醫圣》在上海首演。該劇講述了東漢末年的名醫張仲景臨危受命,在出使長沙郡太守期間帶領全郡軍民奮勇抗擊瘟疫的故事。
本文將以評彈劇《醫圣》的演出為范本,從“守正”與“創新”兩個方面探討評彈如何拓寬演出邊界,既保留其核心的藝術特征,又在戲劇舞臺空間內進行創新性的傳播,為傳統曲藝在當代的傳承發展積極探索新的樣式。
一、守正:堅持以“評彈”為核心
在蘇州評彈現場演出中,演員自彈三弦或琵琶,飾演的角色一般無需裝扮,僅憑說、噱、彈、唱來完成故事的敘述和多重角色的塑造。如何在戲劇舞臺上,遵循、保留并突出說唱藝術的主要特征,讓劇場里的評彈依然像評彈,是《醫圣》所堅持的守正之處。
1. 跳進跳出,觀演親密
在同一敘事環境中,評彈演員身兼多重身份,但他們不依靠角色身份的特定裝扮,而是完全依靠說唱結合來塑造各種角色:不僅以說書人的身份進行第三人稱的故事敘述和評論,也以故事角色的身份進行第一人稱的代言表演,同時通過語言和動作的靈活切換、不同唱腔間的情感表現,來完成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各種轉變。再加上評彈書場普遍規模不大,書臺與觀眾席距離接近,演員還可以隨時根據觀眾的現場反應及時調整演出的狀態,以演員本身的身份在故事情境和書場演出空間中游刃有余。這種表演身份的“跳進跳出”和在演出現場親密的觀演互動,是蘇州評彈藝術最重要也最鮮明的藝術特征。
走上戲劇舞臺的《醫圣》,仍然嘗試著保留評彈藝術的靈活表演和現場互動。舞臺的設計依然以“一桌二椅”的書臺為核心,琵琶與三弦這兩種經典的說書樂器仍舊存在。評彈演員換下說書時的長衫旗袍,穿上漢代服裝,時而安坐時而站立,用不同的臺詞、念白配合各類方言,再加以一系列戲曲動作,在不同的角色之間“跳進跳出”。舞臺另設相關劇情的情境表演,與評彈的傳統說唱區域有機連接,配合樂曲與唱腔的協調統一,讓觀眾在戲劇舞臺的大環境中,依然能夠欣賞到評彈藝術最根本的表演核心。
同時,區別于傳統戲劇演出時觀眾與演員之間壁壘分明的“第四堵墻”,《醫圣》在每場戲的連綴過程中,添加了“說書人”這個角色。說書人會站到臺前向觀眾進行劇情的敘述,替劇中人發聲,還會與觀眾溝通,聽聽他們的意見。據該角色的演出者、評話演員吳新伯介紹,他甚至還想嘗試打開觀眾席的場燈,想要在演出時走下舞臺與觀眾交流,因為作為一個評話演員,他非常希望能夠看到觀眾的表情來調整自己說白的情緒,讓演出的狀態更加飽滿。①
2. 文藝輕騎兵,彰顯正能量
評彈劇《醫圣》創作于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雖然劇情背景發生在漢代,但一代名醫張仲景面對瘟疫病魔威脅,始終用高尚醫德、精湛醫術帶領百姓戰勝時艱的偉大事跡,與當代奮戰在中國抗“疫”防疫第一線的廣大醫護工作者治病救人的英勇事跡無疑產生了共通性與相似性。古代與今朝的藝術時空相互映照,讓觀眾產生共情:原來在中國歷代瘟疫抗災的緊要關頭,中國醫護者的妙手仁心始終未曾改變,千百年來他們始終與前線的百姓站在一起。
《醫圣》劇本創作沿用了傳統曲藝創作的基本思路,重在寫人,并且在典型環境和典型事件中去塑造人的典型性格。“越復雜、越特殊、越艱難、越危險的環境,就越能讓人物的性格得到更好的表現。”②整劇總共4幕,由張仲景為醫為官歷程中的4個典型片段組成:破除迷信治病救人、帶領群眾抗擊瘟疫、懲治哄抬藥價的貪官污吏、歸隱山林編寫《傷寒雜病論》傳世救人。
從內容上看,4幕情節樁樁件件都能與當下抗“疫”時情產生連通,張仲景面對困境的無悔抉擇,既體現了故事中一代醫圣的高尚醫德,也自然地宣傳與頌揚了當代醫療工作者的奉獻與犧牲。從結構上看,每幕戲故事線完整,正反人物角色鮮明、沖突困境構建豐滿,說唱齊全、唱腔完備,每一幕的篇幅相當于一則短篇彈詞的容量。4幕情節再由說書人一角進行串接,構建起一出完整的評彈劇。用戲劇的幕與場的思維來結構評彈短篇,既豐富了評彈敘事的深度與廣度,也保留了曲藝創作短、平、快的特點,突顯了曲藝藝術“文藝輕騎兵”的宣傳優勢。
二、創新:評彈內核與戲劇外衣的平衡之道
從藝術表現形式來看,當蘇州評彈從書場進入劇場,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應該是對于以說唱為主的敘述式表演與以角色體驗為主的代言式表演之間要如何轉換、平衡與創新。評彈藝術要如何既保留其藝術內核,又適應戲劇這個廣闊的舞臺空間,《醫圣》對這個藝術本質的問題做出了寶貴的實踐與探索。以下將以該劇的高潮場次《壽堂殺令》為例,展開分析。
1. 戲劇沖突的呈現:行當齊全,說唱共情
戲劇與曲藝最大的區別在于帶領觀眾入戲的方式并不相同:曲藝是通過敘述、歌唱等口頭藝術形式,描繪出故事情節和矛盾沖突。就像評彈藝術起角色時特有的“跳進跳出”,讓身兼多重身份的演員始終保持著較清醒、旁觀的姿態,帶領觀眾進入故事的情境。而戲劇則不然,演員通過對角色的摹仿構建起故事情境,觀眾觀賞并體驗著角色的喜怒哀樂,沉浸于戲劇的矛盾沖突之中。
在《醫圣》第四幕“壽堂殺令”中,一個演員基本確定只扮演一個主要角色。每個角色在臺上有簡單的走位,雖然缺少大幅度的身段動作,但也借鑒了戲曲行當的塑造,呈現出了太守張仲景、鄉紳吳良坤、茶陵縣令等不同角色及其行當區分。更重要的是,每個角色均有其特定的念白方式、地區方言,也擁有各自專屬的流派唱腔,如張調、蔣調、嚴調等。角色間的對白敘述與評論較少,多是以角色身份進行你一言我一語的交叉呈現,彼此間的沖突在臺詞說表中層層推進,增強了角色交流的戲劇張力。同時,每句臺詞后都有琵琶彈奏充當鼓點,有效地推進了敘事的節奏和角色對抗的情緒節奏,把劇情矛盾推向高潮。
從總體舞臺呈現來看,這段高潮情節是屬于代言式的。但對演員表演來說,用的卻是以說表為核心、輔助以戲曲身段的創新之法。實踐證明,曲藝的敘述呈現與戲劇的代言共情之間并非壁壘分明,兩者間應嘗試一種有分寸的融合,既堅守評彈說唱的藝術特征,也要借鑒戲劇的演出形式,增加“演”的成分,并利用舞美、音效等手段,審慎而開放地構建起評彈劇的創新思維。
2. 表演空間的更新:傳統書場格局的突破
傳統書場里,演出空間相對局促,僅限于“一桌二椅”及其周圍,缺乏舞臺調度。但戲劇劇場的空間呈現要遠遠大于書臺,《醫圣》突破了傳統的說書演出格局,視聽效果從書臺中心拓展到了全部舞臺。
首先,劃分演出區域,突出戲劇空間。《醫圣》的舞臺設計保留了傳統書臺的演出區域,三弦、琵琶等必要的評彈元素也一應俱全。與此相對應的,是突出“演戲”成分的戲劇表演區域。每一幕戲都有效地把舞臺空間劃分為書臺區和表演區,書臺區有評彈必備的說與唱,表演區則是配合說唱所呈現的戲劇情境。演員們分別在不同場次扮演著病人、災民、青年醫生等群體角色,以現實主義的表演方法進行著角色的塑造。根據劇情,演員們有時會以劇中的身份與書臺區的角色進行交流,推動劇情發展;有時會載歌載舞地演繹【無錫景】【道情調】等傳統評彈曲牌,營造故事氛圍;有時也會用動作擺出群體造型,構建莊嚴肅穆的舞臺現場感。以上兩個區域同等重要,并不存在前臺與后臺的差異,彼此間還通過演員互動與道具布景的移動,實現跨區域的統一與融合,大大豐富了評彈劇的視覺空間呈現。
其次,細節抽象、整體真實的漢代舞臺設計。《醫圣》故事發生于東漢時期,其舞美設計不是簡單的現實主義重現,而是像評彈藝術本身的特征那樣,說表融會、虛實結合,全方位地利用舞美的各種元素,呈現出細節抽象,但整體戲劇氛圍真實的風格追求。舞臺背景既有梅蘭竹菊的剪影,也有諸多中醫藥材名詞的有機組合,更有本劇主人公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的古書投射,恰如其分地表現了敘事環境;演員的化妝并沒有特定的角色指向,雖身著漢服,但依然是說書先生的平常妝容,這符合評彈表演多重角色轉換的要求;適當使用舞臺追光,即便是在書臺區域也有效地烘托了說書時的懸念和沖突的進展感;音樂形式則更加豐富,對于傳統評彈曲牌的重新編曲和整理,劇中重要的音樂道具古琴的琴譜,針對角色進行改良的經典流派唱腔,都充分地體現了評彈藝術在融入海派文化后所呈現出來的包容、開放與創新之態。
評彈劇《醫圣》探索了一種傳統曲藝在當代進行創新性保護與傳承的有效途徑。它既保留了傳統口頭說唱“一人多角、跳進跳出”的藝術核心,堅持以靈活輕便的演出創作走在文藝宣傳的前線,也在劇場環境中充分借鑒了戲曲演出的手段,運用行當、身段、舞美、音樂等一系列方法,把三尺書臺拓展成了完整的舞臺空間。它既像評彈,也像劇,演員演出時而敘事時而代言,觀眾時而共情時而入戲。這是蘇州評彈尋求整體性、創新性、轉型式傳承的重要嘗試,但愿這種探索能讓蘇州評彈獲得超越書場的關注度,受到更廣泛的受眾審美認可,為傳統曲藝在當代的傳承與發展提供新的思路與新的借鑒。
注釋:
① 筆者在2020年8月15日評彈劇《醫圣》彩排現場,根據對吳新伯老師的采訪總結而成。
② 繞學剛:《曲藝創作漫談》,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頁。
參考文獻:
① 吳文科:《曲藝綜論》,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版。
② 王筱麗:《上海評彈團首創評彈劇<醫圣>引熱議:從書場進入劇場,評彈這一步邁實了嗎》,《文匯報》,2020年9月17日。
[注:本文為201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晚清以來中國書場研究》(項目編號17BB02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朱庭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