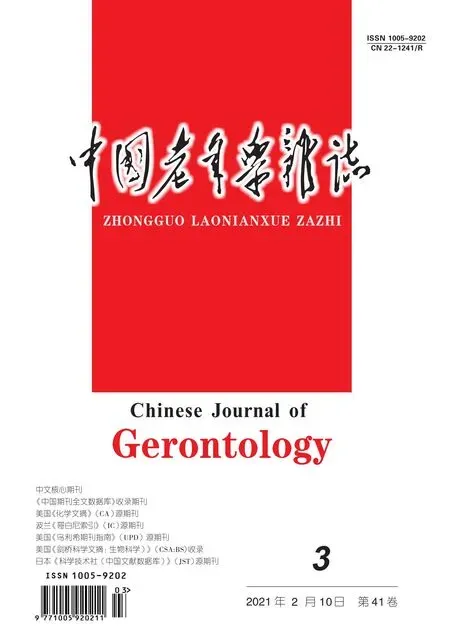居家失能老年人家庭抗逆力
周佳 王玉環
(石河子大學醫學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2)
“失能”作為一個應激源,給照護者及整個家庭帶來嚴重照護負擔。然而,相關研究發現即使在巨大的照護負擔及壓力下,一些家庭也能通過動用家庭內外資源順利渡過逆境,促進家庭健康發展,提高被照護者生活質量。家庭抗逆力作為逆境發生時的首要反應,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往關于居家失能老年人照護的研究多關注居家照護者個體抗逆力,將家庭僅作為影響個體抗逆力的背景因素〔1,2〕。研究發現〔3〕,當家庭遭遇逆境時,家庭整體的應對比個體應對更有效。因此,關注家庭壓力及照護負擔對提高失能老年人照護質量并保證家庭健康發展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當家庭面臨逆境,在如何緩解壓力問題上,學者們引入了“家庭抗逆力”概念并嘗試將家庭作為抗逆力產生的獨立功能實體視角進行研究。本文從家庭抗逆力測量及影響因素對居家失能老年人家庭抗逆力進行綜述。
1 家庭抗逆力測量
1.1概念 由于學者研究視角及學科背景差異,家庭抗逆力至今仍缺乏統一的定義。目前學界對于家庭抗逆力的概念主要從“過程說”及“能力說”界定,如Hawley等〔4〕認為家庭抗逆力指家庭成員面對壓力時的適應及轉變過程;McCubbin等〔5〕將其定義為:家庭利用其行為模式、技能去談判,應對乃至在逆境和危機中成長的能力;Walsh〔6〕認為家庭或成員在面對逆境時,表現出的正向承受能力、靈活機智的反彈能力和自我康復能力。盡管學者們對家庭抗逆力的內涵界定不盡相同,但從中可發現以下3個方面對抗逆力內涵的貢獻。第一,逆境是激發抗逆力產生的起點,沒有逆境就沒有抗逆力。第二,抗逆力具有“彈性”。家庭在危機或壓力下可能會暫時偏離軌道,但能夠動用內外部資源抵抗家庭基本結構的改變,維持家庭健康狀態。第三,抗逆力傾向于從優勢視角被看待。
綜上,失能老年人家庭抗逆力可以被理解為失能老年人家庭在面臨失能這一逆境時,家庭動用內外部各種資源積極應對的能力或過程。
1.2家庭抗逆力理論模型及測量工具 相關領域研究圍繞兩個主要模型展開,McCubbin等〔7〕的家庭調整與適應的抗逆力模型(RMFAA)及Walsh〔1,6〕的家庭抗逆力框架。McCubbin等〔7〕將抗逆力過程分為兩階段:調整及適應。在調整階段,家庭在壓力事件出現后努力實現平衡、維持家庭健康狀態,隨著時間推移,調整階段發展為適應階段,家庭要對壓力源進行廣泛而具體的評估,發揮抗逆力的積極作用,動用家庭內外部資源應對,如果應對失敗,壓力就會進一步轉化為危機。Walsh〔1,6〕從家庭系統出發,提出了1個更加靈活的家庭抗逆力框架,對每個家庭的特定背景下的抗逆力進行評估,包含3個維度:信念系統、組織模式及溝通過程。這三者并不是完全獨立的,而是在同一個家庭系統中相互作用并在互動過程中發揮抗逆力作用。該模型在臨床預防和干預中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除了對家庭抗逆力理論模型進行研究,學者們根據相關理論模型及研究目的編制了不同量表,嘗試從量化角度對家庭抗逆力進行評估。
1.2.1康納-戴維森抗逆力量表(CD-RISC) 由Connor等〔8〕于2003年共同研制。量表包含5個維度(個人能力、忍受消極情緒、積極接受變化、控制及宗教影響),25個條目,總分范圍0~100分。Cronbach α為0.89,重測信度為0.87,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0~4分),得分越高反映抗逆力越好。此量表被改編為多個版本運用到不同研究中,如對老年非正式照護者抗逆力測量〔9〕。該量表常用于測量患者、照護者個體抗逆力水平。
1.2.2抗逆力量表(RS) 由Wagnild等〔10,11〕編制,包含2個維度(個人能力、對自我和生活的接納),25個條目。量表的Cronbach α為0.91。后來學者們將其改編為多個版本(如RS-11、RS-14、RS-15等),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個體抗逆力研究中。該量表在西方國家得到較好發展,但在中國研究較少,且量表版本眾多,使用時需進行信效度檢驗。
1.2.3家庭抗逆力評估量表(FRAS) 由Sixbey〔12〕在Walsh〔1,6〕的家庭抗逆力模型基礎上于2005年編制而成的,最初有66個條目,后發展為簡短版54個條目。由家庭溝通與問題解決、保持積極的態度、社會與經濟資源利用、家庭聯結感、賦予逆境意義及家庭精神6個維度構成。量表采取Liket 4級評分法計分,其中有4個條目反向計分,總分為54~216分,得分越高代表家庭抗逆力越好。量表的Cronbach α為0.96,各個維度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0~0.96。目前除英文版外,還有韓文及土耳其文版〔13〕。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夠用于家庭抗逆力水平測量,在英語文化背景下研制,由于各國家文化價值不同,使用時應做適當改編及調整。
1.2.4家庭堅韌性量表(FHI) 由McCubbin等〔5〕在其家庭抗逆力架構上發展起來,包括3個維度(責任、控制及挑戰),共20個條目。量表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即0分=“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同意”、3分=“非常同意”,其中有9個條目反向計分,總得分范圍0~60分。該量表3個部分的Cronbach α分別為0.764、0.720和0.704,內部一致性為0.82〔14〕。該量表在國際上具有權威性,信效度良好,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對家庭韌性進行評估。
綜上,評估家庭抗逆力并不是對家庭成員個體抗逆力簡單的加減,將家庭作為獨立功能的研究實體,其測量的指標與個體測量指標在一定意義上所反映的問題是不同的,因此在測量對象上,不能將個體抗逆力等同于家庭抗逆力。應按照研究目的及研究內容不同,評估家庭中與抗逆力相關的關鍵人物組,按照組的表述統計家庭抗逆力。盡管上述量表不是為失能老年人家庭抗逆力定制的,但并不影響其在這一研究領域使用。
2 居家失能老年人家庭抗逆力影響因素
2.1家庭資源 家庭資源指為了維持家庭基本功能、應對家庭壓力事件或危機狀態,家庭所必需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15〕。一個家庭可利用的資源越充足,則越有利于家庭及其成員的健康發展。家庭資源包括家庭成員數量、健康狀況、經濟水平等。
2.1.1家庭成員健康狀況 有研究顯示〔16〕,疾病類型、病程及疾病引起患者生活方式的改變會對家庭造成負面影響,使照護負擔加重,從而引起家庭抗逆力水平改變。除了患者健康狀況影響家庭抗逆力,照護者健康狀況也對家庭抗逆力產生重要影響。1項對韓國7家臨終關懷和姑息護理機構273例護理人員的橫斷面研究顯示〔17〕,護理者健康狀況感知差,不僅使個體抗逆力變差〔調整優勢比(AOR)=2.26,95%CI=1.16~4.40〕,還導致家庭面臨更加嚴重的照護壓力。同樣,Fernández-Lansac等〔18〕通過CD-RISC對53例癡呆患者的居家照護者進行抗逆力評估,發現照護者低水平抗逆力與其較差身體狀況(如焦慮、抑郁、精神藥物使用、不良健康習慣等)相關并由此引起家庭抗逆力水平改變。
2.1.2家庭收入 有研究顯示〔19〕,家庭收入是家庭內部一個重要的保護性因素,幫助家庭抗逆力在動態過程中成功應對不利條件,減小不良后果的風險。Kalomo等〔20〕對南非納米比亞農村老年照護者的家庭抗逆力研究中發現,家庭月收入越高(β=0.32,P<0.01)、家庭成員就業越好(β=7.385,SE=2.969,P<0.05),家庭經濟水平越高,則照護者個人及家庭能以更強能力面對逆境。提示就業者及政策制定者應共同努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干預計劃,以改善貧困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人員及家庭的整體經濟狀況。
2.2家庭功能 美國1項使用FRAS對77例成年糖尿病患者的描述性分析中發現〔21〕,家庭功能與家庭抗逆力呈顯著正相關(r=0.59,P<0.01),且家庭功能是該研究中家庭抗逆力的唯一預測因素,解釋了46%的差異。Ni等〔22〕運用CD-RISC、家庭和睦量表(FHS-5)及家庭關懷度指數問卷(APGAR)對香港18個地區的住戶進行分層隨機抽樣,選取10 997例年齡20歲以上的受試者進行隊列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抗逆力與家庭和睦(r=0.20)、家庭功能(r=0.27)呈正相關(均P<0.05)。
2.3社會支持 許多研究證實,社會支持是決定患者和家庭健康及其抗逆力水平的因素之一,依賴家庭、朋友網絡支持和專業支持能對家庭抗逆力尤其是弱勢家庭產生積極作用〔23〕,Lietz等〔24〕研究了兒童福利相關家庭抗逆力,將社會支持確定為有助于家庭實現統一和保持健康功能的幾個因素之一。同樣,Walsh〔25〕研究了基于抗逆力的家庭實踐,認為建立社區和擴大的家庭支持網絡、相互支持和聯系對于非正式照護至關重要。Kim等〔26〕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收集到的292例韓國癡呆老年人家庭抗逆力進行調查,分別使用不同量表對家庭抗逆力的3個維度(信念系統、組織模式及溝通過程)進行評估,結果顯示3個維度得分均與社會支持呈顯著性正相關。通過建立強大的家庭信念系統、利用家庭資源、發展更穩定的組織模式及獲得有效的社會支持能增強家庭抗逆力。Donnellan等〔27〕對來自兩個護理支持小組和1例位于英格蘭西北部護理院癡呆老人的配偶進行了23次深入的護理訪談表明,家庭和朋友服務范圍廣泛,但對不同抗逆力水平的家庭均有作用;朋友支持對家庭是最有幫助的;鄰居只能提供切實的支持,但當緊急情況下家人和其他朋友不在時,照護者會向鄰居尋求幫助,這使其成為一種獨特的、有價值的資源,有助于增強家庭抗逆力。
2.4照護負擔 葡萄牙的1項研究〔28〕調查了180例患病兒童的父母,發現照護負擔水平會影響家庭風險和保護過程,照護負擔是家庭抗逆力及家庭成員健康狀況的顯著危險因素。同樣,1項對108例患有早期乳腺癌的婦女及其照護者的橫斷面研究〔29〕,照護者完成了FRAS中文版及照護負擔量表,在控制患者社會人口學資料的同時進行分層分析,顯示家庭抗逆力與照護者負擔呈負相關(β=-0.28,P<0.01)。
2.5其他 Deist 等〔30〕使用定性(半結構訪談)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對南非47個癡呆非正式照護家庭進行研究,被調查者為家庭單元中選出的代表。研究發現,樂觀、積極的溝通模式、良好的家庭聯系及有效的癥狀管理是家庭抗逆力的保護性因素,有助于家庭降低癡呆照護的負擔。
有學者提出將個體與家庭抗逆力相結合研究〔31〕,一項對1 006例社區老年人的調查問卷,將Walsh〔1,6〕抗逆力理論的9個結構進行因子檢測,最終顯示8個因子結構與家庭抗逆力及個體抗逆力有關;對8個因子之間的協方差進行二級驗證性因子分析(CFA),最佳擬合模型CFA(χ2=360.5,df=196):NNFI=0.893,CFI=0.909,RMSEA=0.045,90%CI=0.038~0.052,意味著個體抗逆力高則家庭抗逆力高。基于此,個人層面的抗逆力在家庭抗逆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綜上,對于居家失能老年人家庭抗逆力,大部分學者從照護者個人層面探究并取得豐富成果,但將家庭視為一個整體進行家庭抗逆力研究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個人層面研究僅能反映個體抗逆力水平,而從家庭層面分析對促進家庭健康、提高居家失能老年人照護質量更有現實意義。因此,理清居家失能老年人家庭抗逆力的概念內涵及發生機制,編制適合我國本土化、多元化及跨學科化家庭抗逆力測量工具將是未來研究的重點和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