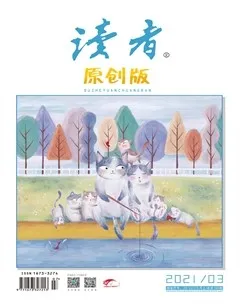浴鍋奇事
莊曉
浴鍋洗澡,又稱“鍋浴”。我在浴鍋中洗了十幾年的澡,從沒覺得這樣的洗澡方式有什么問題。兒時農家條件差,家家戶戶都用浴鍋洗澡,下面燒火上面成湯,火是薪火,湯是澡湯。即便后來家中境況改善,有了浴缸,一至冬日,浴鍋仍舊是重要的洗澡“神器”。一人添柴加火,一人帶好換洗衣物靜候,直至水溫適中,屋內煙霧繚繞,熱氣騰騰,沐浴之人一件一件褪去衣物,虔誠地走向鍋中,仿佛舉行一場盛大而重要的儀式。
直至我外出讀書、工作,才知這浴鍋竟只有我們蘇南一帶有,外人聽說我們用大鐵鍋盛水直接燒水洗澡,無不瞠目結舌。首次帶朋友回家鄉,看到如此大的鐵鍋,他也是一聲驚呼:“鐵鍋作何用?”當得知是用來洗澡時,他驚訝得半天說不出話。幾次勸他嘗試一番,怎么都不肯,說鍋是用來烹飪的,這下面燒火上面洗澡的場景,實在不敢想象。
兒時,家家戶戶都用浴鍋洗澡。鄉村馬路上,偶有叫賣聲:“賣鍋賣鍋,燒飯的鍋、炒菜的鍋、洗澡的鍋……”伴隨著鈴鐺聲一路過去,音調拖得很長。若是不解情況之人,定要疑惑:洗澡的鍋?那是什么鍋?可當地人是見怪不怪的。從前,浴鍋也是財富與地位的象征—家家有灶,卻未必都有浴鍋。浴鍋是蘇南一帶人家家中相當重要的器物,攀親談對象,除了考察有良田幾畝,也要看廚房是否具備一口浴鍋。老人說,早年間整個村子總共也只有幾口浴鍋。嚴冬時分,天寒地凍,通常是一戶人家添柴燒火,臨近的幾戶便拖家帶口一同前往沐浴。空手自然慚愧,通常帶些柴草過去,輪到自家時也要幫著添柴燒火。當然也需要等主人家一一洗浴完畢,才按親疏輩分、鄰里關系、長幼尊卑輪流入浴。一般都是家中長輩及男主人優先,其次是孩童,最后才輪到女眷,由此可見當時女性的地位。由于水越燒越熱,而且浴鍋不是浴缸,沒有單獨的進水口與出水口,所以一鍋水一般不做更換。冬日嚴寒,身上污垢又多,如果水實在渾得看不下去,就去掉一些渾水,再加一些清水,叫作“加湯”。有時水實在太臟了,就把渾水全部倒干凈再重新燒一鍋清水,這叫“換湯”。
鐵鍋的受熱和保溫效果都非常好,水冷了,只需張口喚一聲,便有人添柴加火,很快鍋里又是熱氣騰騰。冬日嚴寒,總有人洗澡慢,半天不肯起身,等的人急了,罵娘的都有。浴鍋很大,躺下一個成年人完全沒有問題。過年時宰了牲畜,還會用這大鐵鍋來燒水燙毛。洗凈浴鍋,就該收拾著準備過年了。過年同樣要洗浴,而這洗浴又有講究。年前可洗,一般是小年夜下午洗,然后除夕夜貼春聯、祭祀祖宗。初一初二不可洗浴、洗衣。當然,隨著時間過去,風俗也不似以往那么嚴謹,很多已經成為老輩人口中的傳說,年輕人聽了不過笑笑罷了。
這浴鍋,其實就是一口大鐵鍋,鐵鍋太燙,任你皮再厚也不敢用臀部去直接接觸鍋底,所以一般都放塊兒厚實的黑色大皮墊子。先擱置了皮墊,再擱置臀部,然后人便可以四仰八叉地躺下去了。自我記事起至今,家中的皮墊就從未更換過,可見其牢固程度。鄉村民風粗獷,兒時也不講究,浴鍋在廚房,出出進進的人多,多數人家又未安裝門簾。等我大了一些,總覺不妥,扯了塊兒舊窗簾遮掩了我家的浴鍋。時至今日,家中灶臺已全部拆除,母親仍舍不得丟棄那口老浴鍋,說是冬天洗澡暖和,又砌在了祖母家灶臺上,安裝了玻璃移門,看上去講究不少。
我生于這里,泡在這浴鍋中長大,卻已多年沒有親近過它。好似遠離的家鄉,被時光帶走的童年,可還尋得回來嗎?
一口浴鍋,見證的是蘇南的風土人情,刻畫的卻是我們祖祖輩輩的生活。也許有一天,有些東西終將消失,但也總有些東西是無法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