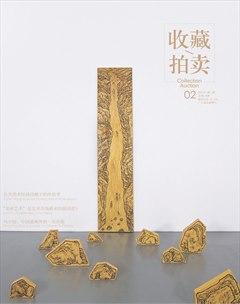馮少協,中國油畫界的一朵奇葩
余一



波詭云譎的大海,海面上烏云滾滾,軍艦馳騁;前方是一頭鬃毛濃密的雄獅,它迎風凝視,目光堅毅。
這頭雄獅近日頻頻見諸各大新聞。這正是廣東畫院副院長、油畫家馮少協歷時兩個月才完成的力作《中國,崛起!》。如以往一樣,不管是2003年的《關注中國文化市場》,還是后來《中東的鴿子》《百年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等系列作品,或如今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鐘南山》《中國,崛起!》,馮少協的每次出招都讓美術界措手不及。
在當代畫壇,有些畫家陷入了教條主義、有的為了參展,很多畫家效仿全國美展獲獎作品的樣式,或陷入模仿某些名家固有的一種繪畫技法,疑似呈現千篇一律的態勢,許多作品缺少思想內涵,難以引起觀眾的共鳴。而馮少協卻以獨特的視角,站在另一個維度,大膽刻畫重大社會現實題材,并且一直走在前列。范迪安曾撰文指出,“馮少協君在當代畫壇是另一種多面手,這些年來,他的繪畫關注現實,以反映戰爭與和平的主題為引領,畫出了大批內容豐富,意涵鮮明的大幅作品”。
用作品說話的藝術家
很多人都聽過“馮少協”這個名字,但少有人能在公共場合或展覽上看到他的身影,這是藝術界對他的基本印象:馮少協到底是哪個人?混跡藝術圈多年的筆者也深有同感,在各類展覽上與馮少協作品已打過多次照面,卻仍不識君。
采訪一開始,馮少協就回應了這個問題:“我從來不在公共場合刷存在感,一貫只用作品說話。”云淡風輕之余,讓我對這位機關出身忽而轉行做專業畫家的60后又多了幾分好奇。
1964年,馮少協出生于廣東普寧的一個鄉村,自小就在鄉中小有名氣,17歲左右在農村就能靠給老人畫炭像掙錢,一個炭像10元錢,他記得有一次一天就畫了5幅掙了50多元錢。后來得到普寧名家馬小其、林世嫻老師的啟蒙指引,開始走向專業道路。而初次讓馮少協在藝術界嶄露頭角的作品應該是《牛的眼淚》,這是他在佛山市城區文化館任美術干部時所畫的,這幅作品是1989年代表廣東上送第七屆全國美展的作品。1991年又創作油畫《黨魂》獲得省建黨70周年銅獎。隨后馮少協便封筆、下海、從政,此后的10年間沒有再從事美術創作。
馮少協曾擔任基層文化局的副局長,分管文化市場工作,作為文化市場最前沿的管理者和參與者,他看到文化市場混亂的一面,深感網吧、游戲機、歌舞廳等外來文化對中國青少年的影響和對社會風氣的腐蝕。憂患意識讓馮少協用審視的態度觀察這一社會現狀,并再次拿起畫筆將現代人的生活狀態通過繪畫語言表現出來。2003年,馮少協這組作品《關注中國文化市場》在中國美術館展出,這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個展,頓時就讓整個美術界為之一震。展出之際,京城不少著名的藝術理論家群集美術館,以罕見的態度肯定馮少協的新方向。著名美術評論家水天中為這組作品寫了評論文章《凝視黑夜》給予高度評價。馮少協也首次被《美術》雜志定位為“新批判現實主義畫家”。
當時,《美術》雜志2003年第9期編者按這樣描述:“社會主義時期仍然需要批判現實主義。但它的性質和‘政治波普與‘玩世現實主義完全不同,它的批判性指向不是革命歷史、革命領袖和健康向上的社會主義真善美,而是一切阻礙社會進步的腐敗的變態的異化的假惡丑現象和觀念。在當今世界畫壇和中國畫壇上,青年油畫家馮少協的新批判主義繪畫的橫空出現,是罕見而獨樹一幟的。”
馮少協就像一匹黑馬,一夜之間沖到中國藝術的最前沿。時隔近二十年,當我們如今再回看這組創作,當時馮少協把波普藝術的拼貼、宣傳畫的樣式和油畫綜合起來探討繪畫語言的做法,那超前的當代藝術觀念,至今仍令人為之一驚。
自中國美術館第一次個展開始,馮少協一鼓作氣。2004年又開始創作《中東的鴿子系列》,這是中國畫壇上少有的關注世界重大事件的作品。《中東的鴿子系列》2006年6月在中國美術館展出,美術館館長范迪安撰寫前言并親自布展,展期罕見的長達21天,當時的外交部部長李肇星還前往觀看并題詞。展覽期間,美術界和文學界還分別在中國美術館和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了研討會,足可見該展覽的重要性。藝術評論家楊小彥在《中國油畫中的馮少協現象》一文中曾評論:“這一回馮少協不再像創作《關注中國文化市場》那樣,僅以現實圖景為創作的依據,而是用藝術來向國際發聲,打破了藝術家不關心國際形勢的陳詞濫調,以積極的態度,首度對一個影響世界和平的局部戰爭發出中國藝術家的強烈聲音。”
兩組作品,兩次展覽,讓馮少協成為中國油畫的一個典型。此時,馮少協的繪畫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他開始敏感于今天的世界,專注于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他的畫面也呈現出了大視野、大關懷、大處理。這種勇氣、魄力與膽略在當時的美術界是極少有的。
2007年馮少協調任廣州畫院,2013年又調任廣東畫院,自此走上了專業畫家的道路。
宏大敘事中的“煙火氣”
從2003年的《關注中國文化市場》,到《中東的鴿子》《百年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等系列作品,再到如今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鐘南山》《中國,崛起!》,我們觀察到馮少協筆下作品呈現出重大題材、宏大敘事、當下關懷、中國氣派這幾類特征。確實,馮少協用美術作品切入現實的膽子非常大。
21世紀中國油畫創作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但似乎那種對現實的人文關懷卻被沖淡了,個性逐漸消解了集體意識。如此態勢,多少畫家的畫布上還能堅持藝術本身的社會責任?
“一個藝術家應該對這個時代的社會真實狀態發言。大型主題創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面。一個畫家,真的有能力的畫家,應該多畫一些能夠留給歷史的作品。藝術不僅僅風花雪月,不僅僅表現個人的小情感。那些東西作為觀賞、體現日常的生活樂趣,也是很好的。但作為一個畫家,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畫家,還是要站在歷史、文化、家國情懷的高度來看待現實,從而創作一些好作品。藝術界流行寫生和主題創作,這是好事情。但是我認為,每個人的角度應該不一樣,當下主題創作主要的問題,是雷同太多。”馮少協說。
在當下的融媒體、全媒體時代語境中,大數據圖像對于美術創作的影響深入而廣泛,幾乎無處不在。“畫照片”的問題成為最為集中的問題之一,一時間對于“畫照片”現象的關注與批判,也成為當代畫壇的顯學與令人矚目的現象。主題創作陷入“圖像”的繪畫,如何解套與破局?
對此,馮少協表示:“‘圖像與歷史的關系甚為緊密。無論是歷史題材還是現實主題,主題性繪畫創作往往具有情節敘事性。網絡時代,我們無法避免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影像視覺圖像,如何充分‘消化當代媒體圖像文獻,如何在大量歷史圖像文獻資料中探尋藝術意象,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想象之間的關系,是作者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去年12月,馮少協創作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鐘南山》被中國美術館收藏,曾引發廣泛關注。而在此之前國油版雕都存在了不少畫鐘南山的作品,馮少協取勝關鍵即是宏大主題背景下,還側重表現了鐘南山先生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感以及復雜的內心世界,這是一種細節真實的“煙火氣”。“如果不能表現人物的思想和靈魂,僅僅是畫得像,有什么用呢?直擊心靈的繪畫從來就不是簡單地臨摹”。這件作品的成功正是表現和捕捉到了創作對象中內心的復雜性。
馮少協的創作,觸發點看似都是偶然的。比如畫鐘南山是看到新聞片段、畫獅子是開車時聽到旁邊在播放的老歌。但是這種偶然也是必然。因為從年輕時開始,馮少協就是一個關注時事的人,尤其關心國際新聞,至今都還保持著每天抽空瀏覽國內外新聞的習慣。“兩個月前的一天,我在開車聽新聞的時候,從旁邊駛過一輛車,傳出那首曾經膾炙人口的粵語歌《萬里長城永不倒》。我馬上聯想到最近正在發生的一些國際新聞事件,頓時激發起一種創作的欲望。”
馮少協這種對宏大敘事的駕馭能力,是因為他骨子里的赤誠之心。馮少協就是這么一位具有敏銳洞察力的關注現實、關注前沿的畫家,擅于將社會現實和個人情感融入畫面向觀者傳達精神的力量。他總是不安分守成于以往,不斷給業界以新的刺激。還是那個畫畫的農民
陳履生稱馮少協是中國油畫界的一朵奇葩。
確實如此,馮少協畫畫向來都是按照自己的“套路”,獨來獨往,從不聚群,也從不進藝術界任何圈子,不懼怕非議,人不裝也不飄,幾十年來都是一樣,走著其他藝術家沒走過的路。偶爾給生活來點調劑,畫畫荷花等具有觀賞性的閑情之作,偶爾也看看電影。
“任何人不應該以個人審美標準去衡量或要求別人怎么畫,也不要去小看任何一個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從專業畫家到業余畫家,只要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在畫畫,就值得我們的尊重和鼓勵。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畫得很好,但我覺得自己就是跟別人不一樣。我喜歡按照自己認為比較合適的方式進行創作,至于行不行,留給時間去判斷。畫畫這個行業就如同農民耕田一般,你種番薯,我種蘿卜,沒有誰好誰壞。”馮少協坦言。
如今擔任廣東畫院副院長的馮少協在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之余,精品力作仍不斷輸出,其創作精力之充沛,令人嘆服。幾米高的大畫,他還是一個人爬上爬下。他媽媽曾在接受電視臺采訪的時候跟記者說:“我這個兒子從小是不用睡覺的。”經常通宵畫畫,還引來樓下鄰居投訴“畫畫的筆扔在地上吵到孩子休息了”。
至此,筆者突然想起剛進辦公室那會對馮少協的初印象:西裝革履、一本正經、有距離感。“藝術家難道都要剃光頭留胡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設,我是從公務員隊伍出來的,我不會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藝術家,毫無意義。”兩個多小時的交談,發現原來那頭雄獅背后的創作者也很有趣,這才是那個真實的馮少協。
綜觀馮少協的美術創作,或許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一句是美術評論家邵大箴所說的“馮少協用美術作品切入現實的膽子非常大,他有這個能力”,而另一句則是著名畫家吳長江對其作品的評價“沒有聲嘶力竭的吆喝,藝術家以不動聲色的方式重構了屬于他的歷史、表達了他的訴求”。從機關公務員到專業畫家,馮少協一路走來風風雨雨。正是這種數十年如一日的專精,令他的作品能更好地詮釋生命中最本質的人文關懷。
但馮少協時刻提醒自己,這些都是假象,不管現在走得多遠都是暫時的,回到畫室,自己還是那個通宵達旦畫畫的農民,喝茶、吃外賣、看新聞、畫畫,日復一日。
(編輯/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