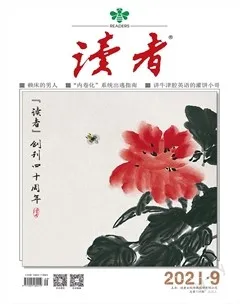當時只道是尋常
季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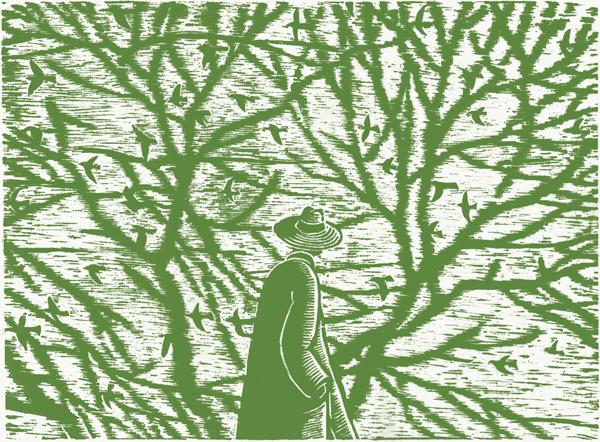
這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話,卻道出了幾乎人人都有的感覺。所謂“當時”者,指人生過去的某一個階段。處在這個階段中時,覺得過日子也不過如此,是很尋常的。過了一二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回頭一看,當時實在有不尋常者在。因此有人,特別是老年人,喜歡在回憶中生活。
在中國,這種情況更突出,魏晉時代的人喜歡做羲皇上人。這是一種什么心理呢?“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真就那么好嗎?人類最初不會種地,只是采集植物,獵獲動物,以此為生,生活十分艱苦。這樣的生活有什么可向往的呢?
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發思古之幽情,幾乎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到了今天,滄海桑田,無論世界有多少次巨大的變化,人們思古的情緒依然沒變。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十幾年前,我重訪了我曾待過十年的德國哥廷根。我的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夫婦還健在。但今非昔比,房子已捐給梵學研究所,汽車也已賣掉。他們只有一個獨生子,已在“二戰”中陣亡。此時,老夫婦二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十分豪華的養老院里。院里設施齊全,游泳池、網球場等等一應俱全。但是,這些設施對八九十歲的老人有什么用處呢?更讓老人們觸目驚心的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某一個房間空出來——主人見上帝去了。這對老人們的刺激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的來臨大出教授的意料,他簡直有點喜不自勝的意味。夫人擺出了當年我在哥廷根時常吃的點心。教授仿佛返老還童,回到當年。他笑著說:“讓我們好好地過一過當年的日子,說一說當年的事兒!”我含著眼淚離開教授夫婦,嘴里說著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過幾年,我還會來看你們的。”
我的德國老師不會懂“當時只道是尋常”隱含的意蘊,但是古今中外人士所共有的這種懷舊情緒卻是相通的。
仔細分析起來,“當時”是很不相同的。國王有國王的“當時”,有錢人有有錢人的“當時”,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當時”。在李煜眼中,“當時”是“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游上林苑的“當時”。念及往昔,他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哀嘆“天上人間”了。
我不想再對這個概念進行過多的分析。本來是明明白白的一點道理,過多的分析反而會使它迷離模糊起來。我現在想對自己提出一個問題:對于我的現在,也就是眼前這個現在,我感覺是尋常呢,還是不尋常?這個“現在”,若干年后也會成為“當時”。到那時候,我會不會說“當時只道是尋常”呢?現在無法預言。現在的我沒有什么不滿足的地方,但是,倘若捫心自問:你認為是尋常呢,還是不尋常?我真有點說不出,也許只有到了若干年后,我才能說:“當時只道是尋常。”
(田龍華摘自青島出版社《人生小品》一書,劉樹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