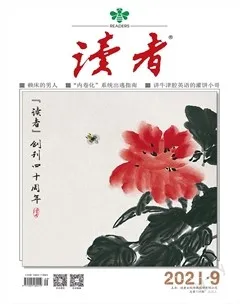創造的腳手架
萬維鋼

有一種可操作又比較高級的創新方法,被創新者在各個領域大量使用,而且外行一般看不出來。這個方法的特點是直接借鑒同行作品——但是不直接使用。
舉個例子,我們小時候讀《西游記》,總覺得這些故事實在匪夷所思,真不知道吳承恩是怎么想出來的!
現代學者認為《西游記》并不是吳承恩一個人的作品,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在于,《西游記》里的很多故事并不是作者一拍腦袋想出來的,而能在《禹鼎志》《玄怪錄》《酉陽雜俎》等傳奇筆記小說中找到素材原型。
魏風華在《唐朝的黑夜》一書中提到,比如,孫悟空在車遲國跟虎力大仙斗法,頭被砍下來也沒事的情節,就取材于《酉陽雜俎》中一個印度僧人“難陀”的故事。而斗法本身,也可能來自書中唐朝道士羅公遠和密宗大師不空和尚在唐玄宗面前斗法的故事。
《酉陽雜俎》里甚至還有一個關于蜘蛛精的故事。說有個叫蘇湛的人,被蜘蛛精迷惑,妻子和仆人去救他的時候,發現有只巨大的黑蜘蛛用蛛絲把他給綁起來了,仆人就用利刃割斷了蜘蛛絲……這不就是《西游記》里盤絲洞的故事嗎?
其實吳承恩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在《禹鼎志序》一文中說:“余幼年即好奇聞。在童子社學時,每偷市野言稗史……”果然從小就愛讀野史和奇聞。
所以像《西游記》這樣博大精深的傳世之作,絕不是一兩個作家坐在家里玩頭腦風暴就能寫出來的。吳承恩通讀了各種傳奇筆記,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哲學,映射了官場政治,把這些綜合在一起,才構建出一個龐大的神話體系。我懷疑他的寫作方法是先布局好這個體系,再安排大鬧天宮和取經故事。
《哈利·波特》《指環王》《冰與火之歌》,其實也都是這樣的。作家深入研究了歷史上真實的戰爭和宮廷政治,把這些東西和傳統神話糅合在一起,換成別的時間、地點、人物,甚至人種,新故事的素材就出來了。
所以創造的基本技術是“借鑒”。
1994年,喬布斯在接受《連線》雜志采訪時,談到了他對創造的理解:“創造就是把東西連接起來。如果你問有創造力的人是怎么做出東西來的,他們會有一點負罪感,因為他們并沒有真正‘做東西,他們只是能‘看到東西。觀察一段時間之后怎么做就會變得非常明顯。這是因為他們能把自己的經驗和新東西綜合起來。”
在這篇訪談里,喬布斯講了他對蘋果電腦市場定位的設計思想,其實也是借鑒的結果。我們知道蘋果電腦比基于Windows操作系統的個人電腦要貴得多,而計算性能也沒有頂級配置的個人電腦快,但是它的外觀設計和用戶體驗特別好。這種在價格、速度和用戶體驗之間的權衡選擇,其實是某個洗衣機品牌教給喬布斯的。
喬布斯一家曾經花了很長時間做市場調研,想買臺好洗衣機。他們發現歐洲貨比美國貨要貴得多,而且洗衣耗時更長——但歐洲洗衣機的優點是用水少、洗后衣物更松軟、洗滌劑殘留少。換句話說,歐洲洗衣機對美國洗衣機,就是蘋果電腦對個人電腦。喬布斯從歐洲洗衣機悟出的道理是用戶體驗比價格和速度更重要,而他悟出這個道理是跟家人連續兩周在晚餐餐桌上討論歐洲洗衣機的結果。
蘋果還有很多高級的借鑒。有人考證蘋果設計總監喬納森·艾維借鑒過羅馬尼亞雕塑家的作品,從糖果廠獲得過靈感,還曾經為了獲得設計輕薄型筆記本電腦的靈感向一位日本鑄劍大師學習。
創造是想法的連接,某些創造是同類想法的直接連接。那為什么我們總覺得有些好想法是橫空出世的呢?這是因為高明的發明人會故意不給別人留下線索。
最后說一個數學家高斯的典故。高斯是公認的天才數學家,是祖師爺級別的人物。他做出了很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別的數學家能看懂他的證明,但是完全想不出高斯是怎樣想到那些證明的。比如,數學家阿貝爾就曾經抱怨,說高斯“就好像走過沙子的狐貍,用尾巴抹去自己所有的腳印”。
高斯對此的回答是:“一個有自尊的建筑師不會在蓋好的房子里留下腳手架。”如果我們能看到每一個發明背后的腳手架,也許這些發明就不會顯得那么神奇了吧。
(夕夢若林摘自“得到App”,謝馭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