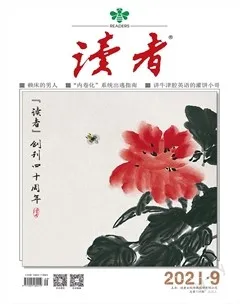小城賣魚30年
一
那時我還在贛州某報社做美食編輯,下了班,打算回家做道“贛南小炒魚”給家人吃,又怕自己不太會處理魚,便在魚攤前猶豫不決。最終,還是魚販先開的口。
“小伙子,想買魚啊?”
“嗯,準備做個小炒魚。”
魚販笑瞇瞇地說:“哎呀,阿姨這里正好有1斤多的草魚,做小炒魚正合適,今天都快賣完了,便宜點給你。”
得到我的默許后,她麻利地撈起一條魚,摔暈刮鱗,取出內臟。
我暗自打量起面前這個忙碌的女人:身材矮小,頭上頂著時髦的金色大波浪,和穿著的防水膠衣、膠鞋格格不入,棱角分明的臉上嵌了一雙丹鳳眼,唇上還抹了口紅。
這個阿姨還蠻講究的嘛,我心想。這時,她突然起身,把殺好的魚裝進袋子遞給我:“小伙子,魚我已經給你剁好了,回家沖一下就可以做。”
我打開一看,魚身已經切成了大而均勻的薄片,魚頭和魚尾整齊地碼放在上面。我付過錢,連連道謝,阿姨揮揮手:“下次再來啊!”
從那以后,我買魚都只到金發阿姨這里買,聽市場里的人都叫她謝阿姨。一回生二回熟,每次去買魚,謝阿姨都拉著我聊家常。
2020年10月,“社區團購”在贛南這座三線小城遍地開花,光我住的小區,就有3家平臺、8個自提點。架不住“擊穿底價”的宣傳,我也在平臺上買過1分錢一斤的臍橙、18元一斤的豬蹄和5元一條的魚。
“便宜就行了,隨隨便便解決一頓,又不用出去買,方便一點兒。”家人都這么寬慰自己。但我是對“吃”很看重的人,沒過幾天,我又來到了謝阿姨的魚攤上。
市場沒有原來那么熱鬧了,下午6點,大部分的攤販都收鋪了。以往這個時間,可是菜市場的“晚高峰”。我穿過一排冷清的商鋪,來到一盞白色長管燈前。謝阿姨面無表情地坐在魚攤上,見我來了,才打起笑臉:“小伙子,來了啊!”
我朝四周掃了一眼,坐在了謝阿姨剛才坐的椅子上,像平常那樣打開話匣子:“阿姨,現在到處都是社區團購的廣告,很多人在社區團購上買魚了,你知不知道?”
謝阿姨放下了手里的魚,看著我說:“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用手點了點周圍的攤販:“就是這個社區團購,搞得我們這段時間都沒生意做。”
二
謝阿姨本名謝寶珍,1970年出生在贛州的水西鎮。
當年的贛州除了城區,基本上都是山路。托了上天的福,謝阿姨家離贛江并不遠,每逢農歷雙數客家人“赴圩(集市)”的日子,夫妻倆就去江邊買魚。買來的魚用搪瓷盆裝著,再用擔子挑到贛縣、虎崗等離江邊較遠的鄉鎮去賣。
那段日子雖苦,但講起來,她眼睛卻是閃著光的。
1993年,贛州衛府里改造成為農貿市場。謝阿姨認為機會來了,便和丈夫商量,用賣魚存的錢,租了一個小商鋪。如今看來,她的決定是對的。市場建成后的很長時間,逛衛府里市場都是贛州人的潮流。
“那時候生意好哇,最多的時候我們租了6個鋪子!”謝阿姨翹起大小拇指比了個“6”。掙了錢的謝阿姨在水西蓋了一棟房子,成了當地最早蓋水泥房的人家,逢年過節,親戚都聚到她家。
然而,舒坦的日子并未持續太久。1999年,謝阿姨的丈夫患上了腸癌。積蓄都拿去給丈夫治病了,往時逢年過節必到的親戚開始躲著謝阿姨,怕她管自己借錢。家里除了當初蓋的水泥小樓,什么都沒有了。

丈夫去世后,她打算在僅余的攤位上繼續做下去。好歹她也是老商販,熟人多,門路廣,前些年開拓市場,維系了一批固定的采購商,一個月穩扎穩打也能掙6000多元,若碰上酒店、大排檔進貨多,還能賺更多。然而如今看來,這個目標是越發不可能實現了。
三
團購App頁面上閃著“今日紅包福利”,點擊后便彈出信息:您已獲得85.59元,推廣提現。還有1分錢一份的蔬果,做任務就能領。
我問謝阿姨怎么看待這些營銷策略,她不以為然地說:“雖然我做的這個是小生意,但是做生意的人都一樣,是不可能虧的。”
聽她說完,我一陣默然。到家后,我的內心良久不能平靜,思來想去,向單位請了4天假,決定去謝阿姨的攤位上幫忙。
第二天早上,我6點就來到謝阿姨的魚攤前,但還是晚了一步——謝阿姨的魚攤在凌晨3點就忙開了。天還沒亮,她就拿著酒店的預定單,去倉庫逐個備貨。有條件的大酒店一般都有養魚池,送活魚去就行;連鎖餐廳和大排檔則沒有,她要一條一條把魚殺好,去鱗去內臟,打好包,等酒店的人來取,或是在午市開業前送過去。
等我趕到時,她已經把這些活忙完了。
12月底那幾天,贛州只有3攝氏度,菜場的陰暗潮濕讓寒冷變得更加刺骨。謝阿姨坐在椅子上,瞇著眼,滿是老繭的手凍得通紅。
早上7點30分,天亮了,按理說,該到了老頭兒、老太太集體出門買菜的時候,可我環顧四周,發現市場依舊冷冷清清。
時針指向10點,終于來了第一位客人。他要了一條雄魚,我穿好圍裙,學著謝阿姨的模樣,麻利地從水里撈出一條魚。
刮鱗是個細致活兒。我翻來覆去刮了幾遍,又從上到下摸了一遍,確保都干凈了,再從魚頭處下刀,把魚剖開,除去內臟,將魚泡單獨拎出,給客人留好。
把魚遞給客人后,我們收到今天的第一筆進賬:39元。我脫下圍裙,理了理沾滿魚鱗的頭發,謝阿姨望向我,笑著問:“好玩兒吧?”
之后陸續來了兩三個客人,買的都是一斤多的草魚。有一回,客人在攤前駐足,我微笑著迎上去:“師傅,您要什么魚?”
“小伙子,你們這鱸魚和草魚怎么賣哦?”
“草魚7元錢一斤,鱸魚13元一斤。”
話音剛落,那人頭也不回地走了——在社區團購App上,鱸魚9.9元一條,草魚一斤只要2.99元。
雄魚賣出的39元,竟成了當天最大的一筆零售額。
四
在魚攤幫工的第二天,我依舊是早上6點到。
家人覺得我去幫工實在是多此一舉,“隨便看幾篇報道也能寫出來”。我沒理會,想著做事還是要腳踏實地。
這天有5家餐廳訂了貨,但都沒有配貨員,要謝阿姨親自送過去。我是美食編輯,對贛州的餐廳了如指掌,便主動攬下送貨任務。謝阿姨答應了:“到10點沒人來買魚了,我跟你一起去。”
10點過后,果然沒客人了。訂貨的5家餐廳在我供職的報社做過推廣,我和幾位老板都頗有交情。然而那天,作為他們的“供貨商”,我突然感到渾身不自然——據我所知,他們進得最多的草魚和鱸魚,到了夜市就會搖身一變,成為招牌菜“贛南小炒魚”和“炭烤深海鱸魚”,賣到48元或者88元一份。
生意做得最大的時候,謝阿姨曾經“拿下”過贛州大部分餐廳。如今還從她這兒進貨的,就剩這么幾家了。“餐廳什么便宜買什么,在那個社區團購上買,第二天貨就送到門口。之前有幾家都是我送的,現在都不來了。”
我安慰她:“三分天注定嘛。”謝阿姨悶悶地嘆了一聲,不說話了。電動三輪車停在餐廳門口,不等我搭手,她便抬起幾十斤重的筐,一步一步挪向后廚。
送完魚,我們回到市場繼續營業。謝阿姨的手機響了,微信收款提示她已收到了當天的第22筆收款,后面是當天的營業總額,共計774元。接下來再送一家麻辣燙店訂的魚,當日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麻辣燙店開在商城步行街,是家新店。我提著切好的魚片進了門,老板是個胖胖的女人,她接過袋子,輕聲囑咐我:“明天我們那單暫時別送了。”
“啊,為什么?”
見我一臉疑惑,她將我引到一個冰柜旁,用手指了指冰柜角落里堆著的袋裝魚片:“我們先用這個,團購上買的,看看好不好。”
五
幫工的最后一天,我打算早點到。凌晨2點30分,鬧鈴響了,一掀被子,我瞬間就后悔了——太冷了。那天,靠近廣東的贛州,氣溫已降至零下1攝氏度。
來到倉庫時,謝阿姨已經忙開了。見我來,她傳給我幾張單子:“按照上面酒店的需求,一條一條拿,殺好,用黑袋子裝。”
倉庫很昏暗,在白熾燈光的反射下,每條魚背都是黑的,很難分辨。想著反正每種魚都要,我先撈上來幾網。大小不一的魚在潮濕的水泥地上甩尾跳躍,污水飛濺在頭發上、臉上、衣服上,我們倆毫不理會,用袖子擦一擦,就繼續忙手上的事。
說實話,之前我沒殺過生。初時殺魚,我連看都不敢,要是旁人在邊上觀摩,一定覺得場面滑稽——一個大小伙兒蹲在地上,緊閉雙眼,抿著嘴唇,一手抓魚,一手拿起刀背,對著魚頭猛砸。
殺多了也就麻木了。到后來,我幾乎是面無表情地把魚拍暈,刮鱗,去內臟,然后丟到一邊,一條,一條,又一條。
所有魚貨處理妥當后,已是清晨5點。昏暗的攤位里,我打開前置攝像頭端詳:我的眼角泛著血絲,頭發則貼在臉上,流下一道道猩紅的印跡,嘴里也是鮮腥的味道。我感覺自己好像一名午夜屠夫。
謝阿姨拍拍我:“小伙子,還好嗎?”
“不太舒服,想吐。”我說。
她讓我去洗把臉,漱漱口,還給我買了豆漿,說:“一開始是這樣,做多了就習慣了。”
這些魚送到顧客手上,就是無數人勞累一天后的晚餐、親朋好友間宴客送人的佳肴,也算是有好的歸宿——謝阿姨這么安慰我。
她說:“我們這些人,做的是殺生的活兒,所以更要善良。我賣魚賣了30年,沒做過虧心生意,我殺魚也是為了養活我的兩個女兒,這是天理,菩薩會原諒我的。”
想起十多年前人群熙攘的衛府里市場,我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只剩4個魚攤了。”謝阿姨說,“原來賣魚的有3排,12個魚攤,大家都搶著租,現在這里都沒人租了。”
那天的營業額只有446元,甚為慘淡。也許,這種慘淡日子也并不長久了。
臨走前,我問謝阿姨:“要是哪天你不做了,會去哪里?”
謝阿姨朝我一笑:“我就去找我大女兒啊,她老早就不讓我做了,覺得我辛苦,但我們是農村人,手腳閑不下來。”
我給她包了一個紅包,她卻怎么也不肯收:“你免費幫我做事,我還收錢,太不地道了。”
我拗不過她,就到隔壁商場買了些補品,放在魚攤上,便離開了。
告別謝阿姨時恰好是中午放學時間,看著嬉鬧走過的孩子,我感覺不到一絲波動,心情就像那天的天氣,陰冷而平靜。
(意 然摘自微信公眾號“看客inSight”,本刊節選,劉程民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