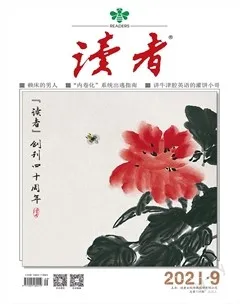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
沈蕓

老派是一種堅持,也是一種信仰。
3年前冬日的某天早上,一個電話打斷了我的思緒。來電者給了我一個號碼,要我與身在美國紐約的程太太聯(lián)系。
我想起來了,那是我爺爺?shù)耐馍骞霉迷崛A,她的丈夫程樹滋先生是華爾街的老銀行家。2010年我們在上海分手后再沒聯(lián)系過。電話接通了,姑姑悲傷地說:“樹滋在9月過了……”她自己在醫(yī)院里度過了生不如死的幾個月,找回了以前的保姆周阿姨,回到新澤西養(yǎng)老院。她很想念我,懷念在上海老房子的時光。
姑姑交代我一些事情以后,周阿姨接過電話告訴了我很多細(xì)節(jié),最關(guān)鍵的是,姑姑吃不到中國的東西,她的腸胃犯了思鄉(xiāng)病。
趕在元旦前,我寄給她一些山核桃仁和柿餅。姑姑很高興,她對我說,她很想家,想吃冬筍,還惦記著我從嘉興給她帶的肉粽子。“那真是美味極了,回味無窮,我一直都記著。”
姑姑吃不慣西餐,像生菜沙拉、土豆泥和牛排一類,她連看也不要看。她住的養(yǎng)老院很高級,每天提供兩頓飯,而她只喝其中的雞湯。周阿姨說,你姑姑會自己燒菜,她很節(jié)省,用冬筍頭熬骨頭湯,前面的嫩尖燒油燜筍。聽著這些,我一下子感覺自己燒筍時扔掉的老頭,太浪費(fèi)了,有些暴殄天物。
姑姑喜歡的冬筍和肉粽子,可不是輕而易舉能帶進(jìn)美國的。我想來想去,想到我們的朋友——在上海的張先生,他有家人在法拉盛,可以托他弟弟在中國城買,然后寄到新澤西。果然,張先生聽說95歲的老太太需要幫忙,非常熱情。我解釋說,姑姑的兒女已經(jīng)是華裔美國人,不太會買中國的食品,張先生十分理解。后面的事情一切順利,姑姑在春節(jié)前收到6個冬筍和6個粽子,心情大悅!她吩咐周阿姨,年夜飯一定要吃粽子和冬筍。姑姑親熱地說,我讓她感到了親人的溫暖。
這以后,每隔十天半個月,我都可以得到姑姑的消息,譬如她想吃炒豆芽菜和番茄炒蛋,可是要等她兒子兩周去一次中國超市,把豆芽菜買回來;她去燙頭發(fā),順便到法拉盛吃了上海點心、餛飩和小籠包,回來的路上,她一直在埋怨小籠包不好吃;感恩節(jié)去兒子家聚餐,她要提前搭配好衣服,化好妝,還要戴上墨鏡和披肩,“這是風(fēng)度”。周阿姨說:“你姑姑很講禮數(shù)!”
從我7歲第一次見到五姑姑起,我們倆的關(guān)系從未像現(xiàn)在這么親密過。我跟姑父倒是聊過天兒。姑父最得意的手筆,是改革開放后他為中美兩國銀行界牽線搭橋,為此,他們夫婦被邀請參加老布什總統(tǒng)的就職晚宴。姑姑給我看過她一身絲絨旗袍,盛裝出席的照片。
過了一段時間,周阿姨說,你姑姑不對了!她經(jīng)常出現(xiàn)幻覺,總是覺得房間里有她先生的影子,她會對著空氣說話,口氣像是在跟先生對話。沒等我把這個信息消化掉,姑姑就正式通知我,她要跟周阿姨一起回中國養(yǎng)老,葉落歸根!
2019年5月,姑姑終于抵達(dá)上海虹橋機(jī)場。“我決定在這個時間回來,我要吃上今年的楊梅,想了好多年。”姑姑把她在美國的家產(chǎn)分給子孫,只帶了日常用的衣物和兩部輪椅,安排做體檢,辦理護(hù)照機(jī)票,登上飛機(jī)頭等艙,一路睡著就到了上海。她不愧是在美國“黃金時代”打拼出來的成功人士,處理事情有著驚人的速度。
姑姑的歸來,讓我的內(nèi)心很幸福。在她的身上,我再一次觸摸到老輩人的脈搏,感受到家族血脈在流淌!
在每一個綿延不斷的古老家族里,都會有一位老奶奶,她們可以是遠(yuǎn)在天邊、彪炳史冊的名流,也可以是弄堂里再普通不過的張家姆媽、王家阿婆。她們會抱怨吃咸肉菜飯時,怎么能缺了燉好的黃豆骨頭湯,也會百般糾結(jié)有客人來吃飯時要加上哪兩道葷菜。在她們看來,這些瑣碎不是小事,而是關(guān)乎規(guī)矩和臉面。
像這樣生活上不湊合,遇大事又扛得起江山的老太太,都是見多識廣的神仙。《紅樓夢》里的賈母,《唐頓莊園》里的老夫人,英國王室的女王……在眾人焦躁不安時風(fēng)輕云淡,就是老派人無人可及之處。在這一點上,家和國是一樣的。
(嶺上白云摘自《文匯報》2021年2月20日,本刊節(jié)選,陳 曦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