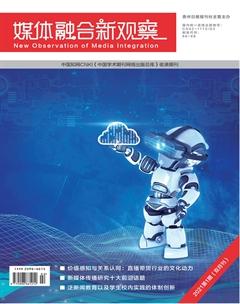移動短視頻中的“網紅”城市現象研究”
周婷婷 曹彥
摘要:以抖音為代表的短視頻媒介平臺打造了“爆款城市”和“網紅景點”,引發青年群體用戶的“打卡效應”。在虛擬層面,物理的城市空間被建構成特定的超真實、界面化、符號化的“抖音之城”,產生一種視覺奇觀;在現實層面,“網紅”效應也空前地帶動了旅游消費增長和城市景觀再造,形成消費奇觀。這種對城市空間的自主性敘事、個體文本生產和身體參與契合了青年亞文化的追求個性和解構的精神以及想象的自我賦權,但這種消費狂歡在政府、資本與媒體的合謀下最終成為一種媒介奇觀。
關鍵詞:短視頻 媒介奇觀 網紅景點 城市空間 青年文化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成熟,移動短視頻改變了傳統視聽媒體和圖文內容的生產與傳播邏輯,成為人們認知和表達的手段之一,也成為人們在虛擬空間中極其重要的存在方式,并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情境來型塑人們在現實社會的形態或行動。
2016年起,短視頻市場進入高速發展期,用戶規模保持強勁增長。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短視頻用戶規模預計達到7.22億人,市場規模也將突破400億元。截至2020年6月,行業頭部抖音平臺的月活用戶達4.97億人。[1]根據企鵝智酷的《快手&抖音用戶研究報告》,抖音用戶以24歲以下的年輕用戶為主,占75.5%,短視頻用戶認為抖音的品牌調性是潮酷和年輕。[2]
當下,以抖音為代表的短視頻媒介平臺正以全新的視聽體驗深度嵌入用戶的生活場景。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抖音與城市旅游消費、城市形象營銷相結合打造了“網紅景點”和“爆款城市”概念和產品,引發以青年群體為主的用戶大規模的關注和追捧。據統計,截至2018年9月,抖音上存在11個視頻數量超百萬的“爆款城市”,重慶、西安、成都三個西部樞紐城市的相關視頻播放量位居前三,超過一線城市,重慶更是被稱為“抖音之城”。[3]
短視頻成為城市形象展示的新窗口,抖音“網紅城市”是對城市空間的重新定位和二次生產,它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建構了人們對城市的視覺想象,又影響了各方力量對于實體空間的再度謀劃。
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20世紀60年代將社會視覺圖景內容稱為“景觀”,他批判“景觀”成為了人與人的中介和社會關系。這里的“景觀”被理解為媒介傳播所生成的圖景,是一種具有主體性的、有意識的表演和作秀。德波稱,“新聞或宣傳、廣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費”都是一種社會景觀,“景觀構成了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生活的現有模式。”[4]
根據當代社會的特征,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發展德波的理論,提出“媒體奇觀”的概念,他認為媒體奇觀是由媒體主動制造出來的具有戲劇化情節的媒體文本,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吸引受眾眼球,消費受眾注意力。[5]凱爾納分析了美國企業和政府以大眾傳媒為渠道制造的具有戲劇性的媒介事件,以此透視美國社會文化。顯然,“媒體奇觀”描述的是一個圍繞著視覺、商品和戲劇性事件而組織起來的媒體和消費社會,是一種視覺奇觀和消費奇觀的交織。
在當下的泛媒介化階段,介入制造奇觀的不只是大眾媒體,還有社交媒體平臺及其所召集的用戶群體自身。拓展這一理論有助于我們批判性分析短視頻媒介所構造出的擬象城市和“打卡式”消費現象。在移動短視頻的“網紅景點”敘事中,城市場景是如何被重構的?形成了怎樣的城市情境?資本搭建的線上社區平臺又是如何帶動線下狂熱消費的?而媒介平臺、政府官方、大眾媒體和青年用戶群體在其中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些問題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二、視覺奇觀:短視頻中網紅城市空間的符號重構
在傳統視聽傳播媒體時代,城市宣傳片總是被官方和專業人士掌握;而移動短視頻的輕資產屬性、低技術門檻、小屏幕特征,使普通用戶加入城市空間敘事,并使這種敘事充滿了解構和個性化意味。以往龐大團隊動用專業機器所精細制作出恢弘壯美的全景式城市形象,被豎屏式的“界面化”的城市場景所取代。在個體身體的參與下,城市通過各種界面被場景化,原本不知名的景點或對于當地人而言日常化的空間被賦予了奇特的符號表征。在這樣一種新的視覺奇觀中,人們對城市的想象被重新建構。
具體而言,城市空間在短視頻中被重構是現實到虛擬的場景轉換過程。首先,用戶進入抖音頁面,點擊“+”號開拍,可翻轉鏡頭、調整速度。通過手持或運用自拍桿,通過身體自由的位移走動、鏡頭視角的變化,用戶將自己的鏡頭之眼對準城市空間,或將自身置于城市背景之中,展現自身與城市的關系。在這樣一種身體參與之下,個體既是拍攝主體,也是敘事主體;城市既是物理空間,也是符號背景。身體在城市空間的“場景”中被觀視,[6]城市成為意義再生產的場域。
其次,在視頻實時合成上傳后,用戶可以在平臺提供的素材庫內選擇添加特效道具、封面、濾鏡、貼紙、字幕、美顏效果等對視頻內容進行美化,多種多樣的效果組合使短視頻的內容表達變得五光十色,酷炫、奇異或搞怪。除此之外,平臺會根據拍攝內容自動推薦匹配的音樂,用戶也能自主搜索音樂或在分類歌單中進行選擇。而平臺的音樂庫早已將音樂切割為幾十秒的片段,使其適合于短視頻傳播。在豐富的視聽修辭的組合運用下,被界面化的城市場景進一步被定格為小屏幕的視覺奇觀。
在抖音、頭條指數與清華大學國家形象傳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究室聯合發布的《短視頻與城市形象研究白皮書》(2018)中,城市形象在抖音中的符號載體被總結為BEST,即BGM(音樂)、Eating(本地飲食)、Scenery(景觀景色)、Tethnology(科技感的設施)。抖音中的“網紅城市”多數在視頻中呈現出BEST多個符號載體。[7]
比如,伴隨方言歌曲《西安人的歌》的流行,西安城墻腳下永興坊摔碗酒在抖音爆紅,截至2020年10月,話題#西安摔碗酒#播放量達1433.8萬次。視頻中,游客排隊喝酒摔碗,碎碗之山高高堆起,這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情境。在重慶,重慶輕軌李子壩站本是普通的交通設施,卻在抖音的傳播下成為外地游客的新晉打卡景點,輕軌在氣勢如虹的配樂下穿樓而過,更有“震驚外媒”“中國科技”“中國實力”的話語豐富了景點的內涵意義,話題#重慶李子壩播放量達2.5億次。重慶洪崖洞被宣稱是宮崎駿動漫《千與千尋》場景的現實版,其話題#洪崖洞播放量達5.8億次,#洪崖洞夜景播放量達9608.2萬次。而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南寧,其“電動車自行車大軍”的街景一度吸引了大量用戶的注意力,配以《騎上我心愛的小摩托》背景音樂,相關短視頻被大量制造出來,南寧成為“城市形象短視頻播放量TOP30”中唯一進入前十的二線城市……[8]這些或邊緣或日常的城市空間和場景被重新挖掘出來,與個體身體的參與產生碰撞,在移動鏡頭下被“玩轉”著,被賦予或改造了意義,一改傳統媒體時代標準化的城市宣傳和常規的旅游方式。
在抖音所搭建的技術平臺和虛擬社區中,城市作為現實生活場所或歷史文化載體的意義被消弭,特定的界面化的虛擬“抖音之城”——充斥著時尚和娛樂的欲望都市被超真實地建構出來。城市空間影像重構了人們對城市的感覺方式和思維方式,形成城市的虛擬文本。[9]再配以洗腦的“抖音神曲”等流行符號,個別景點的視覺文本便成為爆款和流行物。
但需要審視的是,用戶群體生產視頻文本的創意和意義并非持續而多元,更多時候只是陷入盲目的模仿秀,生產出重復的文本。比如,在抖音話題#西安摔碗酒#下,滿屏都是高度相似的場景——排隊、喝酒、摔碗;話題#重慶李子壩#下面,統一都是輕軌到達李子壩站時穿過居民樓的場景,任意點開的一個視頻都與其他的視頻沒有本質區別,都是按照同一模板進行機械復制。隨著跟風模仿的視頻情境大量堆積,物質城市與虛擬城市的界限被模糊,某些爆款景點在用戶的獵奇中被符號化地等同于城市本身,城市的厚重文化和多元意義反而被消解。另一方面,用戶在觀看“抖音之城”的過程中處于一種沉浸式的在場體驗,上下刷屏的慣性以及科技感和音樂等視聽元素的運用使觀者陷入癡迷,在這過程中,觀者對城市的想象力也在一個個話題和標簽中被設限了。
三、消費奇觀:短視頻帶動網紅城市的旅游消費
根據重慶日報、攜程集團聯合發布的《2018年重慶上半年旅游大數據報告》,2018年上半年,重慶接待境內外游客超過2.6億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超過1900億元,游客接待量、旅游總收入增幅排名全國前列。[10]而根據中國旅游研究院與攜程聯合發布的《中國在線旅游發展大數據指數報告2018》,西安位列全國熱門目的地第三位,僅次于上海和北京。[11]城市旅游產業的飛速發展與市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城市的文化產業及公共交通系統的發展等因素息息相關,但毫無疑問,以抖音為代表的短視頻對相關網紅城市所帶來的宣傳效果是促發全民“打卡式”旅游的直接因素。
抖音帶動城市旅游,這是一個從線上到線下、虛擬到現實的過程。通過算法機制,用戶在抖音社區接觸到大量“個體層面的文本生產和集體層面的社群互動”,[12]在社交中萌發了參與的心態。
通過算法智能推送機制,用戶拍攝的城市旅游類短視頻本身如果受關注多即會被推送給其他更多用戶,從而能夠持續發酵。而用戶如果觀看帶有某個話題標簽的城市旅游類短視頻,系統會源源不斷地給該用戶精準推薦更多的相關主題和內容。在這一過程中,大量用戶生產的虛擬文本,即對某個城市空間或景點的視聽再現,被聚集到一個屏幕中接收。當大量的個體文本生產被一個話題的標簽統籌時,它們又能夠在集體層面推動陌生人的社群互動和個體參與,觀看、點贊、評論、轉發的行為將多個屏幕前的主體勾連到一起,推動“流行物”的誕生。
相比于傳統的視聽傳播,移動短視頻的社交模式呈現出更強的交互性,而抖音平臺中由官方發起的同話題創作的“挑戰賽”則更能帶動用戶的參與興趣。在前所未有的視覺體驗和互動交流體驗的激勵下,用戶個體親身參與到群體行為中的欲望被激發,從而將想法付諸于實踐,參與到網紅景點的打卡和實地消費中,并完成自己個性化但頗具模仿性的文本生產,一方面傳遞自身“在場”的真實感,另一方面又通過選擇和粉飾畫面來使真實的景觀理想化。這時,場景又一次完成了從現實再到虛擬的循環轉換,網紅城市的擬象建構被進一步強化。
在抖音平臺的鼓勵機制之下,用戶們一起制造了一個個擬象城市景觀,推出了自我賦權的流行物。通過大眾媒體及其他社交媒體平臺的聯動傳播,“爆款城市”和“網紅景點”被生造出來,嵌入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模仿、跟風式的景點打卡使相似的視頻記錄成為大量碎片化的景觀堆積,它有助于刺激新的用戶因為獵奇和沖動而應邀加入,卻不再具有創新、個性化敘事以及尋找另類空間的意識。
“網紅景點”的傳播短暫地拉動了當地旅游經濟增長,但盲目追逐“網紅”經濟也出現了問題。人山人海的造訪對城市空間造成壓力,導致城市交通系統近乎癱瘓,也對景區環境產生惡劣影響。青年群體熱衷于花五塊錢排隊等待表演一次“摔碗酒”儀式,卻把意義從行為中剝離出去。除此之外,青海茶卡鹽湖的“天空之鏡”變成了“垃圾之鏡”;重慶洪崖洞的電梯前“排隊兩小時,打卡五分鐘”;游客在西安大雁塔地鐵站的“鋼琴階梯”拍攝短視頻干擾行人通行;杭州濱江公園的粉黛花海三天之內被游客踏平……移動短視頻用戶從最初對城市空間的重新尋找和開拓的愉悅、自主性敘事,最終淪為大眾趣味和資本利益的噱頭,消費主義至上的拜物教以及娛樂至死的群體狂歡。
四、“網紅”城市:媒體、政府、資本與青年的“合謀”
列斐伏爾在對空間的研究中提出,空間是一種生產的空間,各種生產關系或社會關系在這里匯集并再生產。[13]因而,現代城市本身就是一種復雜的媒介,這既是物理的空間,也是媒介和意義的空間,城市空間是權力的隱喻。在“網紅城市”或“網紅景點”的空間媒介中,青年群體的娛樂狂歡,大眾媒體宣傳城市品牌,地方政府發展旅游產業經濟,短視頻媒介平臺對用戶市場的爭奪和壟斷等力量相互交織。“網紅城市”的話語孵化于社交媒體平臺,既成為青年亞文化的一部分,又被官方政府和大眾傳媒的敘事模式利用,成為城市營銷和促進旅游業發展的一部分,而用戶從一開始就被短視頻平臺背后的資本看作是有利可圖的流量商品。這場原本看似帶有個性化解構意味的活動仍然落入媒體、政府與資本“合謀”的窠臼。
首先,資本平臺為“網紅城市”的孵化提供了最初的“搖籃”并在這一過程中收割流量、爭奪用戶市場。以青年群體為主的短視頻用戶一開始就是在抖音等新媒介平臺搭建的虛擬社區中進行自我與城市空間的展示,看似純粹的自我敘事說到底還是被局限在既有的規范框架內,遵循著平臺的流量規則和敘事框架,在平臺設置的極具參與性的話題和挑戰賽中,選擇平臺提供或推薦的工具特效、背景音樂等。這種機械的模仿秀在群體效應下成為青年人的狂歡,卻也陷入資本的陷阱中。每個用戶都在視覺體驗、參與和互動中被商業利潤所支配,為平臺增加了流量、加強了自身與平臺的黏性卻不自知。
其次,大眾媒體在這一過程中強化建構了“網紅城市”敘事,引導消費風尚和消費熱點。在大眾主流媒體的敘事框架下,“網紅城市”充滿新聞價值和宣傳價值,城市品牌的打造在這一過程中可以將“關注紅利”轉化成“發展動力”。[14]“網紅城市”看似是對傳統城市媒介形象的解構,但實際上只不過是創造了新一輪的“消費概念和消費模式”,而媒體所擔任的功能則是“消費引導”。[15]青年群體對“網紅城市”的消費越來越多是為了滿足不斷被刺激起來的消費欲望,通過消費來建構符號化的自我身份。普通民眾從一開始的主體敘事者被異化成盲目而狂熱的符號消費者。
第三,政府官方利用“網紅城市”話語大力推進地方旅游業并改善城市形象宣傳。雖說城市空間敘事的權力被開放化,從前被官方所主導的景觀的“屈從式消費”[16]被改變,但地方政府從一開始就并非完全的被動者。就西安、重慶、成都這些“抖音之城”而言,地方政府都善于運用互聯網思維,它們進駐抖音、注冊官方賬號,積極地同抖音展開合作,站在金字塔尖進行清晰的頂層設計,加快解決旅游業的管理困境。政府搭建了一個透明的網,將青年群體的亞文化行為收編成為主流的一部分。重慶李子壩輕軌成為“網紅景點”后帶來驚人的外地客流,渝中區政府甚至為此搭建觀景臺、增設LED屏幕以便外地游客“打卡”和獵奇;[17]西安市旅游發展委員會與抖音達成戰略合作,希望以此帶動城市旅游宣傳模式的創新;[18]西安和成都都進一步通過短視頻擴大了兵馬俑和熊貓這兩大海外傳播品牌的國際影響力。城市景觀為便于視覺消費而被政府重新設計和改造,而官方重視并展示相關的城市空間是為了改善地方形象、吸引資本投資。在這里,個體敘事最根本的目的是為國家敘事服務。
最后,青年群體本身參與到“網紅城市”的意義生產中,并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最終在視覺沉浸和消費狂歡中迷失了自我。“網紅城市”的興起契合了青年亞文化追求多元、時尚、解構和個性化的精神。他們借助移動短視頻平臺進行個體敘事,挖掘城市的日常空間,在虛擬表達和實地探索中改寫了城市空間的意義,追求區別于傳統城市宣傳的個性化體驗,企圖爭奪技術賦權和自我敘述的權利。但在平臺的流量機制下,個性化的敘事逐漸讓位于適合病毒式傳播的高度重復化的內容,自我敘事也被大眾媒體和政府官方所利用進行城市營銷。在消費主義的鼓吹下,青年對城市空間的主動探索,最后演變為容易被復制和模仿的機械“打卡”,以便于掀起一陣陣消費狂潮。
在這場視覺和消費狂歡中,媒體、政府、資本和青年在抖音這樣的社交媒體平臺中對接。青年群體展現了自我、愉悅了身心并想象了自我賦權,但其實一直與媒介平臺的商業利益相互邀約,同時輕易地被相關輿論所引導。[19]
五、結語
在媒介奇觀的視角下,抖音“網紅景點”的爆款現象體現了視覺欲望、娛樂、狂歡和消費主義的交織,其傳播過程呈現出現實——虛擬——現實的循環場景轉換。在虛擬層面,短視頻建構了城市空間中的另類視覺奇觀,使用戶沉浸于視覺符號的快感;在現實層面,短視頻的交互性和參與性也空前地刺激了青年群體的新型旅游行為和身體參與,形成模仿行為和“打卡”效應,這又成為一種新的消費奇觀。
“網紅景點”這個城市空間成為一種意義的媒介,地方政府、資本平臺、大眾媒體與青年用戶群體的各方力量在這里匯聚和博弈。青年群體在官方的邀約下入場,在給定的平臺規則內進行低成本的創作,在大量重復、碎片化的視覺生產中,這場看似個性化的解構最終也淪為一場隨大流的狂歡。
注 釋:
[1]艾媒大文娛產業研究中心.2020年中國短視頻頭部市場競爭狀況專題研究報告[EB/OL]. https://www.iimedia.cn/c400/74380.html.2020-09-18.
[2]企鵝智酷.快手&抖音用戶研究報告[R].2018.
[3][7][8]清華大學國家形象傳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究室.短視頻與城市形象研究白皮書[R].北京,2018.
[4][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M].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3-4.
[5][16][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奇觀——當代美國社會文化透視[M].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2-3.
[6]嚴亞,董小玉.城市空間“場景”中的青年媒介想象[J].南京社會科學,2017(04):113-117+132.
[9]嚴亞.想象與奇觀:城市視覺建構的文本轉換[J].新聞知識,2014(08):19-21.
[10]重慶市政府網站.2018年重慶上半年旅游大數據報告:80后90后游客占比39%民宿收入全國第七[DB/OL]. http://news.sina.com.cn/c/2018-07-09/doc-ihezpzwt8588335.shtml.2018-07-09.
[11]中國旅游研究院.《中國在線旅游發展大數據指數報告2018》在西安發布[DB/OL]. http://www.ctaweb.org/html/2018-10/2018-10-10-9-53-72932.html.2018-10-10.
[12]蔡騏.從窮游亞文化看場景時代的新媒體賦權[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38(12):124-128.
[13]胡翼青.顯現的實體抑或意義的空間:反思傳播學的媒介觀[J].國際新聞界,2018,40(02):30-36.
[14]單士兵.透過“網紅”光環,重新發現城市[DB/OL].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605/c1003-30035288.html.2018-06-05.
[15]蔣原倫.媒體文化與消費時代[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135.
[17]光明網.網紅重慶觀景臺:李子壩輕軌穿樓觀景臺開放[DB/OL].http://www.chinanews.com/life/2018/08-29/
8613316.shtml.2018-08-29.
[18]光明網.抖音和西安達成合作 攜手向全球推廣傳統文化[DB/OL].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8/0423/
c67737-29942910.html.2018-04-23.
[19]嚴亞,董小玉.規訓與抵制:大學生視覺形象重構[J].當代青年研究,2014(02):75-81.
(周婷婷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曹彥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