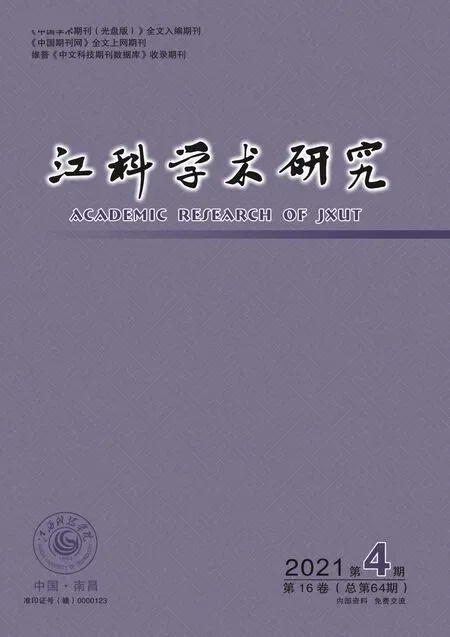從“軟性電影”論中的“機械要素”看都市電影意象的呈現
王希楠
20 世紀30年代是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時期,在思想陣地爭奪加劇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本土“思想論戰”。以內容和意識形態為創作主導的“新興電影”與以形式和感官娛樂為創作主導的“軟性電影”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理論交鋒,二者“論戰”涉及到電影的本質、電影內容與電影形式、電影的意識形態性、電影批評準則等許多問題,其產生的本源在于彼此政治觀、文學與藝術觀以及電影觀等方面的巨大分歧。為了更為客觀地把握這場所謂的“軟”、“硬”電影之爭,筆者將“軟性電影”的理論和創作主張重新進行了一番探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給“軟性電影”的歷史政治站位進行更名,也不否認在一個國家主權面臨危亡的時代背景下,刻意回避政治因素,一味強調藝術傾向性帶來的“現實退縮”。需要申明,筆者高度贊成左翼電影的民族主義、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立場。畢竟在民族危亡之際,如果藝術創作刻意避開現實問題,藝術作品不對這個時代的風云激蕩作出反應,從藝術本質的角度來說,則是忽略了作品與現實之間的互動關系與其價值。不過,若站在電影的現代性創作要求上來看,對軟性電影的客觀評價或許能夠幫助我們重新審視三十年代這場“思想論戰”本身的獨特意義。
一、正視“軟性電影”論的藝術地位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爆發后,民族矛盾劇烈加深。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電影界人士也紛紛加入戰斗中來。由于政治傾向的影響,“左翼電影”被看做是進步性電影(以夏衍、田漢、孫瑜、洪深等為代表人物),它反映了廣大勞苦百姓的下層生活樣態,并首當其沖將當時進步文學的反帝反封的思想主題引入電影領域,認為“要赤裸裸地把現實的矛盾的不合理,擺在觀眾面前,使他們深刻深刻地感覺社會變革的必要,使他們迫切尋找自己的出路。”[1]然而,“軟性電影”(以劉吶鷗、穆時英、黃嘉謨、施蟄存等為代表人物)此刻似乎以一種不合時宜的態度出現了——他們質疑甚至否定“左翼電影”的某些觀點,認為他們“內容重,描寫輕”,政治性和教育性太過高于電影的藝術性。而“左翼電影”則認為“軟性電影”論是不敢正視殘酷現實的表現,其所崇尚的趣味也不過是蒙蔽現實的催眠藥。由于政治的遮蔽,“軟性電影”論的地位在中國電影史上長期處于壓抑的狀態,被認為是反對電影為無產階級和工農大眾及其反帝反封的革命斗爭服務的反革命論調。“軟性電影”論中還包括許多其他認識、批評和創作電影的學說和理論,在“軟性電影”論的闡述中,其領軍人物劉吶鷗、黃嘉謨、穆時英、施蟄存等紛紛發表了自己對于電影本體觀念的認識和理解,并與當時“左翼電影”的種種觀點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論辯。如“讓眼睛吃冰激凌,讓心靈坐沙發椅”,“電影的純粹性”以及“美的觀照態度”等一系列創作原則紛紛遭到“左翼電影”反對,劉吶鷗等人更被認定是形式主義的國民黨御用文人。然而,“軟性電影”論并非只是一種政治傾向的表達,今天我們重新站在藝術本質觀的角度來看待“軟性電影”論,會發現其評判和認識電影的某些藝術觀念的確是值得欣賞和借鑒的。盡管站在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軟性電影”論的提出并不那么合時宜,但拋開沉重的政治宣傳枷鎖和意識形態束縛,“軟性電影”論對于電影認識探索的價值是需要被擺正的。特別是其所強調的電影創作中“機械要素”和“運動”理論的重要性,更是對30年代后中國現代主義電影的實踐創作和理論評價有著莫大的影響。
二、“軟性電影”中的“機械要素”討論
對電影“機械要素”的討論是軟性電影認識并闡述電影本質特征的一個重要論點。“軟性電影”論曾在其創作本體觀念中著重強調了“機械要素”這一概念。認為“電影是科學(光化學、工業)和藝術結婚的混血兒。所以它的表現法上根本就有了許多遺傳的機械性。只就這一點它就已經是跨過了從來諸藝術如文學、繪畫、雕刻、音樂、戲劇等領域外了……機械性的描寫法均是電影藝術家手里所享有的特權,也是電影機能之超乎從來諸藝術機能之理由。”[2]當然,通過對“軟性電影”的深入認識,不難發現其理論論述中對電影“機械要素”認識絕不僅僅停留在電影拍攝的外部技術上,這里的“機械要素”還指涉了創作形式上的“機械性”和都市文化心理上的“機械性”兩個方面(后文將對此論點作具體闡述)。而這些表現內容,一方面在技術上依賴于形式上“機械性”的蒙太奇剪輯手法,主張以新鮮的技法表達不一般的現代景象和感覺,利用蒙太奇、剪輯、以及音樂配合等深化影像外部創造的“節奏”。另一方面,“機械性”也依賴于現代都市心理,推崇捕捉都市的新奇感覺,傳達當時的人們對“現代性”的經驗。可以說,電影既構成了他們的現代性體驗,又是他們的學習對象。
(一)“機械要素”的電影形式節奏
以劉吶鷗和穆時英為代表,其論述的“機械要素”的內涵都來自于他們對電影本質特征的認識——認為電影是運動的藝術,是節奏的藝術,是美的藝術。劉吶鷗明確指出:“像建筑最純粹地體現著機械文明的合理主義一般地,最能夠性格地描寫機械文明的社會的環境的,就是電影。”[3]并提到“要緊的并不是速度的獲得,而是因速度的獲得而產生的人們的情感。人們的精神是饑餓、行動、戰栗和沖動的。同樣是旋律,但華爾茲的時代是過時了,熱烈的爵士才是現代人的音樂,因為慣于都市噪音是不需要絕對調和的音響了。勝利是能夠支配空間,尤其是能夠抓住‘時間’所給予的優美的藝術形式這一邊的。電影在許多它克服了的難題之中只因為它的克服了時間,所以‘電影的造型’變代替了一切‘靜的造型’而絕對地支配著。然而所謂‘電影的造型的根本要素是在哪里呢?這無非是那個建設在‘時間’范疇內的它的‘節奏’了。”[4]很顯然,劉吶鷗強調了電影創作的“節奏”——從而突出他的“機械要素”的觀點。
在當代城市電影中,“節奏”的表現顯而易見。蒙太奇的組接在現代都市電影中的作用往往是情緒表現超過了電影敘事。導演將一系列紛繁不連續的都市意象任意拼接,原本零散的鏡頭畫面的組合帶給觀眾豐富的聯想、想象、夢境、隱喻的心理體驗,影像的碎片化帶來的是個人生命體驗的碎片化。可以說,電影與現代都市的文化關系則表現在電影不僅是現代文明發展的產物,更是反映現代文明的一面鏡子——表現著“機械文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本來面貌以及它的性格。根據記載,劉吶鷗不僅創作了電影劇本《永遠的微笑》,他還參與了《大地的女兒》《民族兒女》《密電碼》等故事片的拍攝制作,在報刊上公開發表電影《The lady to Keep You Company》的分鏡頭腳本,該腳本利用大量閃回與特寫的方式,通過反情節的敘事結構打破“影戲觀”的創作傳統,制造了一種含蓄的審美意境與情緒化的影像節奏。劉吶鷗深受蘇聯蒙太奇學派理論與創作的影響,1933年另獨立拍攝了一部致敬蘇聯維爾托夫的實驗性家庭紀錄片《持攝影機的男人》。這部影片采用完全寫實的手法呈現了創作者早年在臺南、廣東、日本東京等多地的家庭場景和旅行場景記錄,劉吶鷗采用快切和二次組接的鏡頭方式呈現了一部“都市交響樂”。影片中有充斥著現代都市文明的意象場面,大量的交通工具,如火車、汽車、輪渡、飛機等呈現著影片的節奏和速度,不同地區的空間場景被鏡頭并置在一起,生活瑣碎被攝影機揉碎了重組,城市與居民的脈搏心跳在旅行的過程中翻涌。劉吶鷗認為,科學技術推動下產生的“機械要素”是電影得以藝術表現的根本手段,通過這種手段所創造的具象化的、運動的時間與空間才是電影的本質。電影活動是用影像來探索一種可以被“看得見的音樂”,他主張用動感的節奏打破單一的戲劇性線性敘事,從而能夠表現一種“機械要素”的節奏要求。
(二)“機械要素”中的都市文化心理
同時,“軟性電影”論的電影觀跟他們的文學觀是一脈相承的,“軟性電影”論中的審美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新感覺派小說所發展起來的,而“機械要素”的都市心理探索也蘊含其中。“新感覺派”作為我國二十世紀第一個被引進的現代小說流派,其創作主張對“軟性電影”產生了的影響,中國的新感覺派小說是在日本新感覺派的引進下步其后塵所發展起來的。“軟性電影”論的領頭人劉吶歐、施蜇存、穆時英等同一時期也以“新感覺派小說”代表作家的身份而存在著。其文學代表作有《謝醫生的瘋癥》、《白金的女體塑像》、《無軌列車》、《夜總會的五個人》、《在巴黎大戲院》等。新感覺派善于將現代化物質文明下人的精神危機和心理病態作為主要描摹對象,將人們的感覺和直覺作為出發點,在具體手法上認為隱喻、暗示比現實重要,直觀性和體驗性比情節重要,利用人的潛意識、無意識來創造一種“新現實”,“新感覺派”小說是我國現代“都市文學”的一次新開拓。
20 世紀30年代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空前激化,在特殊的文化和政治土壤中,半殖民地大都市中的小資產階級成為其主要描摹對象,創作者們欣賞現代派小說中新奇、怪誕以及感官化的表現手法,將以上海為代表的“東方的巴黎”這一都市人群的精神迷離和情感荒蕪作為打破情節性和統一性的核心,把精神分析、潛意識、蒙太奇等各種現代主義電影的創作思路,納入了現實主義的軌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感覺派”小說。這些文學作品所刻畫的意象是極具現代感和都市性的,例如有代表著心靈逃離的“高速列車”、代表著徹底瘋狂的“夜總會”、代表著冰冷且病態的“醫院”,同時也描繪了都市的賽馬場、影院、茶館、高級別墅、海濱浴場等現代感場景,刻畫了具有都市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交際花、公子哥、富家少奶奶、姘頭、資本家、公司職員等多樣化的形象人物,作品以跳脫的節奏,意識流的結構,生動地顯現出資本主義剝削階級糜爛生活的剪影以及現代化進程下都市人群的自我價值懷疑。可以說,“機械”成了“現代化”的另一個代名詞,對于“機械要素”和“城市機械化”的理解遠遠不止表現在現代工業的進步程度上。縱觀當代城市影像電影,“機械文明”執著于展現現代都市節奏和現代都市風光,更深層次上是表現了現代人的都市文化心理。此類影片大多展現了現代文明中的種種問題和困惑,以及創作者對于這些困境的個人思考。例如弗里茲·朗《大都會》、王家衛《重慶森林》和《墮落天使》、張元《北京雜種》、賈樟柯《小武》、貝納爾多·貝托魯奇《巴黎最后的探戈》、安東尼奧尼《紅色沙漠》等。盡管這些電影在內容表達和主題突顯上不盡相同,但由于“機械文明”的籠罩,這些作品都共同反映出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個性的刻板化或者碎片化,人的自我價值和生命自由的追尋在“機械文明”面前顯得異常困難。現代都市人的精神家園顯得越來越遙遠,理性與感性脫節,人與自然脫節。
(三)“機械要素”的娛樂感官體驗
當然,對于“軟性電影”論而言,電影是令人愉悅的商品,其本身就是資本和技術的產物,因此,電影中的“機械要素”在反映浮華都市下的現代性思考的同時,也要做到“給眼睛吃冰淇淋,給心靈坐沙發椅”[5]。一方面是“給眼睛吃冰激凌”的表達。例如,在實際拍攝時,對女演員進行全身拍攝的時候,運用三十度仰角的鏡頭拍攝最為美觀,能夠拍出女演員微顫的長睫毛以及半閉著眼,為她們添上一抹女性的曼妙。在“軟性電影”代表作《化身姑娘》當中可以具體發現,首先其演員從長相到裝扮上都非常講究,人物外貌美麗俊俏,著裝打扮美觀整齊,表演中的語調和語態得體大方。影片題材比較新奇,是一個由男扮女裝而引起錯綜復雜的情感交集故事。在畫面調度上,攝影機的游走和鏡頭場面之間的分切組合總是極其流暢自然,能很好地把握人物或物體在畫面移動過程中的拍攝的位置和角度,從而凸顯出一種無形的動感和節奏。例如女主人公莉英在房間跳舞的場景,鏡頭從主人公興奮的面部表情、肢體動作的凸顯到腳下的舞步移動,以及與姑媽共舞時兩人各自不同的狀態反應都一一作了豐富而詳盡的表達。流暢而富有動感的畫面剪輯配合上主人公歡樂的歌聲舞蹈,的的確確讓觀眾的眼睛吃了一次“冰激凌”。另外,影片在畫面構圖上也非常考究。畫面中站幾個人,分別站在哪里,以及人物間的移動怎樣配合攝影機游走等等都成了導演著重安排的問題對象。當女主人公莉英第一次以男性身份回國被祖父介紹給眾人時,畫面中賓客位置分別被安排成兩條對角線,形成一個三角形構圖。而莉英則不偏不倚正處由兩條對角線交匯的焦點上——畫面上的中心點和視覺上的中心點。可見導演在“視覺表達”上的要求之高。另一方面是“給心靈坐沙發椅”的表達。《化身姑娘》作為“軟性電影”的代表作,的確與當時的現實條件和政治意識要求不太吻合,然而它滿足了觀眾豐富的好奇心理和憧憬心理。女主人公時不時地換裝,異性之間的愛戀,同性之間的忙盲戀以及一系列都市生活百態的現實顯現等現代社會快節奏的“機械要素”都給觀眾以強烈的新鮮之感。劇中人物個人身份的選擇自由、自我價值的選擇自由和愛與被愛的選擇自由都是觀眾所渴望而不可及的,這種近似完全新奇而自由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說是每個人心里的一種愿望嘗試。盡管影片沒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過多的現實問題的凸顯與評判,但它作為一張“沙發椅”,的確是現代社會中人們一種“詩意棲居”的愿望表達——個人意志的自由選擇。
三、當代都市電影中的“機械要素”及其內涵
“軟性電影”中的“機械要素”理論同樣適用于當代都市電影的內涵認知,這讓30年代的“軟性電影”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程度上具備了鮮明的電影現代性特質,且與長期遵循電影的情節性、場面性和教化性的“影戲觀”電影創作與審美傳統產生了巨大差異。現代城市意象的呈現和想象代表著創作者對現代化“機械”程度的認知體會,都市文明和心理則表現在這些意象當中。電影作為一種現代化科技的產物,必然也保持著它自身的機械屬性。導演們往往將自身的都市生命體驗擴散到鏡頭語言的呈現之中,使得電影始終跟蹤、記錄和保存代化城市進程的發展。
都市電影表現著人與生俱來的作為生命自由個體與“機械”集體規范之間的對立矛盾。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速度”和“節奏”成為都市生活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特質,人們對于都市生活速度和節奏的感受來自現代文明的突飛猛進。都市環境在快速變化,拆遷、重組或者改建都給都市意象以極大的想象和創造空間,而與都市文化相匹配的建筑、交通、公共設施等皆被深深打上“機械”的烙印。在當代都市電影的表現中,我們能夠豐富的領略不同時期不同城市的“機械要素”與個體生命自由之間的矛盾。例如陳凱歌的《百花深處》、王家衛的《墮落天使》、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婁燁的《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都市化進程的速度超越了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階段。原本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的相對封閉的經濟結構所造就的農村和鄉鎮空間逐漸走向以工商業為主發展金融房產以及網絡經濟的現代開放都市,而在以幾何形式規劃的城市當中,水泥森林成了人們新的居住環境。寫字樓、車輛、網絡、酒吧等一個個都市符號處處占據著人們的生活空間和感知空間。可以說,“機械”成了“現代化”的另一個代名詞,在都市電影中,我們能看到人們在鋼筋水泥建立的叢林之中尋找自我和情感歸宿是異常艱難的,是充滿挫折的,他們大都迷失在車水馬龍的物質空間難以自拔,快速的節奏讓人們變得麻木或者瘋狂,規律和效率才是衡量都市的標準,對于個體而言,物與心的搖擺無處不在。此外,在機械化的現代進程中,個人的感知經驗和集體記憶也在不斷受到挑戰,因為“現代化”最大的一個特征就是永遠不會拘于現狀,“現代化”里人也在時刻警惕著時代的速度與自我速度之間的和諧性——一旦兩者之間的腳步出現前后錯亂,自我速度沒有及時跟上時代的速度,那么就很容易出現自我的懷疑和精神上的不確定性。美國人本主義城市規劃理論家凱倫·林奇如此描述當代洛杉磯人:“在當地,人們似乎都有一種痛苦或是懷舊的情緒,可能是由于對諸多變化的怨恨,或僅僅是因為他們跟不上變化的節奏,無法重新確定方位”[6]。
在科學技術和機械文明的引領下,全球一體化進程持續深入,而都市的各個部分也完成了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但這種通過科學和機械文明將人的生活空間帶向無限開放的過程,是否真的可以帶來人的選擇的徹底自由?法國著名哲學家亨利·伯格森對現代科學主義的文化思潮進行持反對意見,他宣揚直覺主義,認為唯有直覺才可體驗生命的本質,即真正唯一本體性的存在,他還提出并論證生命的非理性沖動,認為生命不是物質,而是一種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動不息而又不知疲憊的生命沖動。這種沖動變化是在時間上永不間歇地自發地流轉,故稱為“綿延”或“生命之流”。它像一條永流不息的意識長河,所以也稱為“意識流”。在以表現都市空間為創作核心之一的現代主義電影之中,“意識流”化的影像表達是是普遍而準確的,這種根據人的主觀感受切換鏡頭的方式不僅能體現變化的節奏感,更能呈現個體“意志自由”本身。
在對待“意志自由”和“生存自由”這一問題上,荷爾德林和海德格爾等人曾提倡人的“詩意地棲居”,意在表明通過藝術化和詩意化來抵制科學技術所帶來的人的意志選擇權的喪失和精神世界的崩塌。這里“詩意”的內涵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文學層面的“詩”的含義了,更包括了人作為生命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和對于精神自由的追尋。在都市電影當中,都市人群作為都市意象的感知者和體驗者,在現代化文明的進程中扮演中重要角色。他們在都市空間中駐足或流動,身體和意志本身也成為“機械要素”的一種。“面對那些在流動中游離的人群,我們甚至可以根據他們與都市的關系劃分為:陌生者、朝圣者、旅游者、游蕩者、流浪者和比賽者等類型。這些類名對應了他們在都市中的狀態,也提供了他們感知和體驗都市的方式。”[7]但不管以哪種方式存在于都市空間,“機械要素”本身實際上就是個體在尋找“詩意棲居”的全部過程,盡管我們的看到的是影像中的焦慮、恍惚、迷失與祈禱以及種種感知、動情、沖動、行動、回憶、夢想、思考等不確定性,但在不確定性的彼岸,就是都市“機械要素”真正的“詩意的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