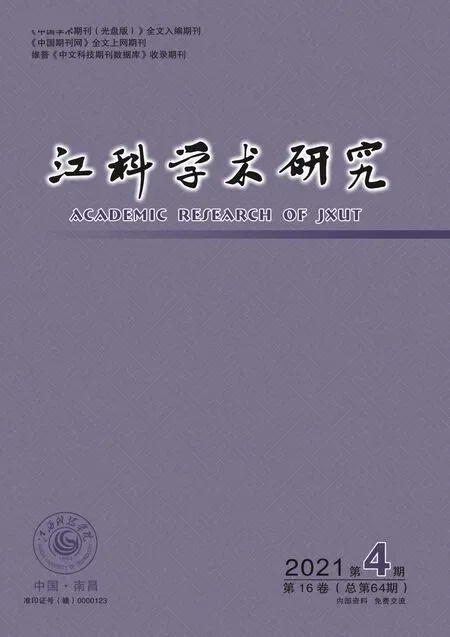歷代詠廬山詩人的山水情懷
龔俊杰
魏晉時期,政治黑暗、社會動蕩,文人為保全性命,紛紛躲入山林,于是廬山便成文人們的“精神家園”。此后,歷代眾多騷人墨客皆曾逗留于此,對廬山山水進行吟詠、考察。詩人在登廬山的山水中,既豐富了體驗提高了審美能力,又使得自身心靈得到了汲養,他們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詠吟自然山水,留下了眾多具有山水情懷的經典作品。
一、寄托理想的山水情懷
廬山自古以“雄、奇、險、秀”而聞名中外,千百年來以其重巒疊嶂,飛瀑流泉,松濤云海,變幻莫測的奇秀之姿,吸引著眾多騷人墨客,孕育了豐富多彩,風格特異的“廬山文化”,成為我國的文化名山。史上無數文人墨客歌詠廬山文學作品為數不菲,尤其是陶淵明、鮑照、謝靈運、蘇軾等詩人把廬山當做寄托理想的一座名山,在此留下了浩如煙海的丹青墨跡和膾炙人口的篇章。
(一)陶淵明歸田躬耕的愛山情懷
在文學史上,陶淵明是以隱逸詩人和田園詩人著稱的。同時也是把廬山自然風光融入田園詩歌創作的第一人,其家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位于廬山西南腳下農村,自然生態良好,從小便有“性本愛丘山”的秉性。他熱愛自然,具有東晉名士那種不慕榮利、閑靜恬適的清高精神。他29歲出任江州祭酒,到42歲便毅然辭去彭澤縣令,面對社會黑暗腐敗,感到不滿和憤慨,卻又無力改變;既不能施展抱負,又不愿同流合污,因此保持自己純潔自然的本性,最后歸隱田園便是他惟一的選擇。總的來說,描寫田園生活,表現隱逸思想,表現跟污濁現實相對立的社會理想,是陶淵明詩歌的主要內容。
最著名的是《歸園田居(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詩作于晉安帝義熙二年丙午(公元406年),即他辭去彭澤縣令歸田居家第二年,詩人時年42 歲。這組詩從總體的思想內容看,可以說是詩人求仕和歸隱的思想矛盾,經過長期的發展,最終以歸隱思想取得全勝的大徹大悟之作。詩寫出了詩人酷愛大自然的真性情,也寫出了他終于發現并無限熱愛的田園生活的真境界。詩中所謂“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所謂“戀舊林”、“思故淵”,都是醒悟之詞,都是要恢復自己的本性——擺脫塵俗,回歸自然。在農村開荒種地,過一種簡樸疏淡的生活,是陶淵明堅持“守拙”的本性,就是要與污濁的社會相對抗,不和它妥協,不和它同流合污。
《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詩中寫其早出晚歸的勞動生活,寫出了勞動的艱辛以及勞動的愉快,他將勞動的生活寫得很美,富有詩意,充滿一種清新之氣。另外,種田自給本身,就表示了反對剝削和唾棄富貴之意。
《飲酒(其九)》:“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這首詩是抒寫懷抱之作,純出于自然,毫無矯飾。從詩的藝術構思來看,全篇設為問答,詩人將日常生活中的瑣碎之事,如開門迎客,對酒談天,都寫入詩中,而且又寫得親切自然,豐腴有味,純樸動人,這也是作品的高妙之處。全篇看似舒緩,卻在表面散漫的行文之中,處處蘊含著不流于世俗的高尚精神。
其他如《飲酒(其五)》、《時運》、《和郭主薄》其一、《移居》其一、《雜詩》、《讀山海經》等,也都是寫田園風光,表現其對田園生活的寧靜閑遠境界和悠然自得心情的。陶淵明喜愛廬山自然風光其實就是他躬耕田園的情懷,他立志躬耕堅守、構建自由的精神家園,保持其純潔而高尚的人格,最后發展升華為“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
(二)鮑照仕途難卜的憂慮情懷
鮑照是南朝初期的杰出詩人,其時臨川王劉義慶任江州刺史時,正是鮑照仕途難遇、心力交碎之際。他曾登臨廬山游覽,親近自然,寫下詩篇《登廬山》:“懸裝亂水區,薄旅次山楹。千巖盛阻積,萬壑勢回縈……”,以此來獲得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解脫。詩中在描繪廬山險峻奇麗、幽邃清冷的景色的同時還采用“移步換景”手法,以其矯健的筆致,直取真境,按照游蹤順序漸次寫來。詩的結尾寫詩人登上廬山故地重游、回歸自然的情趣,抒發了其生性愛好自然,向往廬山山水的情懷。
(三)謝靈運與廬山佛教情懷
謝靈運一生游遍祖國的壯美山川,對佛教有較深的研究,佛學功底甚深。其交游法師,往來頻繁,并利用詩歌作為弘法工具,撰寫了大量佛教題材的詩歌。義熙年間(公元411-412年),謝靈運在廬山東林寺與名僧法師慧遠“及一相見便肅然心服”(《高僧傳》),建立了真誠的友誼并在廬山筑有精舍。元嘉八年(公元431年)謝靈運赴臨川途中,登上廬山最高峰漢陽峰寫下其《登廬山絕頂望諸嶠》一詩:“山行非有期,彌遠不能輟。……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詩人登上廬山漢陽峰山頂,俯瞰山景、極目遠眺時的抒懷寫意的情緒。喜好游山玩水的謝靈運,登臨廬山“絕境”,實現了平日里的愿景,眺望山野:只見“積峽忽復啟”、“巒垅有合沓”,大有杜甫登泰山“一覽眾山小”之氣慨,這壯闊瑰麗的自然景色自然讓詩人感到興奮。而此時謝靈運的詩歌早已擺脫了魏晉玄言詩束縛,已具備山水詩的韻味,堪稱廬山山水詩中的上乘之作。
(四)蘇軾借景說理的廬山情懷
蘇軾一生坎坷,因作詩“謫訕朝廷”等“罪名”屢遭貶放。他被貶赴汝洲任“團練”途中登廬山西林寺,當時他望著眼前山清水秀的景色,想到了朝堂上的是是非非,于是蘇軾有感而發,在西林寺的墻壁上寫下《題西林壁》。
這是一首詩中有畫的寫景詩,也是一首哲理詩,哲理蘊含在對廬山景色的描繪之中。詩中贊美廬山美麗景色,在歷史上被稱為是不同以往的以言理為特點的詩作,因為蘇軾在前兩句主要描寫的是廬山的雄偉景色,而后兩句也是通過景色來表現哲理。他從廬山的正面、側面、遠處、近處來看廬山的跌宕起伏,而后他發現從不同角度看廬山,都能看到廬山不同的模樣。因此,他在最后兩句表達了要想真正認清事物的本質,就應該摒棄主觀與成見的想法,由此看出蘇軾的思想是比較超前的。因此,蘇軾筆下的廬山好比是撲朔迷離的政局,新舊兩黨立場不同,結論也不同。事實上,人們都置身局中,置身歷史長河中,都不免陷入當局者迷的困境,應該更客觀地思考問題,得出恰當結論。蘇軾這種以“言志、言情、言理”為特色的詩風可謂是另辟蹊徑,就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語淺意深,因物寓理,寄至味于淡泊。
二、抒發壯志的山水情懷
自然山水是古典詩歌意象的重要來源,而廬山作為一座最早的審美對象的江南名山,其山水文化結合得最為默契。廬山獨特的自然山水以及人文物使眾多詩人在此抒寫性情、傾吐苦悶。其中,慧遠、白居易、孟浩然、李白等人通過其詩作,來表現其與污濁現實社會相抗爭,可謂壯志凌云、豪情萬丈。
(一)慧遠隱遁息心的佛理禪機情懷
據記載東漢僧人慧遠,是最早歌詠廬山水的隱逸詩人,其具有代表意義的廬山詩兩篇:其一《游廬山》:“崇巖吐清氣,幽岫棲神跡……”。詩開篇寫廬山“奇峰突起、山嵐云蒸、恍若仙境”的自然風光,結尾通過寫景述懷,借機隱逸淡玄。作者通過身游“仙境”——歌詠廬山風光本身的意趣,同時還抒發其中領悟到的玄理妙道,宣揚佛家頓悟、超脫的思想境界。
其二《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忽聞石門游,奇唱發幽情。褰裳思云駕,望崖想曾城……。”此詩寫其身游匡廬仙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弘揚佛法大道的哲學玄思,抒發從中感悟到的玄理妙道。
(二)白居易皈依自然的情懷
大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夏,白居易被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其內心十分苦悶,便把失落的情懷寄托于江州附近的奇山秀水之中,并在廬山香爐峰和遺愛寺之間的一處風景清幽的地方修筑草堂,翌年三月草堂落成。四月,白居易與朋友二十二人齋具,寫下詩文《草堂記》:“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詩文說明了建草堂的經過及其周圍幽美的環境,抒發了自己寄情山水的向往。文中描繪景物細致入微,感情抒發自然質樸,寫作手法變幻多姿和語言平實親切是此文的一大特色。
詩人采用了自問自答的方式闡釋草堂環境甲廬山的原因,作者用細膩的筆觸從各個方面描繪出一種幽深寧靜而又充滿生機活力的景致。山竹野卉,古松老杉。蘿蔦葉蔓,白石垤塊,飛泉瀑布乃至白蓮白魚,盡收筆端,而四時之變化,晨昏之奇觀也如在眼前。眼前有美景,耳邊有泉聲,鼻端有茶香,使人身心俱快。詩中作者采用比喻手法,寫古松老杉修柯低枝的形態“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寫瀑布黃昏時其色如練,夜深時其聲如環佩琴筑之音。寫以剖竹引來的泉水由屋檐滴下,“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都極為貼切地寫出了事物的特色。經過這種細致動人的渲染,作者的“外適內和,體寧心恬”也就是極為自然的了,而由此引發出的對于山水的熱愛留戀之情也就顯得真實可信了。
(三)孟浩然仰慕廬山情懷
唐朝開元二十一年(733)五月間,漫游吳越的孟浩然,自越州返襄陽,途經潯陽(今江西九江),傍晚時分船泊江邊眺望匡廬時,發思古之幽情而作《晚泊潯陽望香爐峰》五言律詩。
此詩上半首敘事,略微見景,稍帶述情,落筆空靈。以欲揚先抑的手法寫得見廬山時的欣喜。吳越漫游,沿江而返,揚帆何止千里。一路之上,固不乏名山勝水,但都沒有引起詩人的興趣,只是到了潯陽城下,泊船江岸,看見挺拔秀麗的廬山時,才使詩人精神為之一爽,發出得遇名山的贊嘆。“始見香爐峰”一個“始”字,道出詩人掩飾不住的喜悅。下半首以情帶景,該描繪廬山秀麗的景色,香爐峰煙霧繚繞的神奇,飛流而下的廬山瀑布,似乎都不曾引起詩人的注意,因為天色已晚。香爐峰只能看出一個模糊的輪廓?廬山瀑布的白練已為夜色掩沒?還是因為詩人之意別有所屬?恐怕是后者。孟浩然由香爐峰聯想到的,是東晉名僧慧遠,以空靈之筆來寫內在的情感。全詩簡淡自然、空靈無跡,頗有隨筆的味道,而在隨意揮寫間,不但勾畫了江山風景,而且抒發了傾慕高僧慧遠、向往隱居勝地的隱逸情懷。
孟浩然另有一首《彭蠡湖中望廬山》,大概是作于他將漫游吳越之時,同樣也是夜泊眺望,卻細寫了廬山景致:“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默疏凝黛色。崢嶸當曙空。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在詩的后半部分,則表達了自己對隱逸生活的向往:“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將半,星霜歲欲窮。寄言巖棲者,畢趣當來同。”孟浩然此番出游,仍懷有仕進之意,故歸隱乃是將來之事。而待到漫游歸來,心境已然變化,再見廬山,感受倍覺親切,同時也多了幾許悵惘,所以發言吐詞,便與上一首不類。這兩首望廬山詩合看,更能了解孟浩然的性格心境,也更能看出它們各自的特點。
(四)李白求仙問道的拜山情懷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曾五次登臨廬山:開元十三年(725)“仗劍去國,辭親遠游”時上廬山,作《望廬山瀑布》二首并曾有終老此山之意,體現了很強烈的“求仙訪道的廬山情懷”;天寶九載(750),李白被賜金還山、仕途無望之時上廬山,作《廬山東林寺夜懷》、《別東林寺僧》等詩表露心跡、得山水之樂養清靜之心;至德元年(756)安史之亂時李白南下避亂隱居廬山五老峰下,作《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上元元年(760)秋,李白流放夜郎、遇赦東歸后回到廬山作《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抒發高蹈出世之情。
廬山因山色秀美、環境清幽,所處交通靠近政治中心,成為李白待時而動、東山再起的政治根據地,更是李白在仕途遭挫、身心疲憊時,安放靈魂的庇護所和慰藉受傷心靈的療養地。其所吟詠的廬山詩,富有多重深沉的思想意蘊和情感寄托,散發出高妙傳神的藝術魅力,為其求仙訪道產生了拜山情懷。
三、結論
總之,廬山是一座“蒼潤高逸,秀出東南”的千古文化名山。在歷代詩人登臨廬山的過程中,他們有的是官運亨通時登高詠懷,感恩謝德;有的是仕途遭貶隱居待命,慰藉心靈;有的是政治遇險遁跡塵世,棲息山中;有的是信奉佛道深居寺觀,修仙慕道;有的是憤世嫉俗義憤填膺,心事浩茫……。詩人們一方面對廬山自然山水進行濃墨重彩、抒情寫意,另一方面也是文人們抒發內心情歌的樂歌。通過他們,不僅我們欣賞到了廬山的“真面目”,而且使我們洞察到了他們的與廬山山水的物我兩忘情結,使廬山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