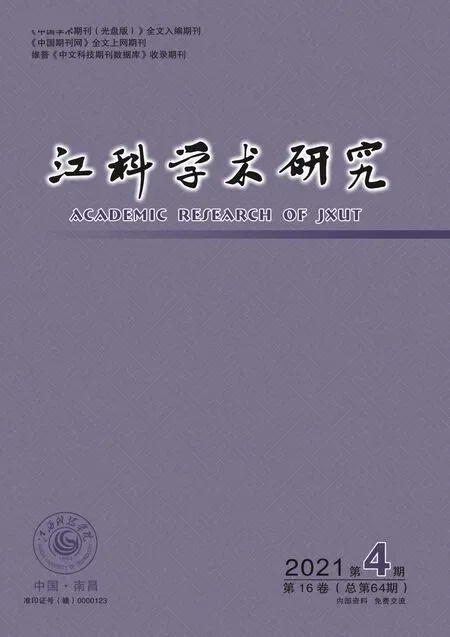安徽花鼓燈“馮派”的特征與藝術價值
高遠志
曾身處消失邊緣的安徽花鼓燈在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入選的41 項民間舞蹈中脫穎而出,成為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民間舞。這離不開著名花鼓燈老藝人、安徽花鼓燈“馮派”奠基人——馮國佩先生的巨大貢獻:20世紀60年代初期,馮國佩苦心鉆研,和其他老藝人們一起編創了第一部以花鼓燈為主的大型花鼓燈歌舞劇《摸花轎》,并且融合了歌、舞、劇的表演,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巨大反響。其代表性的動作“鳳凰三點頭”猶如鳥細語枝頭,“風擺柳”仿佛春風楊柳般得意。“馮派”花鼓燈是老先生用數十載光陰鉆研花鼓燈所得經驗用心澆灌所創,而現今深入了解“馮派”安徽花鼓燈的人卻屈指可數,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花鼓燈瀕臨絕境,但其所承載的藝術價值卻不容小覷,它是中華民族藝術的瑰寶。
一、安徽花鼓燈“馮派”溯源
(一)安徽花鼓燈的起源
“安徽花鼓燈”盛行于我國淮河以北地區,它是典型的漢族民族民間舞,以歌、舞形式的相結合來表達情緒的一種自娛手段,流行在當時淮北農村一帶。對于安徽花鼓燈的發源眾說紛紜,甚至還有一些遠古時期的傳說,比如“禹王傳說”(山民祝賀大禹治水成功)、“驚蛟傳說”(人們玩燈驅趕蛟神)、“唐母之說”(唐王為母祈福)等,從這些說法我們可以看出安徽花鼓燈的起源傳說很多,都有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歷史背景。由此可見,安徽花鼓燈具有復雜性,但是通過對關于安徽花鼓燈傳說的描述分析,不難發現其相似性,例如:“唐母之說”中唐王為了母親身體痊愈,聽信民間說法,與眾人玩鬧花燈后,唐母果然痊愈,花鼓燈也因此開始呈現表演;“禹王傳說”中因大禹治水成功,山民前來道賀,并建“禹王廟”和玩燈對其慶賀。通過分析對比可以得出結論,安徽花鼓燈的起源具有復雜性,但它的表達目的性又相類似,主要表現在:為了表達喜悅之情;都有祈福和祝愿的深刻意義;它是廣場藝術,不局限于只是舞臺化的演出,具有自發性;它是隨性創造、隨意發揮的,表演性不多,反而自娛性的藝術形式更大。而安徽花鼓燈的流派也是如此,流派紛呈但其內涵意義都是一樣的。
(二)安徽花鼓燈“馮派”的形成之因
就安徽花鼓燈“馮派”的起源來說,其家族性傳承花鼓燈的方面、所處的地域影響力、“馮派”獨有的特性和當時的競爭環境下時將其形成的主要影響。安徽蚌埠有一個馮嘴子村,開創者馮國佩家族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那里,在當時,花鼓燈盛行,他的家族也就是馮氏家族大部分都是玩花鼓燈的高手,玩燈的影響力從蚌埠地區一直到淮河以北地區,因此馮氏家族對“馮派”花鼓燈具有深切的影響力,這才促使馮國佩本人擁有扎實的花鼓燈功底。馮國佩在當時被譽為花鼓燈界中的泰斗,從少年時期學藝花鼓燈并以之謀生,再到改革開放,花鼓燈的興起和盛行,馮國佩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花鼓燈的幾度滅絕再到重新崛起,他的經歷大起大落,其個人的人生經歷也被融入進了“馮派”的肢體表達中,他的經歷和他曼妙的舞姿一樣高潮迭起,真是因為馮國佩不斷的取其精華,不斷繼承創新,最終形成了特有的“馮派”藝術。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馮國佩之所以能成就“馮派”花鼓燈舞蹈藝術,與當時的時代影響、還有一代傳一代的承襲方式、特有的表現形式和流派的角逐密不可分。同時,這些因素也都形成了“馮派”的肢體特色,動作的靈活度、流暢度刻畫了一個又一個的“蘭花”形象。無論是嬌羞溫婉還是含情脈脈,甚至俏皮嫵媚,塑造的每一個“蘭花”都區別與之前傳統的“蘭花”,有恬靜時的害羞、溫柔中的質樸、秀麗中的活潑,甚至還有細膩的嫵媚,所刻畫的人物,既與安徽懷遠地區花鼓燈的端莊典雅不同,又與安徽鳳臺地區的詼諧幽默大不一樣。馮國佩用真摯的情感和熱情,所表現的“蘭花”時而奔放、時而溫婉、時而嫵媚、時而豪邁,形成了以“腳下溜,韻律強,身姿美,情感真,神態媚”為核心的馮派藝術特征流傳至今。
二、安徽花鼓燈“馮派”藝術特征
(一)建國前階段
馮國佩對花鼓燈舞蹈發展的藝術貢獻不容忽視,在不斷變更的現實時代背景之下,他讓“馮派”花鼓燈在不斷變更的現實背景之下依舊居于安徽民間舞蹈前列,這使他在眾多學習花鼓燈的演員中脫穎而出。
上世紀四十年代,由于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一直是男演員飾演花鼓燈中的“蘭花”,但這通常需要克服男女在骨骼等先天方面的困難,例如,為了模仿出舊時代的小腳女人的“三寸金蓮”的走路姿態,男演員在表演時,都需要穿著“襯子”來跳舞、玩燈。這也是封建思想以“三寸金蓮”為美在舞蹈藝術中的體現。因為演員的雙腳需要踩住“襯子”,所以小腿必然會緊收,膝蓋呈自然彎曲狀,但在走步伐時,腳下需要很快的小碎步,微微透著一種“溜勁”;而在“蘭花”走短距離的前進步或急促的跑跳步時,雙腳和雙膝都會存著一股勁兒來保持平衡,這就是花鼓燈舞蹈獨特的特征——“梗勁”。花鼓燈專家高倩用四句話形容了花鼓燈舞蹈的精髓之處“重心靠右后,走路腰晃扭。腳下梗住勁,傳神靠眼瞅。”
(二)建國后階段
從新中國的成立,馮國佩的思想、審美都受到很大沖擊,隨之對于安徽花鼓燈的觀念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建國前,由于馮國佩一直都在仿效舊社會的小女子,所以表現出的“蘭花”大多都是嬌柔忸怩的動作姿態。但在建國后,新事物的出現和舊事物的變化,沖破了一成不變的觀念,在時代更替的發展下,馮國佩的審美也隨之改變,他不想花鼓燈做為舊社會的產物繼續走下去,不愿再塑造單一的傳統舊社會女子那不自由、委曲求全的情感表達,他更不愿再繼續持著“邁小步”的舞蹈姿態來迎接嶄新的社會,他決定跟隨社會意識形態將“馮派”花鼓燈改良融合。首先在肢體特點的造型上變得昂首挺胸,其次是動作幅度有所加大,動作風格變得瀟灑矯健,例如“馮派”動作中的“拐彎”,速度和技巧性較之以前都有明顯加快。相應的,男演員登臺演出時所必須要穿的“襯子”被拿掉了,并且花鼓燈出現了新一代的女演員。這樣的大膽創新也給“馮派”花鼓燈有了巨大的變化,演員腳下更溜了,穩定性更強,腳下沒有了“襯子”的束縛,所需要表現的韻律感更能展現。馮國佩還大膽的吸取了西方芭蕾舞的基本挺拔的姿態,把芭蕾舞挺拔向上的氣息和他特有的花鼓燈結合,這個變化讓演員在花鼓燈中的腳下步伐能夠柔韌有余的更加“溜”。建國后的“馮派”花鼓燈煥然一新,舊社會的害羞表演幾乎已經看不見了,而大方瀟灑、潑辣嫵媚的新時代女性形象正一點一點深入人心。
(三)風格成熟與定型階段
前文已經提到,馮國佩在建國后的特點有了質的變化:矯健、瀟灑、大方的風格特征。但從對流派的比較和馮國佩本人的舞蹈肢體分析中看出,“馮派”花鼓燈的藝術風格和自身條件有很大關系,首先是馮國佩本人身材嬌小,所以在反串時,不用考慮體態問題;其次,經研究證實馮國佩自身的腳較小且富有靈活性,很自然的形成了“溜得快”這一特點。
從“馮派”花鼓燈的一些典型組合中可以看出,其舞蹈姿態和舞蹈動作張弛有度,而其表現形式也相當精彩,活潑又不缺嫵媚,優雅又不失瀟灑。例如“馮派”花鼓燈中的經典動作之一---“單拐彎”,在開始和結束都加了歡快的小跳躍,情感表達和空間運用都相當豐富,甚至出現三度空間的跳躍,這些技巧性動作可以看出馮國佩扎實的花鼓燈技藝,也能夠看出其舞蹈特點“動靜結合剎得住,收放自如節奏強。”
綜上所述,能夠看出馮國佩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后,對于“馮派”花鼓燈的重大改革和其貢獻,無論從思想文化上、表演情感上,還是從動作語匯中、角色刻畫里,都有較大的變化,安徽花鼓燈“馮派”的藝術表現風格也日漸成熟。
三、安徽花鼓燈“馮派”發展道路與藝術價值
(一)安徽花鼓燈的傳承方式
舞蹈作為表達人類情感的空間藝術,它不像文學、繪畫、書法可以保存如此之久,舞蹈在過去的傳承大部分都只是靠言傳身教。就如古時候的安徽花鼓燈并沒有系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過去安徽花鼓燈有3 種傳承方式:其一,.表演中教學(即在表演過程中和觀眾互動的方式來教學,耳濡目染后,新一批的年輕演員會有所收獲,這種傳承方式舞蹈規范性要求較低,但大眾娛樂性強,傳播范圍廣,不受性別和年齡的約束。);其二,師徒傳授(在過去的傳承中,除了世代相傳,師徒選擇是自由開放的,各類流派和不同的花鼓燈班子都相對固定。);其三,薪火相傳(家族性質的傳承,以親代關系為主。)由于時代的變遷,安徽花鼓燈的承襲方式也同樣在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改變,從舊社會的家族血緣關系的傳承,到現如今,不論上門拜訪求學花鼓燈的人是外姓還是外村,老藝人們都會親自教學。
(二)安徽花鼓燈“馮派”的發展道路
安徽花鼓燈已逐步走進各大專業類院校的課程中。以北京舞蹈學院為首,以“馮派”為主的安徽花鼓燈引進大學課堂。上世紀五十年代,著名花鼓燈民間老藝人馮國佩前后受北京舞蹈學院、中央戲劇學院等高校的邀請,親自示范花鼓燈的教學,這是安徽花鼓燈走進專業院校的開端。在這次北京之行之后,北京舞蹈學院會委派教授專程來到安徽,向老藝術家馮國佩學習安徽花鼓燈民間舞蹈,回學校之后又將自己得所見所聞教授給學生,就這樣一步一步探索出了一套比較完善的花鼓燈教學體系。中專舞蹈專業生在第四、五學期開設花鼓燈民間舞蹈課程,本科舞蹈專業教學開設在第二年開始授課,課時均為一學期。與此對應,還編撰了很多針對花鼓燈的教學材料,創編了花鼓燈元素教學法等眾多書面教本。“馮派”花鼓燈漸漸成為各大專業類院系的高年級必修課程。
“馮派”花鼓燈逐步發展,從走進各大專業院校后,漸漸有了花鼓燈的專業團體,最典型的花鼓燈專業團體非“安徽花鼓燈歌舞劇院”莫屬,它的前身是蚌埠市歌舞團,是馮國佩的家鄉。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馮國佩先生就開始在蚌埠市歌舞團擔任副團長并創作出了大型花鼓燈歌舞劇《玩燈人的婚禮》。他在歌舞團里主要工作就是傳授花鼓燈技藝給歌舞團的演員們,跟著馮國佩學習的有十幾人,在其中,演員婁樓作為“馮派”花鼓燈舞蹈的中流砥柱,多次在全國各項舞蹈大賽中,獲得作品和編導的大獎。
(三)安徽花鼓燈“馮派”的藝術價值
花鼓燈專家謝克林在《從花鼓燈的保護,探討非物質遺產保護機制體系的構建》一文中說:“花鼓燈的舞蹈和音樂語匯,靠文字、錄像、圖像是不能完全保存下來的,必須靠老藝人的口傳身授才能完成,而建立活體傳承機制對于保護像花鼓燈這樣的具有民族標志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安徽花鼓燈是中國民族民間舞中首批由民間家族式的言傳身教的方式來進行傳承,一步一步走入了各大藝術類高等院校的民間舞課堂,馮國佩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研究創新,“馮派”成為花鼓燈舞蹈藝術中最出色的流派之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外開放的中國在北京召開了亞洲舞蹈研討會,作為安徽花鼓燈藝術家和“馮派”創始人的馮國佩在吳曉邦的大力推薦下進行現場表演,也是僅有的一個在會上進行演出的民間舞蹈人。在此次表演結束后,世界舞蹈理事會主席蓬特黑格做出了極高的評價“花鼓燈不僅是中國藝術,而且屬于世界。”
中國在建國前、建國后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再此期間,花鼓燈也經歷了巨大浪潮,它的恢復期、發展期都受到強烈的文化沖擊。在花鼓燈藝術的研究和收集花鼓燈圖文以及視頻的資料整理中可以得出結論,在現如今,花鼓燈的恢復到達頂峰。遺憾的是花鼓燈藝術家馮國佩在2012年離世,但花鼓燈藝術還要繼續向前。經典是經得起時間的反復推敲的,安徽花鼓燈“馮派”的經典是可以經受時間的檢驗的,其藝術價值更值得去保護傳承。
四、結語
安徽花鼓燈作為極具中國藝術特色的漢族民間舞蹈,其發展與馮國佩先生的執著與赤誠息息相關,“馮派”正是在經歷了特殊的歷史時期才獨樹一幟,對花鼓燈的考察和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動作特點、劇目情緒等這樣的表面分析,對于發展和傳承也不能只淺談表面,其存在的藝術價值、蘊含的文化內涵得現代舞蹈工作者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