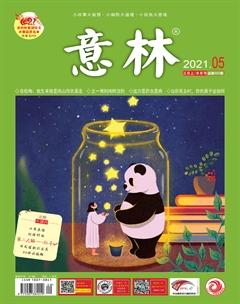種下兩百萬棵樹的女人
沈軼倫
01
因為采訪,我已經認識“大地媽媽”易解放快十年了。我知道她為什么一直堅持種樹。我記得不久前在她的工作室里,她坐在我面前的樣子,一臉憔悴。她眼睛里都是血絲,六十歲開外的人,熬了幾夜沒睡。一切只有她和丈夫兩個人在做主力。12年,這對上海老夫妻在內蒙古沙漠種下了200萬棵樹。
如果說某種因果,那科爾沁和阿拉善沙漠里的那片綠蔭的因,就是這對夫婦失去的兒子。
02
易解放的獨子在2000年去世。
當時,是這一家三口東渡日本的第七年。易解放在日本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丈夫楊安泰開了一家私人中醫診所。唯一的兒子楊睿哲在中央大學商學部讀書。像往常一樣,一日晚餐后,旅日的一家人圍在電視機前收看中國的新聞。那天正在報道中國北方的沙塵暴:遮天蔽日的沙塵里,行人們捂住口鼻在沙塵暴中摸索前行,汽車在白天甚至都要開著車燈。22歲的楊睿哲看著電視不禁對母親說:“我大學畢業后要回中國為沙漠種樹。”睿哲接著說:“要搞就搞大的,種它一片森林。”易解放隨口說:“啊喲,那哪里來的錢呢?”兒子不響。
兩周后的5月22日,易解放像往常一樣去公司上班。可剛到公司半小時,就接到兒子學校打來的一個電話:睿哲在上學途中出了車禍。等到夫妻倆趕到醫院,兒子已經永遠地停止了心跳。
整整兩年的日子里,易解放和丈夫都在保留了兒子衣服的房間里,一遍遍聽留有兒子聲音的磁帶。一個聲音忽然在易解放的腦海里清晰,那是兒子生前這段關于沙漠種樹的對話。終日以淚洗面的她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標。她真的回到中國,又去了內蒙古。
她在日本成立了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NPO)“綠色生命”組織,第一筆去中國種樹的啟動金,就是兒子去世后的生命保險金。在遠離熟悉的都市生活的內蒙古通遼市庫倫旗沙漠里,她牽頭成立的“綠色生命”組織與當地政府簽訂了協議,并種下了第一批樹。
在沙漠里種下第一批萬棵楊樹后,易解放執意在附近住下,同當地村民一道守護樹苗。有時夜半風起,猛然驚醒的她會赤腳奔向林地,在一棵棵樹苗前奔跑停頓,看看樹苗有沒有被吹倒……小樹苗栽下的第三天,一年無雨的庫倫旗終于下了一場透雨,村民們拍手稱奇,笑稱易解放是“雨女”。在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訪時,她和我說,是楊樹唉,小楊,就是兒子的名字,不是嗎?

如此,一年數次,她往返于日本、上海和內蒙古,呼吁捐款募集資金,帶領志愿者去實地勘察種植,傳遞環保防沙知識,事事親力親為,漸漸從50歲出頭,一路也就過了耳順之年。
03
后來關于易解放的報道漸漸多起來了。時不時,就能在媒體上看見她的臉。
她立誓要用10年時間在內蒙古通遼市庫倫旗科爾沁沙漠種植110萬棵樹。11年過去,宏愿已經完成了,可她又在內蒙古多倫縣啟動了種植1萬畝樟子松防沙林工程,繼而又開始在內蒙古西部磴口縣的烏蘭布和沙漠種植梭梭林2000畝。
她說她已經停不下來,這次已經不再僅僅是為了兒子的心愿,而是她自己的心愿。“如果你看過那里的生態環境,如果你看過那里的孩子……”
“你停不下來的。”她說。
隨著廣而告之,每年總有百人和她同去內蒙古。她記每一筆捐款,做賬管理,聯系每一個有意參與的志愿者,安排前往內蒙古的時間、路線和住宿。哪怕只捐一棵樹,她和丈夫也要回信感謝再三。就連出門坐出租車,她也會趁機對司機宣傳和募捐一次。
2010年,易解放腹痛難忍,在志愿者的再三催促下,她才去醫院體檢,結果發現腸子里有癌細胞。但手術后第8天她就下床工作。2012年,傷口又痛了起來,回滬后發現已經腸粘連,急需再次手術。去年,她又一次躺在手術臺上,但剛剛出院,她又出現在了去內蒙古的路上。
“我得到很多幫助,但并沒有后繼有人。誰能代替我呢?有時一些商會也請我去演講,或者請我參加活動,我也要給面子的對不對?我不去,就少一筆捐款不是?”她說,笑笑,兩頰都是細紋。
04
總還是有人會尋到易解放,要她一遍一遍講她種樹的初衷。如《祝福》里的人那樣,特意尋了祥林嫂去那樣,叫她重復喪子的故事。但易解放不惱,有人拿這些做文章或者煽情的切入點,也無所謂。她說她已經不再是為了自己。甚至房價這么高漲的年月里,她賣了在上海的一套房,繼續貼補種樹的事業。
十年,我見證她慢慢變老。也一遍一遍看著她在各類訪談節目里打起精神,說她的故事。我一直記得這個場景——2007年3月,在上海展覽中心東二館的二樓窗畔,窗外的春光。
這一天,是我第一次遇見易解放,當時58歲的她,第一次和我說到兒子的死。那天東二館樓下,有棵三米多高的海棠正值花期。風一搖,粉色的花瓣,就像雨一樣宛轉飄落,有幾瓣,隨風旋至二樓的窗。易解放看到了,就停止了說話。她的聲音里已經沒有哽咽了,語調是平靜的,但有那么一會兒,我覺得采訪本身是一件殘忍的事情。我們倆靜靜坐在那里,一起看這棵樹。飛上來的花瓣柔軟地落在窗邊,如有靈魂一般。
當她把頭回轉過來時,沒有再說自己的事,而是問我:“你幾歲了?”我說了年紀。她聽了,若有所思地點點頭,伸出手想要比畫一下,仿佛前面就有一個孩子似的,她說:“若是我兒子活著,就比你大一點兒。”我心里一動。這比后來她告訴我如何賣房種樹、如何沙漠行走、如何夜里求雨更叫人心里酸澀。
對于母親來說,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只有兩類,比我家孩子大的和比我家孩子小的。她說她把兒子的墓帶回上海了,每周都要去,貼著墓碑說話。
總有一天,一切會歸于平靜。沒有話筒、燈光,沒有鏡頭和講臺,也沒有募捐和志愿者。但等到這普通的一家三口都不再存在于這個世界上時,沙漠里的那些枝葉畢竟還在,在遠離都市喧囂的地方,婆娑聲聲,繼續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