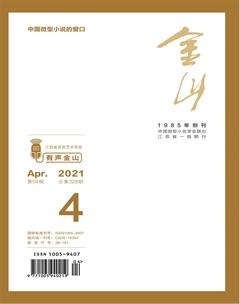羞于啟齒的期刊印數
編者按:
相裕亭先生的這篇《羞于啟齒的期刊印數》,短短九個字,我感覺他是在描繪現今主編們的顏面尷尬與無奈。而徐習軍教授則站在時代的角度給我們又上了一課。余清平先生撰文指出,紙媒優(yōu)勝劣汰,這是自然現象,不必驚慌失措!
下期話題:名家“模仿”,要將微型小說帶往何處去?
期刊印數下滑是出版業(yè)業(yè)態(tài)轉型的表征
——相裕亭的“羞于啟齒”從何談起?
關于“期刊印數”,這本來是出版業(yè)界經常涉及的話題,在作者和讀者之間來探討這個話題基本沒有意義,然裕亭兄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在《金山》刊發(fā)了《羞于啟齒的期刊印數》,其中還不忘記對我以及我所主編的期刊“羞辱”(也許沒有“羞辱”之意,只是“撩騷”)一番,對裕亭這個兄弟我一向偏愛,無論是爬我頭上撓癢還是往我臉上吐口水,我依然愛他!讀了《羞于啟齒的期刊印數》,我在“哈哈”的同時想起網上常說的“貧窮限制了你的想象”,這里我只能說裕亭對于出版時代性的“不知”(我愛護兄弟沒有用“無知”)而從表面現象說了一些“盲人摸象”般的幾近外行的話語。按照《金山》嚴總的“挑唆”及“相峙南徐”欄目的規(guī)則,我在這里需要“懟”一下裕亭,也算是給裕亭普及一下常識。
說到一些期刊,其印數下滑嚴重甚至辦不下去而停刊,這是街頭大媽都知道的事情,根本無需作家們在這里饒舌,然“期刊印數”下滑所反映出來的“出版業(yè)態(tài)轉型”才是業(yè)界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根本不是裕亭說的“羞于啟齒”。“羞于啟齒”出自司馬光《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感到羞恥無法言說。“期刊印數”下滑是出版人自己做錯了什么嗎?出版人應該“羞恥”嗎?顯然不是的,恰恰是“時代發(fā)展”使然,作為出版人根本不必也不會感到“羞于啟齒”,出版人都不會覺得“羞于啟齒”,你裕亭“著什么急”啊?事實上出版界在“出版業(yè)態(tài)轉型”中積極探索出版和傳播的新途徑,推動著時代出版。
“期刊印數”標志著什么?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發(fā)行量大小,決定著期刊的市場效益;二是決定著期刊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這才是期刊出版的本質。從這兩個方面來和裕亭說說。因為裕亭所目見的只限于發(fā)行量,所以就先從市場角度來看,期刊“市場”的時代變化。
20世紀90年代,數字技術的發(fā)展和應用使得傳播領域逐漸數字化,本世紀初就有人預言“紙媒正快速退出舞臺”“數字出版和消費很快就會普及開來,出版業(yè)很快就會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預言”只對了后半部分,數字出版和消費確實快速普及開來了,然“紙媒”并沒有消亡(只是少數的被淘汰或主動停刊轉型),我認為至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也不會消亡。近10年恰是數字出版快速發(fā)展的10年,然而紙質出版依然如火如荼。為了避免列舉某某期刊引起不必要的不快,我借圖書出版的數據來說明時代出版的轉型發(fā)展。2017—2019三年圖書市場發(fā)行收入連續(xù)三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分別是803億、894億、1023億人民幣。市場對紙質傳播保持兩位數增長,裕亭看不到,只盯著某某雜志從68萬發(fā)行量下滑到了幾萬份,看不到數字出版和傳播的快速發(fā)展也不要緊,難道裕亭沒有看到另一個現象——你說的就連《連云港文學》都有12萬發(fā)行量的時候,那時全國有多少刊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不足2000份刊物,到了2008年全國共出版期刊9549種,平均期印數16767萬冊(出版署統(tǒng)計數據),如今正式期刊加上各地區(qū)、各機關、各機構辦的內刊,早已有數萬種,使得期刊種數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翻了數十倍,報紙則成百倍地增長,如果不論數字出版的影響,僅僅就“印數”說事,就用小學生的思維,面對紙刊種類“數十倍地增長”,單份期刊印數也應該“數十倍地下滑”啊,按正常的行業(yè)淘汰機理,報紙期刊“紛紛停刊”也屬于正常的,裕亭你說這有什么“羞于啟齒”的?
再說另一個問題,“期刊印數”與影響力,按照裕亭的思維,期刊發(fā)行量(印數)大,讀者一定就多,所刊發(fā)文章影響就大!這已經out了。以我自己而言,我發(fā)在甘肅省社科院一個核心期刊(這是千份級印數的純學術期刊)上的一篇“太專業(yè)”“很小眾”的論文,360、百度文庫以及中國知網等網絡顯示閱讀量過萬,還有大量的下載記錄,全國從事這個專業(yè)的學者加上研究生也不會過萬人,說明有的讀者不止讀了一遍,這是刊物借助網絡傳播實現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與“期刊印數”沒有關系。不拿別人的刊物說事,僅僅就裕亭“撩騷”的我們刊物來說,印數之少我們從沒有感到“羞于啟齒”,我們在目錄數據項和封底上清楚地印著1100份,裕亭看到印刷廠那個“鴨舌帽”工人送上樓到我辦公室的僅僅是200份,其余直接送學校郵局“照單發(fā)行”了。然而就這1100份我還嫌印刷多了,我們根本不指望傳統(tǒng)發(fā)行,只保證從國家圖書館到各省區(qū)市和重點高校圖書館館藏及有關學報編輯部交流就可以了,發(fā)行的影響力在于“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等數十家簽約的網絡(網絡發(fā)行收入也是和我們分成的),很多時候我們在紙刊未出版的時候就已經在網上優(yōu)先出版了,就不指望“買刊物”的印數只有1100份的期刊,前任主編交接審計時我們還結余近200萬營收(按裕亭的思維,要賣多少本刊物才能實現啊)。不知還記得否,2020年第5期我們的一篇論文引起全國性“輿情”,各網累計點擊閱讀超過數十萬,這完全不是印數只有1100份的期刊可以做到的,我們做到了。我想這是不是應該顛覆裕亭的想象啊。
就期刊傳播影響力而言,網絡時代數字傳播、數字出版的優(yōu)勢已經不需要考慮甚至直接忽略裕亭以及裕亭們糾結的“期刊印數”這一傳統(tǒng)問題了。就“走市場”靠發(fā)行量“掙錢”的期刊而言,辦刊人也都在為期刊發(fā)展業(yè)態(tài)轉型進行積極探索并付諸實踐,比如《金山》,在辦刊理念上順應時代,積極探索網上《金山》、有聲《金山》、寫作培訓、書籍出版、文學藝術活動等,在內容上也進行板塊化革新,不僅吸引了廣大讀者,也承擔起文學期刊培養(yǎng)文學新人、繁榮文學事業(yè)的責任,使得《金山》的影響力大幅提升的同時保證經濟效益不滑坡、有增長。
因此,我認為期刊印數下滑是出版業(yè)時代轉型的表征,并不可怕,更不是裕亭說的“羞于啟齒”,反而能倒逼期刊人為探索順應時代的辦刊模式而努力。
袁龍
紙媒衰落,情懷依舊,文學不死。時代潮流,浩浩湯湯,若想再現洛陽紙貴之景象,何其難也!
紙媒的衰落主要是指紙質期刊出版物。本期討論的主題《羞于啟齒的期刊印數》與之前我們討論的投稿話題其實是有直接關聯(lián)的。期刊印數與發(fā)行相關,作為作者,可能只會考慮投稿問題,但作為期刊負責人,則必須考慮發(fā)行。期刊印數與發(fā)行量關系到期刊的市場生存空間問題。
在我的印象中,2010年至2014年,很多純文學期刊,如韓寒主編的《獨唱團》、安妮寶貝主編的《大方》、老牌文學雜志《大家》《萬象》等先后停刊,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發(fā)行量暴跌。以《大家》為例,1998年,《大家》開始走市場化道路,自負盈虧。由于文學市場邊緣化,純文學期刊的運行成本和稿費支出遠遠高于發(fā)行收益,發(fā)行量由原來的20000份跌至5000份,《大家》因此入不敷出,雖想出開設理論版增加版面收入,仍難以為繼。我們今天能相聚在《金山》雜志的“相峙南徐”,要感謝@嚴有榕 等期刊核心團隊的用心經營,為他們點贊!僅2020年,就有34家傳統(tǒng)媒體停刊。其中很多報刊的副刊曾刊登過微型小說。停刊后,微型小說作者就少了發(fā)表的園地。所以我當時發(fā)了一個朋友圈,感慨:唇亡齒寒……
雪弟
我倒是覺得,少一些陣地好。現在發(fā)微型小說的太多了,導致大家濫寫,一半以上的作品就不該發(fā)出來。
袁龍
發(fā)不出來的作品有很多進了“年選”,我們近幾期討論的話題其實都牽涉到微型小說的生態(tài)問題。當文化開始產業(yè)化的時候,我們身在市場化的場域,難以逃脫。
余清平
是的,我這里以前書店很多,街邊的報攤比比皆是,光春夢書店就有七八家,現在幾乎全沒有了,就剩一家春夢書店,還是以賣玩具為主。新華書店為什么行,一是有政府支持,二是學生的書、習題、卷子全部屬于新華書店經營。我每次去里面買幾本書,除了學生還是學生,幾乎沒有青年人。新華書店里經銷的雜志除了《故事會》就是《意林》,前幾年還有《微型小說選刊》《小小說選刊》,去年也沒有了。
袁龍
《微型小說選刊》和《小小說選刊》的發(fā)行量也在減少。以前高峰時都是數十萬發(fā)行量。
上善若水
余姚市政府里以前都是訂十幾份雜志,《小小說選刊》《微型小說選刊》等都有,現在我看不到一份,報刊亭也很少見,根本看不到這兩個雜志,這證明確實在萎縮,沒辦法,這是紙媒刊物的趨勢,發(fā)行量萎縮是正常現象。
余清平
充分挖掘紙媒能量,印數才不會羞于啟齒
每一年的新年伊始,在社交平臺上或者微信群里,總是看到一些爆炸性的消息——紙媒停刊的啟事。作為作者,也作為讀者,心有戚戚之余,恨不得有回天之力,“大庇天下作者俱歡顏”,讓紙媒多一些再多一些。不過,誰都知道,這期望是不現實的。紙媒存在即合理,但是,其停刊也有其“合理”的原因。
或許,很多紙媒的出版者還活在回憶之中。想當初,讀者一刊難求,雜志報紙出版發(fā)行量十幾萬冊、幾十萬冊,甚至幾百萬冊,這也不是什么可望不可即的事。像《金山》《微型小說選刊》,單冊發(fā)行幾十萬冊不是難事,因為,讀者多。作為讀者群中的一分子,我見證了紙媒的興衰史。我一直是個堅持訂閱刊物的讀者,且每年不止訂一家刊物,多的時候訂12家刊物。我訂閱刊物是從中學畢業(yè)后做老師時代起,直到現在,也只上世紀90年代初因為生活原因而中斷過幾年。閱讀,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嗜好。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紙媒“身強體壯、風度翩翩”的時候,市場也推波助瀾,到處是書攤、報攤、書店。幾乎達到讀者出門就能買到書報的程度。那時候,紙媒是寵兒,能養(yǎng)活很多人,能給市場帶來大量的經濟效益。一個報攤、書攤就能養(yǎng)活一家人,至于吃紙媒致富的出版商,也不少。然而,現在由于網絡、QQ、微博、電子書籍、微信等諸多新媒體的出現,對紙媒體的沖擊幾乎是致命的,造成紙媒的訂閱量迅速下滑,城市街道上的報攤、書攤幾乎絕跡,書店也因此紛紛改行。面對此情此景,總會有一些有識之士站出來,為紙媒的沒落而“把脈并診治”。
《金山》雜志,嚴有榕主編憂天下紙媒之憂,于2020年在《金山》雜志上辟出珍貴的版面,設“相峙南徐”欄,專為當下的刊物癥結把脈、診斷,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創(chuàng)舉,這是敢為天下先的一大壯舉,值得為之點贊的一件大好事,是刊物、作者、讀者的福音。
說內心話,我對紙媒一直抱有信心。直覺告訴我,畢竟像我一樣喜歡閱讀的人還不少,盡管大量年輕人沉溺新媒體,也有的是因為現在這快節(jié)奏的生活而抽不出時間閱讀書報,還有一個原因是部分人的自我提升意識沒有跟上來,都沒有意識到自我修養(yǎng)是通過一系列閱讀來提升的。改革開放這40多年來,物質生活還是擺在人們生活的首位,好好享受在思維里“霸屏”,但一旦大家生活富足,而精神沒有跟上,意識到閱讀紙媒的重要性,讀者群是否會回歸呢?穆罕默德說過“給你兩個面包,就要用一個面包換一朵水仙花”,為什么這么說?精神生活也很重要。我想大家明白了這道理,就會通過閱讀紙媒上刊載的作品,來獲得“水仙花”,這“水仙花”不僅僅能“修養(yǎng)”自己,更能影響后代。可以放眼看看,家庭中教育健全的父母親都喜歡閱讀。
現在,紙媒發(fā)行量下滑的這種狀況,我倒認為是紙媒在自我調整。我曾經與一些朋友辯論過,網媒雖然來勢兇猛,但是,有其致命弱點。一是不能長久保存,就像沒有倉庫的堆在露天地的產品,時間一長,就被腐蝕了(網站管理方會定期刪帖);二是作品質量良莠不齊,發(fā)表門檻低。網絡里雖然也有編輯放行,但是,那是一審制,對作品質量要求不高,故精品少(雖然像《盜墓筆記》《明朝那些事兒》等堪稱經典,可是,這些作品都無一例外地出了書。究其追求出書原因,也是意識到只有紙質書才能長久傳承下去)。而紙媒(雜志、書籍)則不同,不僅編輯眼光獨特,而且是三審制,還有,紙媒編輯對作品的把握能力強。
我任過多家網站編輯,更是寫過十多年的網文,也做過網站的站長,熟悉網絡操作程序。后來放棄網絡寫作,也是基于網絡的弱點。網絡變革時,首當其沖被刪除的,就是文學作品。像風靡一時的“榕樹下”網,作者發(fā)表的作品隨著網站的關閉被“毀尸滅跡”。
因此,我倒是覺得紙媒的高峰尚未到來。關于說紙媒已經衰落了,現在斷言,還真的為時尚早,因為,人們沒將紙媒(紙文化)挖掘出其應有的實效。現階段,紙媒被更便于閱讀的網絡“撞了一下腰”,這不應悲觀,應該說是紙媒發(fā)展中所必然遇到的。也許,這于紙媒的發(fā)展是一件好事。其實,紙媒體大有潛力可挖,還有許多功能,有待作者、出版社和刊物去探索。如何挖掘出紙媒應有的能量,我覺得在這幾方面可以考慮:一是作品的質量。好質量不一定是“陽春白雪”,也得有“下里巴人”,適合各層次的讀者,讓讀者自己去選擇閱讀。為什么四大名著一版再版不缺銷量?為什么《論語》不缺銷量?因為是佳作。二是紙質刊物可以當禮物相贈。煙酒、食品可以當禮物,書刊為什么就不可以?當人們的思維獲得轉變的時候,這一現象為時不遠,何況,現在就有許多人互贈書籍。三是紙質刊物易于保存,可以反復閱讀。比如,我們讀一篇小說、一篇散文,多年后想回頭再讀,紙媒的優(yōu)越性就體現出來,而新媒體刊載的作品幾年后或許已“尸骨無存”。四是出版物也可以參加展覽會,刊物可以采用吸收會員的形式,能夠增加訂閱量,會員就像明星們的粉絲。好作品好刊物,誰舍得放棄。五是推廣,達到紙媒無國界,實現全球化,通過交流擴大影響,擴大發(fā)行量。六是紙媒的多元化。也就是說,紙媒與新媒體相結合,這并不是無奈之舉,反倒是相融合,取長補短。紙媒上的作品放到網絡里、手機里,實行付費閱讀(網上早就有付費閱讀,只是沒有與紙媒相結合)。七是集團公司的涉足。有文學情懷的企業(yè)家們投入資金,辦出品牌雜志,像衣服、食品一樣創(chuàng)出百年老店。八是文化是屬于公眾的,是屬于社會的,也是屬于人類的,不能全部走市場化,要文化部門扶持。比如,一個人生病了,僅靠自身免疫力是不行的,該用藥就得用藥,該手術就得手術。文化與科技應該同等對待。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紙媒優(yōu)勝劣汰,關閉了一些,這是自然現象,是為了令存在的更好地存在,不必驚慌失措。甲骨文、竹簡、手抄本、刻板印刷,每一種的存在方式至少是幾百年,為什么今天活字印刷的紙媒就只有幾十年的壽命?不可能!因此,終上所述,得出結論:只要充分挖掘紙媒能量,印數不會羞于啟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