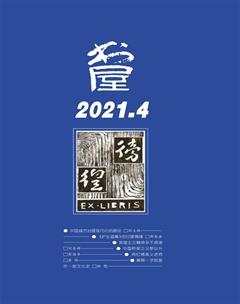熊希齡的“詩教”
秦燕春
一
湘人被視為國土疆域中性格甚為鮮明的一類。錢基博先生直以“地氣剛堅,民風強悍”擬之。但誠如深知湘人根底的沈從文所言,此地于激進與保守兩路常各趨其極。我的理解則是,激進或守舊,取舍并不第一重要,一旦取舍則一定要“趨極”,或者才是此地人最有風格的選擇。也正因此,某類于“趨極”之風中極力“守中”且同樣是用“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的“趨極”的力道來“守中”的人物,湘省就尤其難得。
這種心性特別又典型的湘人,湘西名城鳳凰第一個中進士點翰林之人、之后更成為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理的熊希齡便是極好的典范。
熊希齡緊湊忙碌的一生中充當過各種要角。不僅1898年“湖南新政”年少氣盛是核心骨干,不少要務都一任在肩、奔走在先。即使經歷了“戊戌政變”被革職管束,他也盡力襄贊地方教育乃至專注實業,更在1903年趙爾巽專折保舉復出后,高調參與了“易代之際”許多關鍵時刻。1913年8月受命出任北洋政府內閣總理,算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卻短暫倉促而禍亂叢生,僅僅維持八個月,1914年2月他就在一片羞辱聲中辭職下臺。對于這位視“保全名節”直如“八十老翁過危橋”(1910年3月9日致熊燕齡、熊岳齡函)的傳統儒士而言,他的傷痛一定苦不堪言。
這其中悲歡,熊希齡并非沒有預感,“今以浮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鮮恥世界,雖孔子復生,無補于世。希齡擬俟蒙邊少定,即歸營實業,不復與聞政事”,所謂“與現在之暴烈分子、腐敗官僚兩派絕不相容”。因此,這民國總理任上又帶上了些“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特有的悲壯色彩。
1914年,熊希齡辭去國務總理及財政部長后于民國政壇漸行漸遠,轉身繼續他早年熱心亦擅長的教育工作。賑濟災民、興修水利、平民教育之外,1920年10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專收孤貧兒童的“香山慈幼院”的成立讓熊希齡投入了余生大部分精力。身為世界紅十字總會中華分會會長、南京國民政府賑款委員,在一波接一波的天災人禍、戰火紛飛面前,熊希齡照樣任勞任怨,一秉其“實干”、“傻干”乃至“硬干”、“窮干”精神埋頭做去。
價值判斷與道德觀念經常陷入混亂的清末民初時局,對熊希齡這種實干心性其實很不利。他不僅經常要背上些莫名其妙的罵名、例如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參議會中激進派人士視其為“前清猾吏”,也似乎因此很難有舒舒服服施展拳腳的余地。葉景葵在《鳳凰熊君秉三家傳》中嘆他“平生似遇而實未遇,欲有為而終不可為”。揆諸其一生際遇,可謂知根底語。
因為“無可如何且潔身,保全人格作詩人”(《題畫菊》)的現實無奈,一生自負“辦事”而無意文學的熊希齡居然也留下了不算單薄的詩詞作品,至于朋友都會刻意提醒這位“實干家”不要擱意于詩:
經濟文章付外篇,獨將吟玩遣華巔。
蒼生猶望資霖雨,不信山泉老偓佺。
身為功底深厚的翰林學士,熊希齡如果試圖吟風弄月,他并非沒有機會。但他的詩詞就是他的性情,一以貫之。庚子年(1900)因政治變故避處湘西,《題蜀葵》中“物生原不貴,勁節始能奇。夕影雖偏向,孤心終不移”,以及《題雨景山水》中“故山千萬疊,煙雨暗難開。不畏風波惡,一帆歸去來”,都是勵志語。1930年,好友譚延闿過生,熊希齡寫下《金縷曲·戊辰冬壽譚祖庵五十生日》,稱道譚氏“十七年來堅苦事,要全憑旋轉乾坤手。容與忍,是首功。書生故態猶依舊。共流連,笑談歡樂,頓忘昏晝。末路故人多變節,誰是始終成就?真不負平生操守。”坊間廣為流傳關于熊希齡早年畫“木棉花”自題“此君一出天下暖”的故事更像后世針對慈善家生平志業的事后蓋棺,未必真實。倒是譚延闿本人寫過一首極耐人尋味的《豆花》詩:“自是人間有用身,不矜香色斗芳新。城中何限閑花草,只與游蜂哄一春。”用來形容熊希齡一生包括詩詞寫作,居然都十分允當。
熊氏詩詞風格穩健遣詞端莊,據說丹青也頗見功夫,但他顯然并不在藝事上太花心思,甚至早年還自謙稱“本無學術,只管辦事,不知其他”(1898年7月15日《為時務學堂事上陳寶箴書》)。這并不妨礙熊氏詩學其實飽含了豐沛的精神意義:一位傳統中國老派士紳特有的價值關懷,作為核心與基本的人格養成與情性化育,自然而然于詩學世界中豐沛流溢,并進而反身潤澤其精神質地。
二
一生以其特有的實干、傻干乃至硬干、窮干精神鍥而不舍救國救社會的熊希齡貢獻最為卓越者最終落實在了慈善教育。甚至對于教育,他也是傷心人別有懷抱。“破壞原為建設初”,對于清末民初這最先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儒者而言,現實的業力洶涌顯然遠遠突破了他們的精神預期,例如民初新進政治人的教育素質令他深感意外,“瓦釜雷鳴鐘毀棄,不堪重讀老人書”(《題顧子用所藏馬相伯先生序稿》),連教育也都已經很難維系他們曾經熟悉的理想教育了。
曾經對新建的民國懷有與時俱進希望的熊希齡被民初政局的翻云覆雨傷透了心,盡管當此亂世他算得上大節無虧。1926年12月3日,熊希齡寫下《丙寅十月二十九日為淑雅夫人五十初度賦贈》長篇敘事詩,于中基本涵納了自己五十六年來的系列遭際與反復思考。“余志在澄清,反為操莽嗾”可謂是民初最后的士人一片傷心之語。他不是不懂得,也不是不明白,只是他此刻仍然必須選擇“澄清宇內”的有為法,這是傳統之“士”的宿命。
熊希齡自知在逆流而動,“歷盡冰霜氣未孱,晚霞天半擁朱鬟。可憐世界皆成紫,獨有孤山不改顏”(《為叔通畫朱菊并題》),卻至老豪氣不衰,“奮斗艱難已半生,斬蛟射虎氣縱橫。回思三十年前事,夢里猶聞擊楫聲”(《題三十年前照片》)。于此,必須考慮到他獨特的近代湖南氣質,所謂學必“經世致用”,所謂“齡本草人,生性最戇,不能口舌以爭,惟有以性命從事”(《為時務學堂事上陳寶箴書》),所謂“實際能醫讀死書,古人曾有帶經鋤。埋頭硬干和窮干,怯弱身心病自除”(1934年10月3日《甲戌八月廿五日平民教育促進會景慧中學校紀念熊朱其慧夫人寄贈》)。
1919年因為調停“南北和談”失敗被指為“五四運動”的幕后推手,熊希齡傷心宣布“邇來厭倦政治已達極點,且深覺世界雖變,人心不變,政治社會均屬罪惡之藪”(1919年5月17日《聲明退出和平期成會不再過問政治致和平期成會聯合會電》)。但終其一生他都沒有真正放舍過“天下”。1910年寫給兄弟的信函中尚有如此溫熱的關懷:“蓋吾人所擔當者,國家之事,關系于公眾安危,非一人一家可比。故以世人比兄弟,則兄弟為親,而以國家比兄弟,則兄弟為輕,國家為重也。……古人云:公極則私存,義極則利存。義利之界不容紊也,紊則求榮反辱矣。……夫人當境遇困難時,愈宜站定腳跟,不為利動,不為茍且之事,方是豪杰。”(1910年3月9日《批評其不識大體致壽峰三弟捷三七弟函》)
兵荒馬亂的生民流離在熊希齡不足古稀的一生中基本一直都在持續。他日常生活的具體感受就是“頭緒紛紜中,掛一恐萬漏。東扶西又倒,此起彼又仆”。對于民生疾苦,他始終就是“放不下”。這是不能“放下”,更是不肯“放下”,這是儒者的“民胞物與”,更是佛門的“大乘菩薩”。因為“彝師、澤老均已化去,僅余鄙人,奔走道途,一事無成,殊有愧于作者矣”(1915年9月1日《告知旅途情況致朱淑雅夫人函》),對于他所繼承的傳統而言,“神州袖手”都是無法接受的逍遙,他一定也應該繼續“有為”,即使這“有為”需要不斷調整、經常飽受委屈。
關于不再參與彼時愈演愈烈的軍閥政治,熊希齡是毫不動搖的,寫于1918年的《戊午和趙式如雙清別墅原韻》中他視此退步抽身為具有自知之明的急流勇退、壯士斷腕之舉:
樹色山光雨后勻,長松不改四時春。
雙泉石上湍流急,似策當機勇退人。
但退出政界乃至實業都絕不意味著放棄責任。他一直在各個領域埋頭苦干,更時時都在努力體現一種“忘我”的精神、探索一種以“無為”、“出世”之心行“在世”、“有為”之法的可能性。1917年1月5日他寫下《登泰山絕頂觀云海》,即表達了這種于“真空”中行妙有的愿景。1918年的《戊午旅行江南題棲霞寺天女散花圖》同樣毫不猶豫宣稱自己投身苦海的決心:“擾擾何時見太平,眾生苦痛已非輕。原憑妙手回春力,不治維摩治眾生。”
時隔四年之后,香山慈幼院已成立有日,《游森玉笏》(1922年5月)再次重申了這一發愿:“遠看塔影漾湖波,又聽群兒唱晚歌。唯念眾生無限苦,萬松深處一維摩。”
雖處居家而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卻常修梵行的維摩詰居士是他追隨在心的表率。如何能夠處相而不住相、對境而不生境;直心正念真如,親證平等實相;具足恒沙煩惱無量功德,起方便教化,使一切眾生除心源上之煩惱、顯心源上之功德。這應該是深喜佛教的熊希齡最看重的。
三
發愿尚屬容易,一生堅持甚難。無巧不成書的是,熊希齡早年有個齋號即是“有恒”,正見其心志。熊氏生命最后二十年操持慈善幼教的過程可謂一波三折、艱苦備至。借著他善于實務的實干、傻干、硬干、窮干精神,他一次又一次化險為夷。
罕見的是,熊希齡正面批評1919年前后發起的這波“新文化運動”,但這位晚清新政曾經最勇銳無惑的老“運動員”于此的實際批評恐怕無所不在:“近年國人浮慕文明,偏重物質主義,對于精神教育棄之不顧,雖學業技能皆有所長,而于人情物理毫無常識,即飲食、居處、言語、動靜、應對、進退之間,亦覺其雜亂粗鄙,無秩序,無條理,無輕重,無緩急。”(1928年《慈蒙新課本序》)
香山慈幼院堅持“教育意義,重在審辨真偽,明定是非,若因回避責任而自欺欺人,即屬教育破產,人格破產”,養成“人格”一直被他視為無論踐行教育理念還是養成社會環境的最重要標準,“養全他的廉恥”成為慈幼的核心(1922年6月《香山慈幼院創辦史》“現在的缺點”)。依其慈愛細膩的天性以及與時俱進的精神,傳統教育出身的熊翰林甚至對于兒童的天性應該如何順勢而教,都有入微考量。而從對“學生自治會”的效果深感滿意可以看出,熊希齡依然是那個晚清時期最樂于和西方對接的新銳的現實派。
他很傳統,看重“婦順”的美德,但他又有很現代的一面。1928年侄女生日他寫詩以祝,重申“賢母良妻”時論之外,更強調“蒙養”與“母教”的關系,對女性做出了社會學意義上的充分尊敬:“家事即職業,工作獨女負。男實依賴者,是言誠不謬。”1929年他親自撰寫《慈幼院女校上工歌》中也表達了這一思考:“一家生活女當沖,男兒何有功?親井臼,習烹縫,尤須薄記工。”
熊希齡生命后期對“平民教育”投入甚多,一則配合了清末民初啟蒙救亡的時代趨勢,二則,其實是戰亂頻仍、民生凋敝、生靈涂炭的現實壓力讓這位“務實”的干家不得不先顧吃緊處,完其慈悲救世的一腔關切:他先后創辦了北京北洋平民工讀學校、湖南平民大學、長沙兌澤學校、孔道學校。1921年12月與蔡元培、黃炎培等人創辦中華教育改進社,1924年8月由其夫人首倡發起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靠什么支持此際人類搖搖欲墜的精神世界?儒學之外,熊希齡對佛教的好感與親近是毋庸置疑的,這也同時成為他一生最強有力的思想支柱。
1898年,那場大病之后,對于因緣果報之說就頗令熊希齡生信好之心。1916年4月11日,身在常德的他寫給夫人信札中已經在明確索要“余之佛教書”。對于熊希齡一生的意義取舍而言,他是佛徒還是儒生,或者對道教是否有實踐都不是第一要義,關鍵在于他一直堅信“信道創于前,行慈繼于后”。早在1910年1月15日寫給堂弟熊岳齡處世產業函中,已經涉及如下幾個熊希齡待人處事的原則:其一,“(合于商業破產之法)即問之于心,對天地鬼神而無愧”;其二,“吾輩做事,只要合理,即格外險阻,亦復何懼”,“信之一字勝于身命,茍合乎義,即為弟事掛誤,亦所甘心”;其三,“古之君子,惟患難乃見其真”,“艱難仗友生”。無論“天地鬼神”還是“合理”守“信”,都是恪守現實標準之上還另有道義原則,對于熊希齡和他稔熟的文化傳統而言,人格教育原本就關乎信仰問題。
“法到圓時猶應舍,虛空粉碎有何哀。”(《游臺山中臺》)因為這種信仰的力道,熊希齡埋頭“辦事”的一生——他有多忙,看其一生存世文章絕大部分都是各種電報公函,最可見得逼真——主調與基調始終都是積極光明的。佛教中“色身非凈,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何物為我,我實不存。我既無我,朽骨何靈?凡相虛妄,焉用佳城”的基本理則,對于熊希齡的生命狀態,并無消極避世的味道,而是一直向更積極救世的層面轉化,此即1932年春《為香山生壙自撰墓志銘》中的宣稱:“今當國難,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許國,遑計死生!或裹馬革,即瘞此塋。隨緣而化,了此塵因。我不我執,輪回不輪。”
因為活泛而務實的性格,熊希齡并不拘泥于自己的背景與趣味,他考慮到學生未來的就業情況,主張香山慈幼院行白話教育——回思清末“湖南新政”中的類似舉措,則熊希齡實在是晚清最勇銳新進之人。他自己后期經常為嬰兒教保院撰寫白話標語對聯,親自用“醉桃源”詞調為香山慈幼院的孩子寫下《上床歌》、《下床歌》、《飯前歌》、《飯后歌》、《上課歌》、《下課歌》等系列口語化的歌詞。這位按理只會將“玉米”稱作“苞谷”的湖南翰林,居然學會了使用“棒子”這個北方民間稱謂!
1937年,在“淞滬抗戰”的槍林彈雨中,一生務實年近七旬的老人每天堅持打坐,卻依然堅守在救亡一線,一如既往做了許多瑣碎樸素、沒有華詞麗句卻件件人命關天的事:
當戰事初生時,亦有勸余遠走者,余以老病之軀,又無官守言責,本可行就安全之地,但以國難當前,余亦國民一分子,應為國家社會稍盡義務,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決計留滬,與紅十字同仁從事救護工作,設立臨時醫院四所,難民收容所八所(此專指十會而言,其他團體尚有百余所),共救出傷兵千余人,難民十五萬余人。
這是熊希齡1937年9月20日身在滬上寫給內侄朱經農的信。僅僅二個月之后,他遽然病逝香港。
因為暮年豪舉,所謂“艷詞清福”,熊希齡六十六歲高齡續弦子侄輩的毛彥文還留下生命中空前絕后一批“情書”而令后人議論紛紛。其實,熊希齡性格的真摯細密同樣體現在私生活,例如他終生反對納妾。熊希齡垂老和毛彥文結合更帶有尋覓志同道合“同志”的意味——在其身后繼續他和亡妻堅持多年的“香慈”事業。情路坎坷而又恩深意長的毛彥文“有協助他辦理此事的能力、熱情與愛心”。至于何以誕生了那些和熊希齡絕大多數詩詞風格迥異的“艷情”之作,這其實要從毛彥文本人的情感際遇講起。經由這段婚姻,我們會有機會見識到“鳳凰才子”共感共情的精神風姿。熊希齡不僅是清末與民國在政治、實業、教育皆能獨當一面的科舉能人,就其處理與毛彥文的感情的方式而言,他更像全新的人物——或者我們不妨說,傳統文化養成的儒者與君子也并不缺乏現代意義上的“愛的能力”。這是另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