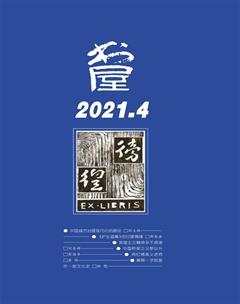再憶傅高義老師
當(dāng)2020急景殘年之時(shí),美國再掀狂瀾的新冠疫情加上晴天霹靂般的傅高義老師噩耗,令我多日寢食不安。天地蒼茫,凜冬已至,臨風(fēng)懷想,不禁百感千端縈懷,于年末寫下悼詩一闋:
悼傅吟
驚聞哈佛傅高義教授驟逝,哀感無端。傅者,父也。傅老師喚我為“中國兒子”,我們見面必以“父子”相稱。
天涯枯轍頗離枕〔1〕,厚衾暖月忘夜沉。
樹蕙唯知蔭涸澤,滋蘭但識(shí)解危心。
詩存諸往啟來者〔2〕,文立孤標(biāo)試石金。
牛渚〔3〕溯源悲俛仰〔4〕,登舟空憶淚沾襟。
〔1〕頗離枕,見溫飛卿:“水晶簾里頗離枕。”古指留宿處。只身留美第一年后,洛城加大因故忽然斷了原來承諾的獎(jiǎng)學(xué)金,傅高義老師馬上把我邀到哈佛擔(dān)任研究助理,并請我住進(jìn)他的家中。
〔2〕《論語》:“詩,告諸往而知來者也。”
〔3〕牛渚,寓“知音遇合”。語見《世說新語》:晉朝貧士小工袁宏于牛渚遇謝將軍賞識(shí)的故事。李白詩曰:“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云。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4〕王羲之《蘭亭集序》:“俛仰之間,已為陳跡。”俛仰,即俯仰。
此詩,又引出了更多的久遠(yuǎn)追憶。
1980年,因?yàn)楦蹈吡x老師的熱心建議和推薦,我方才有改變?nèi)松呦虻母懊懒魧W(xué)旅程。但我當(dāng)年從洛杉磯加州大學(xué)到哈佛大學(xué)——自太平洋至大西洋的“兩洋水”之行,卻有許多瑣細(xì)關(guān)節(jié)不易言述。比如,我的“哈佛生涯”,說來其實(shí)是“二進(jìn)哈佛”,一如上述注釋里所言:1982年春我抵洛杉磯加州大學(xué)(UCLA)讀研一年后,因指導(dǎo)教授學(xué)術(shù)休假一年,校方竟然中斷了原來承諾給我的獎(jiǎng)學(xué)金,我的學(xué)業(yè)一時(shí)陷入中斷尷尬,生活也處在孤立無援之境。時(shí)任哈佛費(fèi)正清東亞中心主任的傅高義教授聽聞,馬上給我寄出了東亞中心的正式邀請信,以訪問學(xué)者的身份邀我擔(dān)任他的研究助理,并請我住進(jìn)他在哈佛校園的家中,不但一解我的燃眉之急,也因之打開了哈佛學(xué)府的高檻大門。哈佛一年后,加大的指導(dǎo)教授學(xué)術(shù)休假結(jié)束回返校園,他馬上設(shè)法幫我爭回減免學(xué)費(fèi)的獎(jiǎng)學(xué)金,我于是又在1984年秋天回到加州大學(xué)校園,繼續(xù)修讀完成我的東亞文學(xué)碩士學(xué)位課程。加州大學(xué)采用的是學(xué)季制(三個(gè)月為一學(xué)期)。我于1985年夏天獲得碩士學(xué)位后,傅高義老師又一次邀請我再赴哈佛,同以訪問學(xué)者身份受邀到費(fèi)正清東亞中心,并再次住進(jìn)了他的家,繼續(xù)擔(dān)任他的中文研究助理。
兩次進(jìn)出、頭尾兩年半的哈佛訪學(xué)生涯,與傅高義老師夫婦的朝夕相處,成為我當(dāng)年的留美經(jīng)歷中學(xué)旅最充實(shí)、“含金量”最高的“高光”段落。因?yàn)椤肮稹碧烊痪哂械母吲_(tái)階與寬視界,還有“訪問學(xué)者”身份的選課自由與時(shí)間寬裕,我能有機(jī)緣把自己完全浸潤在跨學(xué)科的書籍學(xué)養(yǎng)的海洋里——參與和旁聽東亞中心每周的各種與中國有關(guān)的講座,以及住家附近的猶太博物館、藝術(shù)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與科技館隨時(shí)舉辦的各種活動(dòng)(科技館的電影廳是我最常流連的場所,可以免費(fèi)觀看各種新近流行的電影和文獻(xiàn)片)。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占據(jù)了書庫角落的一張固定小桌,把書庫各門類自己列了計(jì)劃要讀的書籍擇出堆在一角,那里是我每日潛心讀書寫作的僻壤靜界(我的留學(xué)生小說集《遠(yuǎn)行人》的大多數(shù)篇什完成于此)。我以哈佛身份證購買了“美利堅(jiān)即景劇場”的年度演出季套票(看六場演出只需三十八美元),兩年間幾乎看遍了當(dāng)時(shí)在哈佛上演的所有先鋒實(shí)驗(yàn)戲劇(由觀劇引發(fā),1988年北京《讀書》雜志以連載五期的大篇幅,刊發(fā)了我與畫家袁運(yùn)生共同署名的“關(guān)于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胡言亂語”系列);忘記是哪一位學(xué)長建議,我還曾多次到建筑學(xué)院的階梯課室旁聽設(shè)計(jì)比賽評圖,記得其中一次是圍繞波士頓市政廳的改建設(shè)計(jì)方案評圖,各種標(biāo)新立異的設(shè)計(jì)及其激烈火爆的爭議讓我大開眼界,用今天網(wǎng)絡(luò)語匯,則是“腦洞大開”。更不必說,對于我這位古典音樂的“發(fā)燒友”,圣殿般的波士頓交響樂廳和哈佛紀(jì)念堂音樂廳以及那個(gè)聞名遐邇的超過百年歷史的哈佛男聲合唱團(tuán),那一場場無與倫比的音樂會(huì)了。特別是,與“文革”后最早留學(xué)哈佛的第一批中國大陸人文學(xué)科的學(xué)兄學(xué)長如趙一凡、張隆溪、巫鴻、葉揚(yáng)、馮象等的日常交往交流,還有哈佛華裔教授如張光直、杜維明、趙如蘭等對我們的關(guān)照教誨,所給予我的特殊滋養(yǎng)了(那時(shí)候楊聯(lián)陞教授還健在,可惜與我們交集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據(jù)張光直教授告訴我,每月最后一個(gè)周五在趙如蘭教授和陸惠豐教授家輪流舉行的“康橋新語”華裔文化沙龍(開始叫“康橋夜譚”),就是他們幾位哈佛華裔教授有感于校園內(nèi)的中國大陸和臺(tái)港人文留學(xué)生愈來愈多,特意為促進(jìn)美中多地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而用心開設(shè)的。“康橋新語”沙龍日后成為堅(jiān)持?jǐn)?shù)十年、在美國東部院校名聲顯赫的一個(gè)文化景觀,東部各校許多名家教授與博士生都常常聞風(fēng)而至。我呢,當(dāng)時(shí)是沙龍里的“茶童”,大家叫我“茶博士”(Dr.T,借用當(dāng)時(shí)電視肥皂劇里一個(gè)搞笑角色的名字),專門負(fù)責(zé)給與會(huì)學(xué)長們沏茶遞水和遞送每晚的夜宵八寶粥。
正是傅高義老師為我敞開了哈佛學(xué)宮的大門,使我得以縱情暢游在知識(shí)與學(xué)術(shù)的溪澗、河川與海洋里,像海綿一樣、花蕊絨毛一樣,吮吸著科學(xué)與人文的諸般雨露陽光和精神養(yǎng)分,完成自己去國前夕立下的“把自己徹底打碎,再重新捏吧回來”的生命重塑宏愿。這是傅老師賦予我這一生命的奇跡,我將感恩終生,銘記終生。
我當(dāng)然知道,近時(shí)坊間對傅高義老師及其學(xué)問文章的評論見解趨于兩極化。而對此“兩極化”議論最敏感、也最能包容的,恰恰正是傅高義本人。記得2011年秋天在耶魯,傅老師把兩大厚本的中、英文版《鄧小平時(shí)代》贈(zèng)予我的當(dāng)時(shí),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現(xiàn)在對我這本書的評價(jià),無論在美國或在中國,都有兩極化的評論。喜歡的,有很高的評價(jià);批評的,也把話說得很重。其實(shí),這兩方面的意見,我都很了解,也很能理解,雖然我仍舊是堅(jiān)持自己的基本判斷的。他在耶魯關(guān)于這本書的講座上的開場白,也是重復(fù)說著同樣的話。而傅高義老師多年來多次對我說過的——正如他一直在美、中、日三個(gè)文化、政治系統(tǒng)里身體力行地在做著的——?jiǎng)t是他重復(fù)多次的另一句話:“Bridge。”“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在各種兩極化的看法和差異之間,搭建一道橋梁,我做的就是橋梁Bridge的工作。”他早年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xùn)》是如此,近年的《鄧小平時(shí)代》更是如此。近時(shí)坊間很多談?wù)摳蹈吡x的文字,會(huì)引述筆者前述拙文里提及的傅老師對我談到的從“局外人”(outsider)到“局內(nèi)人”(insider)的角度,以及“在中國語境中去認(rèn)識(shí)中國”的意見。但上述話題,其實(shí)每次都是在傅老師提及他最喜愛的一位學(xué)生——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時(shí)提及的。他多次向我感慨:他是從Perry身上,領(lǐng)悟到這個(gè)要從“局外人”轉(zhuǎn)化到“局內(nèi)人”的角度去認(rèn)識(shí)中國的道理,這就是“在中國語境中去認(rèn)識(shí)中國”的意思。在我看來,無論傅高義或林培瑞——我深為熟悉的這兩位觀點(diǎn)去向或許不一定一致的洋人漢學(xué)家,都是兩位極難得的、真正愛中國、“把中國的事情當(dāng)作自己的事情”的人。林培瑞是“愛之深而責(zé)之切”,而傅高義則更多地取“了解之同情”的角度。關(guān)于這個(gè)“了解之同情”的說法,傅高義老師也曾在好幾個(gè)訪談中提及。此說,其實(shí)出自陳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寫的《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上冊審查報(bào)告》的開篇:“凡著中國古代哲學(xué)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xué)說,應(yīng)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而在陳寅恪先生之前,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的序言里也曾說過:“(讀此書)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這“了解之同情”與“溫情與敬意”,用傅高義老師自己的語言,就是做“Bridge”——搭建在國族與文化差異中的交流交通的橋梁。或者,也就是近期許多回憶傅老師的文字里不斷提到的“同理心”與“共情能力”吧。
都說“歲月不欺”。但歲月卻常常欺負(fù)我們的時(shí)光記憶——對許多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的追憶,會(huì)發(fā)生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誤差。比如近時(shí)紀(jì)念傅高義老師的諸篇文字里都提到:他是于2000年自哈佛大學(xué)榮譽(yù)退休的,那件印有他的漫畫頭像的T恤上也有“2000年退休紀(jì)念”的字樣。但因?yàn)槲矣浀米约旱母赣H是2003年末去世的,我在文中提到的,在傅老師稱我為他的“中國兒子”的那個(gè)酒會(huì)上,我明確提到了自己剛逝去的父親,這樣的記憶又是異常清晰的(我甚至記得我當(dāng)時(shí)用的是什么英文單詞去表述),那就應(yīng)該是2004春天的事情啊。難道,那次活動(dòng),不是2000年傅老師榮退的哈佛酒會(huì),而是日后哈佛大學(xué)專門為紀(jì)念傅老師退休而舉辦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的酒會(huì)?(耶魯史景遷教授榮退一兩年后,耶魯校方也專門為此籌辦了一個(gè)專題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我也只能這樣去解釋自己的記憶渾誤了。
附錄一:
我寫給傅老師夫人Charlotte Ikels(艾秀慈)的悼念卡的文字(中文本):
Dear Charlotte,接到傅老師驟逝的噩耗,我和妻子孟君都震驚哀痛不已!悲傷的心情至今沒能平復(fù)。傅老師是我生命中的貴人、燈塔和人生的楷模!他不但是搭建在美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一座美好的文化橋梁,也是照亮我生命的一道美麗彩虹。他真的是我的“美國爸爸”,而我也以能成為你們的“中國兒子”為榮!我深深感受到您的哀傷和震撼,請接受我和孟君的深切哀思與安慰,和對傅老師永遠(yuǎn)的懷念!
您們的“中國兒子”蘇煒和孟君
2021年1月2日于耶魯
附錄二:
我們的“中國兒子”
——為蘇煒的中文著作序
傅高義
當(dāng)1980年我第一次能夠踏入中國去做研究的時(shí)候,我和我太太Charlotte Ikels教授住在廣州的中山大學(xué)。我們作為大學(xué)的客人在中大校園住了兩個(gè)月。在那期間,我們可以參加中山大學(xué)的一些活動(dòng),并對廣東做一些初步的研究,參觀學(xué)校、公社和工廠。
就在1980年的那個(gè)夏天,我有機(jī)會(huì)認(rèn)識(shí)了一些中山大學(xué)的教授和學(xué)生。蘇煒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蘇煒當(dāng)時(shí)是中文系文學(xué)專業(yè)的,他是學(xué)生文學(xué)雜志《紅豆》的主編。他很有文學(xué)才情,已經(jīng)發(fā)表了一些短篇小說。我和我太太看到,那時(shí)的蘇煒有很多朋友,在中山大學(xué)的各種活動(dòng)中表現(xiàn)很活躍。那時(shí)候,正是1977年恢復(fù)高考不久,一些大學(xué)的教材還沒有全面修訂,大學(xué)的許多建筑也比較老舊,正在修復(fù)中。蘇煒向我們介紹了大學(xué)生的生活。那時(shí)八個(gè)學(xué)生住在一間宿舍里。學(xué)生的伙食非常簡單,穿著也非常樸素。每天早晨都聽到高音喇叭在播報(bào)新聞。校園里沒有電視,當(dāng)然更沒有手機(jī)。
在我們抵達(dá)中國之后的那些年里,幾乎所有的大學(xué)生都是高中畢業(yè)那一年進(jìn)入大學(xué)的。但是蘇煒卻不同,他在那個(gè)年齡時(shí)像很多其他同齡人一樣正在農(nóng)村插隊(duì),他和眾多在農(nóng)村插隊(duì)的學(xué)生一起準(zhǔn)備高考,最后通過考試才進(jìn)入了大學(xué)。雖然蘇煒的年齡比那些高中一畢業(yè)就上大學(xué)的學(xué)生大一些,但是他的氣質(zhì)仍然像一個(gè)年輕的男孩子。他的眼睛總是睜得大大的,總是帶著渴望學(xué)習(xí)的光芒。
蘇煒成長于廣州一個(gè)大家庭。我們后來有機(jī)會(huì)認(rèn)識(shí)了他的家人。他們當(dāng)時(shí)住在廣州一個(gè)比較簡陋的家里。他的家人看起來都是知識(shí)分子,他兄弟姐妹中的大多數(shù)都考上了大學(xué)。當(dāng)時(shí)的大學(xué)生都很害羞,不習(xí)慣也不太敢跟外國人打交道。蘇煒卻很愿意與我們見面,幫助介紹中國的情況,告訴我們他“下鄉(xiāng)知青”的經(jīng)歷。他解釋說,他當(dāng)“下鄉(xiāng)知青”,是因?yàn)樗?dāng)時(shí)被下放到海南島的一個(gè)農(nóng)場。我和我太太后來得到許可,可以去海南島參觀;而蘇煒也被允許陪同我們一起去海南,回訪他當(dāng)時(shí)下鄉(xiāng)的一個(gè)有名的國營農(nóng)場。那里有一個(gè)國家熱帶研究所,位于蘇煒下鄉(xiāng)的農(nóng)場附近,對許多國營農(nóng)場的橡膠樹進(jìn)行研究。
蘇煒帶著我一起回到了他曾經(jīng)下鄉(xiāng)的村子。那是蘇煒離開已經(jīng)四五年以后第一次回去。當(dāng)一個(gè)老農(nóng)看到蘇煒時(shí),立刻大叫“蘇煒!”然后緊緊抱住他,就像抱住一個(gè)多年不見的兒子。他看到蘇煒非常高興,蘇煒也非常高興,他們真的像是分別了多年的父子一樣。
我在中山大學(xué)認(rèn)識(shí)蘇煒幾年以后,蘇煒作為中國文學(xué)專業(yè)的學(xué)生進(jìn)入了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分校。在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分校學(xué)習(xí)以后,他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獲得了哈佛大學(xué)的入學(xué)許可,并成為我的研究助理。
蘇煒在哈佛大學(xué)兩年多的時(shí)間里,他住在屬于我和我太太的房子的一個(gè)房間里。那時(shí)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經(jīng)上了大學(xué)住在別的地方。我和我太太真的把他視為我們的兒子。即使蘇煒已從中山大學(xué)畢業(yè),并且獲得了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分校的碩士學(xué)位,他仍然保有一個(gè)年輕男孩的活力和好奇心。那時(shí)蘇煒又繼續(xù)發(fā)表了一些小說,他用中文和我談話,通過幫我閱讀他寫的小說,來教我學(xué)習(xí)中文。在哈佛期間,蘇煒有很多朋友都是中國學(xué)生。他的房間成了中國同學(xué)晚上聚會(huì)的最佳地點(diǎn)。他們常常在一起討論美國的生活和在中國的經(jīng)歷。
蘇煒還在繼續(xù)寫他的小說和散文。我和太太都為他能在耶魯大學(xué)教授中文感到非常驕傲。我從我們的耶魯朋友中聽到,他是一個(gè)非常受歡迎的老師。我們也為他的長篇小說被翻譯成英文并正式出版感到異常興奮,同時(shí)我們也為他中文精選文集將要出版,感到由衷的興奮和驕傲。我們?nèi)匀徽J(rèn)為他是我們的兒子——“干兒子”。
2018年5月23日于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