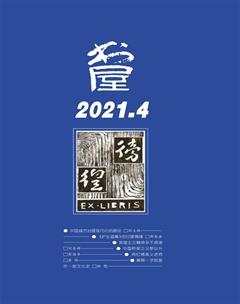心之所善,九死未悔
王澄霞
被譽為“文壇常青樹”、民國十大才女之一的蘇雪林,以散文集《綠天》和自傳體小說《棘心》登上五四文壇,其后大半生則以屈賦研究和神話研究聞名學界。縱觀這位一直自命“五四人”的非凡一生,她才華之出眾,成就之驕人,因渴求新知而遭受打壓之殘酷,抗爭之激烈,及其性格缺陷之醒目,俱現一身,足為今人提供借鏡。
一
蘇雪林的前半生備受封建專制社會的殘酷打壓,作為女性的基本權益被剝奪殆盡。首先是身體遭受摧殘,她四歲起被祖母纏足五年,“日也纏,夜也纏,終于把我的腳纏到她理想的標準了。可是使我成為‘形殘,終身不能抬頭做人了”。其次是不被允許上學讀書,屢屢被剝奪受教育權利。再次是被強制接受包辦婚姻,婚姻自主權利被剝奪,身心遭受極大摧殘。其間又遭受經濟來源上的壓制,生活幾度陷入困頓,幾次被迫輟學等。但蘇雪林毫不屈服,倔強堅韌,拼命掙扎,拼死反抗。曲折坎坷的人生經歷造就了她的倔強個性,畢生堅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徹底掙脫專制家庭走上社會,終成一代大家。
蘇雪林的求學之路充滿坎坷浸透血淚。蘇家雖非名門,但也足稱當地大戶,無奈家庭極端保守,一家之長的祖母“偏又是一個冷酷專制的西太后一般的人物”,“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根深蒂固,所以,蘇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樣讀書,只是圖及孫女將來能教自己念經和代為寫信記賬,信佛的祖母才破例開恩,允許七歲的蘇雪林跟著叔叔及兄弟們“名不正言不順”地在祖父衙署所設的家塾里跟讀。跟讀不及一兩年,男孩子們相繼進了新式學堂,家塾里的教書先生本不固定,她不得不輟學。1914年,在叔父幫助下,十七歲的蘇雪林得以進入安慶當地一個教會學校培媛小學讀書。僅讀半年,因隨母遷回祖籍太平縣嶺下村,學業又止。不久,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范登報恢復招生,得知消息的蘇雪林“萌生了要受教育的自覺心理,但同家庭辛苦激烈的斗爭也于焉開始”,“費了無數眼淚、哭泣、哀求、吵鬧”,頑固的祖母一意不允,蘇雪林只得以死相拼。她曾回憶說,愈受壓抑,求學之心愈加熱烈。到后來竟弄到如醉如癡,飯不吃,覺也不睡的地步,甚至獨自跑到一個離家半里、名為“松川”的樹林里徘徊再三,幾回都想跳下林中丈許深澗自殺。“若非母親因對女兒的慈愛,戰勝了對尊長的服從,攜帶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則我這一條小命也許早已結束于水中了”。1919年,已是安徽第一女師附小教師的蘇雪林,為了走出目光如豆的閉塞省城,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師范進一步深造,“我想前去赴考,赴考前必須通過家庭這一關,這一仗打得比民國三年投考安徽省立第一女師更加激烈百倍”。此時她已被家庭許配婚姻,“家人也預料到她求學野心無底止,所以要趁這個機會,逼她出嫁了事”。只為“要求上進”這一念,為到京城繼續升學,反抗家人逼婚,她又一次以死相抗,“不茶不飯,僵蠶似的僵在床上七八天,終于觸發了她的宿疾,而害了一場性命危于呼吸的大病”。蘇雪林當時患上了因結核桿菌侵入淋巴結而引起的瘰疬病。因為危及生命,家中尊長遂不敢逼她完婚,并同意她赴京應考高等女子師范,滿足她繼續升學愿望。“‘升學,‘升學,費了那么大的奮斗,付了那么大犧牲!”1921年,直至通過了法國里昂中法學院留學資格考試后,二十四歲的她才告知父親,并在離京出發前一天才寫信告知母親,就是憂及家庭對她讀書上進的一貫反對。在法留學期間,屢屢遭受經濟煎迫,再加疾病纏身,原本七年的留學期限只得縮短兩年提前歸國。
二
蘇雪林前半生飽受挫折,促成了她性格的倔強堅韌,在艱難處境中刻苦精進,頑強奮斗,這一個性又造就了她在文學創作尤其是學術研究上的斐然成就。
蘇雪林是新文學早期的重要女作家。她的文學創作主要有散文集《綠天》(1928)、《青鳥集》(1938)、《屠龍集》(1941),自傳體小說《棘心》(1929)、小說集《蟬蛻集》(1945),傳記作品《南明忠烈傳》(1941)等。其中《綠天》、《棘心》曾多次再版,并被入選中學語文教材。文史專家阿英曾贊許她是“女性作家中最優秀的散文作者”。
高校從教開啟了蘇雪林的學者之路。1928年她擔任上海滬江大學教授,次年任蘇州東吳大學教授,1930年任安徽省立大學教授,1931年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在武大任教達十八年之久,與凌淑華、袁昌英一起被戲稱為“珞珈三劍客”。其間出版了《李商隱詩》(1928)、《蠹魚生活》(1928)、《李義山戀愛事跡考》(1927)、《唐詩概論》(1934)四本學術著作。蘇雪林1952年任臺北師范學院教授;1956年直至1973年退休一直擔任臺灣成功大學教授,其間曾于1964年應聘赴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一年半。
蘇雪林學術成果豐碩,成就斐然。她勤于耕耘,廣收博蓄,態度之勤勉,治學征引材料之詳備,令人驚嘆。屈賦研究是蘇雪林半生的事業,從1943年應約寫稿《〈天問〉整理的初步》開始,到1973年,出版一百八十萬字的《屈賦新探》,歷時近半個世紀。蘇雪林對楚辭及其神話的梳理和論證,不但融會貫通了中國“官方”與“民間”的兩大文化主流,而且找到了組成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線索,進而證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以及“中國文化亦世界文化之一支”的大膽發現。正如印度文化研究專家糜文開在《屈原研究的新發展》一文中所評價的那樣,“蘇女士的屈賦研究,竟從發現一些礦苗,挖出‘先秦時代外來文化考的大礦藏來,而這大礦藏竟又連通著‘世界文化同源說的更龐大的世界礦藏的。這不可不說是一個驚人的大發掘”。現在雖有學者指出蘇雪林的神話研究忽略了一個民族的神話既有民族自身的主體創造,也可能接受其他多民族文化的影響之可能,有陷入泛巴比倫文化的窠臼之嫌。客觀而論,迄今為止關于楚辭或屈賦的研究成果不計其數,但放眼世界文化圈,溝通中西文化,開創跨文化研究的先河,拓殖楚辭研究的新天地,則不能不歸功于蘇雪林先生。
蘇雪林的學術成就要歸功于她的執著和堅韌。在武漢大學任教時,她將自己對楚辭與世界神話關系的零星發現著文請教同道,被視為無稽之談而遭不屑,但這毫不影響她在自己認定的學術方向上繼續頑強前行。1950年,蘇雪林二次赴法,搜集關于楚辭的研究資料。在巴黎,她依靠從國內帶去的工薪節余,省吃儉用,不久便因經濟拮據,身體欠佳,在他人資助下于1952年乘船返臺。于此種種都可見證她的精進努力,她對學術的熱誠與癡迷。
三
評價蘇雪林,她的半生“反魯”亦為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蘇雪林對魯迅生前死后的態度可謂冰火兩重天。魯迅生前,她曾謙稱自己是魯迅的“學生”,并撰文對其《阿Q正傳》等小說創作給予很高評價,稱“魯迅是中國最早、最成功的鄉土文藝家,能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誰都知道魯迅是新文學界的老資格,過去十年內曾執過文壇牛耳……”并認為“魯迅的小說創作并不多,《吶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時代到于今的收獲。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的中國文學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但在魯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去世后,蘇雪林對其態度突然大逆轉。1936年11月12日,蘇雪林拉開了她“半生‘反魯的序幕”。她寫了長達四千言的《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公開祭出反魯大旗,破口大罵魯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在文壇“興風作浪”,“含血噴人”,并影射、攻擊魯迅勾結日本特務機關內山書店,“行動詭秘”。還稱“魯迅病態心理將于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她還攻擊魯迅的雜文“文筆尖酸刻薄,無與倫比”,“含血噴人,無所不用其極”。1967年,蘇雪林將自己“反魯”的大部分文章結集出版《我論魯迅》。該書出版時,蘇雪林稱“半生的‘反魯事業,……以后我不高興再理會了”。
為何對魯迅態度前后不一,蘇雪林本人的解釋是,她看不慣魯迅對楊蔭榆女士的攻擊。楊蔭榆是蘇雪林在女高師就讀時的校長。1925年剛從法國歸來的蘇雪林為深陷女師大風潮漩渦中心的楊蔭榆講了一句“公道話”:“這場風潮的發生和進展時期里我恰不在女師大,雙方的是非曲直,不敢輕易評斷,但當時北平學風之過于囂張,學校秩序之凌雜混亂,都是事實。”蘇雪林認定自己因此而遭魯迅忌恨。再聯系1928年11月4日在北新書局宴會上魯迅對她“神情傲慢”,這些都讓生性敏感好強的蘇雪林自動站在魯迅對立面,與魯迅“立于敵對地位”。
蘇雪林性格倔強乃至偏執,她敢于挑戰權威,堅持己見,一意孤行,不為他人及社會輿論所動搖,顯然多有偏狹。她堅持半輩子反魯,也歸因于其個性。網名“絕色佳人”分析蘇雪林的反魯心理:“大家指責她,她會覺得自己是不被理解的英雄。大家不理她,她又會覺得自己是孤獨的英雄。”此說也有一定道理。
筆者還想補充一點,蘇雪林的半生反魯,恐怕與她的人生隱痛也有關系。蘇雪林與丈夫張寶齡因父母之命而結婚,其實兩人性格不合,雖未離婚,但他們真正的婚姻生活只維系了三四年。楊蔭榆早年奉祖母之命嫁了一個傻子丈夫,后來脫離夫家擺脫桎梏自我奮斗,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成為民國時期少有的女性教育家。楊蔭榆一直沒有再婚,一輩子不得意,性格也漸趨別扭,最終又為保護學生被日寇槍殺。楊蔭榆與蘇雪林人生境遇是否有著太多相似?而魯迅在女師大風潮中所寫《寡婦主義》一文中說:“在女子,是從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兒女,而后真的愛情才覺醒的;否則,便潛藏著,或者竟會萎落,甚且至于變態。”譏諷楊蔭榆管理學校施行的是“寡婦主義”或“擬寡婦主義”。蘇雪林與楊蔭榆同病相憐惺惺相惜,想必對魯迅施加的“寡婦”、“擬寡婦”標簽,尤為耿耿于懷深惡痛絕吧。
蘇雪林的“反魯”言論,用盡人身攻擊的一切詞匯,對魯迅極盡口誅筆伐和潑婦謾罵之能事,無論觀點、內容還是文風都刻薄之極,實在有違一個學者在學術探討、思想交鋒時應有的客觀理性。這是蘇雪林作為著名學者學術履歷上的醒目缺陷,無法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