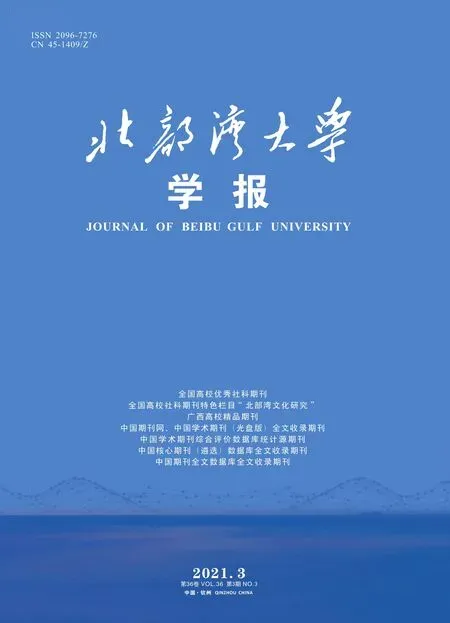南漢的禮儀與“非禮”
(香港中文大學(xué) 歷史系, 香港 沙田999077)
南漢國祚不長,且偏安嶺南,歷來不受史家重視。 作為不具正統(tǒng)性的十國之一,南漢的禮儀史記錄相較于五代及吳越等國更加簡陋。 從宋朝到當(dāng)代,南漢的歷史研究受史料記錄所限制。 作為第一手史料,南漢臣子胡賓王所著的《劉氏興亡錄》本應(yīng)是最直觀的文獻[1]71,可惜宋元后已亡佚。 作為節(jié)度使出身自立稱帝的劉氏,常不受史家待見。 薛居正將南漢列為“僭偽”[2]1799;歐陽修雖將南漢列為“世家”,但安排在“雜傳”和“考”之后[3]809。
史家在記載南漢史時通常將其視作十國史的一部分,如《九國志》《十國春秋》等。 直到晚清,學(xué)海堂的兩位學(xué)長梁廷枏、吳蘭修才以南漢為本位出發(fā),撰寫了《南漢書》《南漢紀》等。 而今人的研究,大多基于對古籍的考據(jù)以及南漢二陵的發(fā)掘。 陳欣的《南漢國史》專注于南漢的軍政制度,兼論當(dāng)時的佛教文化。 廣州文博系統(tǒng)的全洪、程存潔、張強祿等人基于對德陵、康陵的發(fā)掘情況撰寫了考古學(xué)報告。 其中,程存潔、張強祿等人有專文論述南漢的哀冊儀禮和陵寢制度。
而在禮儀史范疇內(nèi),史家多認為五代十國是“禮樂崩壞”的年代,無禮制可言。 的確,五代戰(zhàn)亂迭起,小朝廷重兵輕儒也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 后晉出帝石重貴曾道:“禮非我家事業(yè)也。”[2]1067歐陽修評價五代道:“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3]188但是,五代亂世還是有禮儀可言的[4]415。 這些小朝廷在主觀上都認為自己是正統(tǒng),相互之間亦以鄰國外交禮節(jié)相待。
史家有意避開五代十國禮儀史的另一原因是五代十國大多繼承唐制。 吳任臣在《十國春秋·十國百官表序》中提道:“十國官制,大略多仍唐舊,間有與《六典》異名者……南漢內(nèi)三師、內(nèi)三公,則又不足道者也。”[5]1639史家認為,十國離唐朝太近,而掌控十國政權(quán)的人又大多曾在唐朝任職,若想研究十國禮制、官制,大可在唐史中找到依據(jù)。
筆者認為,不受古代史家重視的南漢禮儀也應(yīng)該得到研究。 因此,筆者拋磚引玉,展開對南漢禮儀的探究。 尋找史料中殘存的南漢禮儀記錄,比較研究南漢的禮儀與不合禮儀的“非禮”事件,討論南漢“禮樂崩壞”的原因是本文的主題。
一、 南漢的禮官制度
五代十國離唐朝不遠,且眾多君主曾任職于唐朝。 因此,五代十國的官僚制度大多仿照唐制,各國也會根據(jù)自身的實際情況稍做增減。 吳任臣在《十國春秋·十國百官表序》中表達了自己對南漢“內(nèi)三師、內(nèi)三公”的厭惡情緒。 事實上,南漢的官制幾乎全盤照搬了唐代的制度,但是自南漢高祖劉執(zhí)政末期開始重用宦官后,宦官幾度成為南漢朝廷中最大的一股政治勢力。
《南漢紀》載:“高祖雖寵中官,其數(shù)裁三百余……至是(后主劉鋹時)漸至七千余,有為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nèi)字,諸使名不翅二百。”[6]66由此可見,至南漢后期,宦官甚至可以任職宰相,是否加綴“內(nèi)”字僅是其身份的區(qū)別符號。 宦官能夠形成如此大的勢力顯然不符合規(guī)制。 這是南漢在官制上的“非禮”表現(xiàn)之一。
拋開宦官掌權(quán)的南漢后期朝政來看整個南漢的官制,我們發(fā)現(xiàn),被史家唾棄為“禮樂崩壞”的十國中,其實亦有掌管禮儀的專職官員。 劉隱任靜海節(jié)度使時以禮賢下士而出名。 《南漢書》載:“烈宗折節(jié)下士,敬禮不少衰。”[1]47南漢設(shè)立禮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劉隱任靜海節(jié)度使時藩鎮(zhèn)內(nèi)的掌書記一職。 《資治通鑒》載:“(掌書記)掌朝覲、聘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長絀之事。”[7]6905由此可見,掌書記即藩鎮(zhèn)內(nèi)部的禮官,主要協(xié)助節(jié)度使解決藩鎮(zhèn)與朝廷及藩鎮(zhèn)內(nèi)部之間的禮儀祭祀事務(wù)。 擔(dān)任這一職務(wù)的是陳用拙,他在劉隱任靜海節(jié)度使時任掌書記并攝觀察判官[5]891,兼職禮儀和軍事,符合當(dāng)時藩鎮(zhèn)的實際需要。 此人“少嫻習(xí)禮樂,工為詩歌”[1]52,可謂不務(wù)正業(yè)。 但其在乾化四年(914 年)代表“大越”(南漢前身)出使吳越國,以不卑不亢的氣度完成了在吳越國的賓禮儀式,并獲武肅王賞賜大量金帛。
恢復(fù)科舉取士,為國家選舉人才本應(yīng)是禮部侍郎李殷衡的本職,但實際上,提出恢復(fù)科舉的官員是兵部侍郎楊洞潛。 乾亨四年(982 年)三月,楊洞潛上書請求開設(shè)學(xué)校與科考:“洞潛遂乘間陳吉兇禮法,請立學(xué)校,開貢舉,設(shè)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敘。”[5]889此后,南漢每年通過進士明經(jīng)科的考試選舉出十余人入朝。 兵部進行倡議,實際上是干涉了禮部的正常運作,雖然恢復(fù)科舉是有利之事,但也反映出南漢立國之初禮部運作的混亂情形。
除了禮部,主管南漢禮儀的還有太常寺,寺設(shè)太常卿主政。 在吳任臣編纂的《十國百官表》[5]1654與陳欣整理的《南漢中央官制表》[8]139中,均有南漢太常寺中只設(shè)太常卿的記錄,卻未有太常少卿一職的記載。 但在現(xiàn)存的南漢國史著作中,并沒有關(guān)于太常卿的詳細記載,以至于今人無法得知究竟有誰于何時擔(dān)任過南漢的太常卿。 與吳任臣、陳欣二人所制之表相補充的則是梁廷枏的《南漢書》,其中有載:“周杰……大有中,遷太常少卿。”[1]51由此可見,南漢太常寺是設(shè)置了太常卿、太常少卿等官職的較為完備的禮官部門。同時可以斷定,吳任臣和陳欣的官制表對南漢太常寺禮官的記錄存在遺漏。
至于太常寺在南漢朝廷起什么作用,史籍中并無過多描述,但可以從南漢臣列傳中互見。 根據(jù)唐制,太常寺應(yīng)當(dāng)主管郊祀、社稷和明堂禮儀。大寶二年(959 年),尚書右丞兼參政事鐘允章與宦官集團在圜丘祀禮的祭壇上起了沖突。 《南漢紀》載:“十一月,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shè)神位。”[6]64-65雖然吳蘭修并沒有提到鐘允章所率領(lǐng)的禮官究竟是來自禮部還是來自太常寺,但依據(jù)南漢沿襲唐朝禮官制度的習(xí)慣,可以推斷鐘允章率領(lǐng)的禮官來自太常寺。因此,太常寺卿、少卿等禮官的職能亦能夠明確。
關(guān)于管理皇室宗族事務(wù)的宗正寺卿,《十國春秋》有由劉濬兼任的記載:“高祖即位,拜宗正卿兼工部侍郎。”[5]890此外,并無其他關(guān)于南漢宗正寺卿的任何記錄。 據(jù)《五代會要》記載,后周的宗正寺是“見管齊郎室長……見管禮料庫收貯”[9]的宗族禮儀管理機構(gòu),此外還負責(zé)太廟等祭禮的準備工作。 我們有理由相信南漢宗正寺的職能應(yīng)當(dāng)與五代其他國家相差無幾。
南漢還設(shè)立了一個獨特的職務(wù)——崇文使。在其他朝代中,找不到設(shè)立同名官職的信息。 由此可見,南漢崇文使的設(shè)立既非繼承唐代,又非模仿同時期的其他國家,更沒有流傳到宋代。 通過對比《十國百官表》中各國相似的官職,筆者發(fā)現(xiàn),同時期的吳國禮儀使從屬于客省使這一條目,而南漢的客省使與崇文使在表中相鄰;后蜀的禮儀使與南漢的崇文使則被吳任臣放置在同一條目中。 由此可見,雖然史籍并沒有記載崇文使的具體職能,但通過對表格條目的分析,筆者認為,崇文使或多或少參與了有關(guān)禮儀的事務(wù)。 《南漢書·諸王公主列傳》印證了這一觀點:“(立儲)議已定,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 高祖以其事訪之。 益力言不可,乃止。”[1]38按官品論,崇文使的級別并不高,再往下就是三司、內(nèi)侍省和各州刺史、藩鎮(zhèn)。立儲之事,劉完全可以和宰相這一級別的官員商議。 筆者推測,崇文使蕭益之所以能夠介入南漢“立嫡長”還是“立賢”的討論中,一方面是因為其與劉的私人交情,另一方面是因為崇文使本身的禮儀職能。 崇文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著王國的禮儀事務(wù)。
經(jīng)過對南漢禮部、太常寺、宗正寺和崇文使的考據(jù)及分析,筆者發(fā)現(xiàn),南漢雖處“禮樂崩壞”的五代十國,但其仿照唐制建立了自身的禮官系統(tǒng)。這些禮官在南漢皇帝的郊祀、立儲等禮儀宗法事務(wù)上起到了重要的協(xié)助作用。 不過,在南漢禮官系統(tǒng)中也有其“非禮”的、不合章法的部分,例如楊洞潛作為兵部侍郎干涉禮部的工作、鐘允章在祭祀圜丘時與宦官許彥真起沖突等。
二、 南漢的祭祀禮儀
在南漢立國以前,劉氏藩鎮(zhèn)內(nèi)部已有專職禮官掌管禮儀事務(wù)。 除禮官之外,劉隱的賓客幕僚中還有一大批通曉禮經(jīng)禮義的中原人士。 這些中原人士是南漢的立國之本,也是南漢儒家的代表。例如宰相趙光裔、陳用拙、王定保、周杰等人皆晚唐進士出身,為劉氏藩鎮(zhèn)和南漢在與中央朝廷和各個國家之間的交往禮儀中作出了不少貢獻。 其中如趙光裔在主政時說服劉與馬楚通使,在主導(dǎo)兩國完成聘禮的同時解決了南漢多年來的“楚難”[5]887-888。
南漢立國之初,有這樣一個“非禮”事件:王定保作為唐朝進士,客居嶺南,一向支持劉歸順后梁、恪守節(jié)度使的本分。 劉作為晚唐、后梁兩朝人臣,本身已是“貳臣”的身份,若再僭越稱帝立國,更是不符合君臣之禮。 劉氏宗族一向敬畏中原人士的正統(tǒng)觀,但在帝王之位面前,正統(tǒng)的禮數(shù)顯然是劉的障礙。 由于敬畏王氏的威嚴,劉想稱帝只得調(diào)離王定保。 “越主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荊南。”[6]28“俟其出境,乃舉即位禮。”[1]51劉最終還是無視人臣的禮數(shù)即位稱帝。 但此次“非禮”事件還沒有結(jié)束,王定保返朝得知建國的消息后道:“立國當(dāng)有制度。 頃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是藩鎮(zhèn)之名號未除也。 藩鎮(zhèn)而稱制,四方不取笑乎?”[1]48也就是說,南漢立國本身就是不合禮數(shù)的僭越。 而立國之后,南漢也并不注重禮儀制度的更新,這是造成“非禮”事件發(fā)生的根本原因。
五代各國禮儀雖然大多繼承唐制,但也會根據(jù)各自的實際條件自行增減儀式的程序、器物。易言之,五代時期,尤其是南方諸國,其立國時間短且缺少通曉禮儀的學(xué)者,對禮儀的認知往往較為淺薄。 加上朝廷儀式大多與政治意義掛鉤,以及南方諸國統(tǒng)治者深信佛教、道教,王國禮儀通常被改革得十分功利且草率[10]11。 鐘允章在郊祀祭壇布置神位時與宦官集團發(fā)生沖突,許彥真用“潛有所禱”[6]65的罪名誣陷他。 后主劉鋹很快就以謀反的罪名將鐘允章和他的兩個兒子一并處死。 由此看來,雖然五代十國的禮儀在繼承唐制的基礎(chǔ)上有所增減,但是禮儀與政治統(tǒng)治之間的關(guān)系依舊十分牢固。 但凡牽扯到禮儀之事,以南漢為代表的各國統(tǒng)治者都非常敏感。
南漢皇帝十分重視郊祀和社稷禮。 首先是郊祀禮儀。 五代十國的統(tǒng)治者重視郊祀禮,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國帝王大部分出身于晚唐、后梁的藩鎮(zhèn),在主觀上他們建國稱帝均得不到正統(tǒng)性的支持。 正統(tǒng)性的缺席會給五代十國的統(tǒng)治者們帶來一種心理上的弱勢[10]12。 如何扭轉(zhuǎn)這種心理弱勢并在國家內(nèi)部建構(gòu)正統(tǒng)是南漢乃至五代十國的帝王必須正視的問題。 因此,郊祀祭天就成為五代十國的統(tǒng)治者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途徑。
關(guān)于郊祀的時間和對象,五代十國各國保持的傳統(tǒng)各有不同。 例如,吳國保持在孟夏行雩祀和冬至祭天[10]4;南唐傳承得更完備,保留了祈谷、雩祀、皇地祇和祭天禮[10]8。 吳國與南唐已經(jīng)是五代十國中保存郊祀非常完備的國家,其他國家包括南漢在內(nèi),大多數(shù)只保留了祭天之禮。 至于在唐代出現(xiàn)的極其重要的明堂禮,在五代十國時期都只存在于各國的禮制設(shè)想中而已。 在南漢的歷史中,皇帝在都城南郊共進行過三次祭天之禮,劉、劉晟和劉鋹各行一次。 劉在開國的第二年祭天:“冬十一月,帝祀天南郊,大赦。”[1]7劉晟以弒兄上位,為建構(gòu)其篡位的正統(tǒng)性他在即位后的第一年就舉行祭天儀式:“十一月丁亥,帝祀天南郊,大赦。”[1]16劉鋹在安葬好劉晟后的第二年也舉行了祭天儀式: “辛亥, 祀天南郊,大赦。”[1]22
在史籍的寥寥數(shù)語中,我們可以確定南漢的祭天禮儀嚴格遵循了《開元禮》中對祭祀時間的要求。 三次祭天的時間都是在冬天十一月,且有極大可能都是在冬至這一天。 關(guān)于祭祀的對象,史書中并沒有提到相關(guān)信息。 筆者推測,南漢祭天的對象是昊天上帝。 但南漢是否繼承了唐代從祀五方帝的傳統(tǒng),這應(yīng)當(dāng)存疑。 王光華認為,南方諸國冬至祭天,大多主祀昊天上帝,而極少從祀五方帝。 例如,前蜀高祖王建就將五方帝與昊天上帝分開祭祀:“夏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翼日,祀地祇于方丘。”[5]525南漢極有可能與南方諸國一道,將祭天的對象限定為昊天上帝。
南漢祭壇所在的位置即皇城所在地——興王府的南郊。 宋人方信孺在游歷廣州時曾賦詩:“一德由來可享天,東鄰牛祭亦徒然。 荒涼到處游麋鹿,誰識郊壇八面圓。”[11]可以推測,南漢祭壇的位置處于宋代廣州城南的一個十分荒蕪的地區(qū)。 廣州考古所在挖掘南漢二陵時曾誤認為南漢祭壇位于廣州小谷圍島。 而《南漢國史》則推測南漢郊壇在河南地區(qū),即珠江以南的隔山鄉(xiāng)[8]281。其中,小谷圍遺址已經(jīng)被確定是劉的康陵,而“隔山鄉(xiāng)說”也沒有過多的證據(jù)。 根據(jù)南漢廣州地圖分析,當(dāng)時珠江的北岸大致在今天的文明路稍南。[12]而珠江的南岸大致為今曉港公園稍北一帶。 從南漢新南城到隔山鄉(xiāng)的江面距離超過三公里,不過隔山鄉(xiāng)位于南漢皇城中軸線的正南方。筆者認為“隔山鄉(xiāng)說”有一定的道理。 迫于南漢時廣州繁雜的水文地理以及禮制上的苛刻要求,南漢帝王將祭壇設(shè)置在珠江以南的地區(qū)也并非不可能。
除祭天禮外,南漢還是南方諸國中唯一保存籍田禮的國家[10]12。 “(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籍田之禮。”[2]1808“(乾和) 十二年,晟親耕籍田。”[3]816根據(jù)梁廷枏的考證,劉和劉晟的兩次籍田禮都是在春季正月舉行的。 《禮記·月令》載:“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13]由此可見,南漢的籍田禮依舊是遵照傳統(tǒng)的時間點而舉行的禮儀。 值得一提的是,薛居正等人在史書中說明,南漢帝王是僭越行天子之禮。 劉和劉晟都是僭越即位的帝王,一個是節(jié)度使稱帝,另一個是弒兄稱帝。 他們在執(zhí)政中期選擇舉行籍田禮,一方面是為了彰顯農(nóng)業(yè)在南漢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強調(diào)自己在國家中的政治地位,至少強調(diào)了在南漢朝廷內(nèi)部建立臣民的正統(tǒng)觀。 這也從側(cè)面體現(xiàn)出南漢在禮儀方面尤其是在天子禮儀方面為建構(gòu)政治正統(tǒng)性而做出的努力。
綜上,通過對南漢祭禮史料的分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南漢在禮儀儀式中所要表達的政治內(nèi)涵頗多。 作為一個并無執(zhí)政正統(tǒng)的僭越政權(quán),從劉到劉鋹,四代帝王都在努力地通過郊祀、籍田等儀式建構(gòu)自身的正統(tǒng)。 雖然在開國之初劉為了盡早稱帝鬧出了一些“非禮”事件,但至少南漢自始至終都恪守著相關(guān)禮儀的儀節(jié)要求,比如祭壇的位置、祭祀的時間、祭祀的對象等。
三、 南漢的宗法與神祇
五代十國出現(xiàn)過多次弒父、弒兄的篡位現(xiàn)象。從這個角度看,五代被稱作“賊亂之世”理所當(dāng)然。 但是,弒父、弒兄的本質(zhì)是封建王朝各國王室內(nèi)部的政治斗爭,如果因此就下定論說五代是一個不講宗法禮制的時代則有片面性。 從客觀情況看,在封建王朝里五代十國的宗法禮制保存得還算完備,只因各國的實際情況和戰(zhàn)亂程度稍打折扣,而就宗法傳承角度而言,五代比十國傳承得更好。
該時期,各國在建國之初就建立宗廟以維護王室宗法,并以此顯示自己立國的正統(tǒng)性。 后晉就曾在立國后因為宗廟問題引發(fā)了朝廷的爭論。天福二年(937 年),段颙上書晉廷請立宗廟,認為:“今臣等參詳,唯立七廟,即并通其禮。”[2]1898而劉昫、張昭運等人反對立七廟,認為:“況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約舊章……追尊四廟為定。”[2]1902簡言之就是,段颙主張立七廟以顯示后晉王室的功德,而劉昀、張昭運則主張仿照隋唐慣例先立四廟。 四廟之制在五代頗為盛行,后周在廣順元年(951 年)亦建立四廟:“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會使奉冊四廟。”[2]1904后晉、后周都是依照唐朝慣例先立四廟的典范,而后唐則在明宗時建立了七廟制度,薛居正記有:“盛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2]1909后唐立七廟是因為明宗認為此時的后唐已經(jīng)達到中興,可以仿照唐制擴展宗廟的規(guī)格。
但南方諸國并沒有五代那么長的血脈傳承。包括吳國、閩國和南漢在內(nèi)的南方國家都很難湊夠四廟或五廟的形制。 劉在建國伊始就建立了宗廟制度,《資治通鑒》有記載:“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7]8817由于劉氏家族在劉安仁以前并不見經(jīng)傳,劉立宗廟也只能夠立三廟,無法仿照唐朝和五代中央朝廷建立四廟或七廟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被篡位的殤帝劉玢和被宋朝招安的后主劉鋹這兩個無法入祀宗廟的皇帝之外,南漢在被滅國之前也只是剛好湊夠五廟而已。 至于南漢的禘袷祭祀史料,因均已失傳,筆者不好多作推測。
關(guān)于南漢宗廟的位置,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唐朝長安皇城與太廟的相對位置進行推測。 唐朝的太廟位于皇城的東南部、太常寺的東邊。 南漢時,興王府城東有東濠,北有城北濠池,西有藥洲園林,南臨珠江北岸[12]。 南漢都城彼時建立在禺山一帶。 這個不到0.5 平方公里的興王府城被人為地切割為北中南三個部分,北部是紫禁城,中部是皇城,南部是新南城。 按照南漢帝王從劉開始大興土木建設(shè)宮殿群的奢靡傳統(tǒng),興王府城中應(yīng)當(dāng)只有較少的民居,且集中在新南城的南部。 學(xué)者全洪曾說過,南漢宮殿出土的柱基、鴟吻的形制大多類比唐長安,有的規(guī)格甚至超過了長安(1)全洪老師的說法,出自廣州大學(xué)某學(xué)生課題組的一次視頻采訪:解密南漢國[EB/OL]. https:/ /www. bilibili. com/video/av52312464/? from=search&seid=5927388088055406249,2019-05-13.。可以推斷,南漢的宗廟可能與長安城的宗廟相對位置相似,大概在當(dāng)時禺山以東的地區(qū),即今廣州文德路以東一帶。
除了延續(xù)宗廟制度外,南漢的立儲也恪守著嚴格的宗法制度。 在劉氏宗族內(nèi)部,共有三次父子相傳和一次兄終弟及的繼承方式。 劉謙是封州刺史,聚集了眾多幕僚和士兵,死后將官職傳給了長子劉隱;劉隱在去世前將清海軍藩鎮(zhèn)傳給了弟弟劉;劉稱帝傳位給了嫡長子劉玢;劉晟弒兄篡位,后傳位給了長子劉鋹。 可以說,南漢朝廷除了劉晟篡位不合禮法外,其他時候均恪守著“立嫡立長”的宗法制度。 關(guān)于立儲事宜,在劉執(zhí)政末期曾有這么一次宗法討論,當(dāng)時,劉最出色的九子萬王劉洪操已在交州戰(zhàn)中陣亡,而最有才能繼位的應(yīng)是五子越王劉洪昌。 劉亦想立洪昌為太子,《南漢書》有載:“惟洪昌類我,意欲立之。”[1]38右仆射王翷甚至已經(jīng)制定好將秦王、晉王遷出都城協(xié)助劉立儲的計劃。 但崇文使蕭益卻以宗法制度為由極力勸阻,這方面《南漢書》也有記載:“立嫡以長,古今通制。 違之而立少者,則長者必爭。”[1]63因為劉的長子、二子均早夭,若蕭益的嫡長子繼承建議成行,最大的受益者是三子秦王劉洪度。 劉順從了傳位嫡長子的建議,將劉洪度立為太子。 但劉洪度“性庸昧且荒淫”[1]15,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晉王劉洪熙所殺。 盧膺在《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中道:“法成周而垂范,稽世祖而作則,構(gòu)大業(yè)而云忠,偃巨室內(nèi)而不惑。 嗣主仁孝,僶俛祚階,抑情登位,感結(jié)疚懷。”[14]這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恭維,也是南漢帝王恪守宗法禮儀而缺失政治考量的體現(xiàn)。
中宗劉晟(即劉洪熙)在篡位后的數(shù)年里將十三個親兄弟殘殺殆盡。 劉晟沒有盡到一個大宗統(tǒng)領(lǐng)各小宗的宗法義務(wù),反而制造出極其不合禮法的宗族事件。 《南漢紀》載:“(乾和五年)九月,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洪弼、貴王洪道……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后宮。”[6]55劉晟將弟弟們滅殺殆盡,而將所有弟妹納入自己的后宮,這種亂倫的行為叫作“收繼婚”。 雖然在春秋時期,中原曾出現(xiàn)過這種婚姻制度,但《左傳》中將這種僭越禮法的婚姻稱作“烝”,被視為不正當(dāng)?shù)男袨閇15]。 因此劉晟的這種行為亦是不合禮法的“非禮”丑聞。
除宗法制度外,南漢亦通過加封境內(nèi)山川神祇來統(tǒng)一地方和朝廷的信仰觀念。 《南漢書》記載:“乾亨元年秋八月癸巳……置五岳,皆建行宮。”[1]7劉在登基當(dāng)天就仿照南詔在國境之內(nèi)設(shè)置五岳,以顯示自己是一個獨立的政權(quán)。 劉鋹執(zhí)政時,南海縣(今廣東廣州市)一女子生下一個“兩首四臂”[6]75的嬰孩。 劉鋹認為是南海神顯靈,又封南海神為昭明帝。 南漢敕封的地方神祇并不少,但從南漢帝王崇尚佛風(fēng)的宗教追求來看,地方神遠遠不如佛寺的地位。 筆者基于吳蘭修的考證[6]26-27,補入?yún)侨纬肌⒘和彽恼f法,制作了《南漢敕封神祇表》,具體見表1。

表1 南漢敕封神祇表_
南漢帝王皆信仰佛教,尤其是后主劉鋹,更是在興王府四周仿照二十八星宿修筑了二十八寺,又在羅浮山上修建天華宮、黃龍洞等。 在帝王的推廣下,南漢一度重現(xiàn)“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壯觀景象。 相比之下,地方神祇的敕封與先前提到的祭天儀式則遜色了許多。 可以肯定的是,在南漢后期,代表正統(tǒng)禮儀的儒家遠遠落后于宦官集團與佛僧方士。 綜合來看,南漢雖然恪守宗法立儲傳位、遵循正統(tǒng)敕封地祇,但這是南漢帝王礙于開國中原進士集團的面子而作出的讓步。 高祖、中宗殘暴無禮,殤帝荒淫無度,后主崇尚佛教,以上種種,都說明了南漢作為“禮樂崩壞”的五代十國的一員,無法避開“非禮”的時弊。
結(jié)論
南漢歷經(jīng)四主,只有短短五十多年的歷史,且所處的是“禮樂崩壞”的五代十國時期。 就南漢禮制本身而言,由于受正統(tǒng)觀的影響,史家大多不愿詳述,多以僭越之名一筆帶過。 與此同時,本身就稀少的南漢禮儀史的相關(guān)記錄大多散佚,我們只能在十國軍政史中搜尋殘存的史料進行研究與推測。
總體而言,南漢前期勵精圖治,憑借富饒的嶺南區(qū)位優(yōu)勢和被迫南遷的中原進士集團勉強維持王國的穩(wěn)定,并在國內(nèi)通過祭天禮、籍田禮、宗廟禮和敕封地方神等手段構(gòu)建自己在國境內(nèi)的正統(tǒng)性,扭轉(zhuǎn)宗室僭越稱帝的心理弱勢。 由此可見,南漢禮儀本身具有極強的政治意蘊,皇帝對禮儀的施行十分重視且敏感。 簡言之,南漢前期的國家禮制具有三個特點:第一,以中原人士為禮儀基礎(chǔ),如趙光裔、王定保等中原進士集團成員是南漢禮儀的主導(dǎo)者;第二,藩鎮(zhèn)特征并未褪盡,禮儀官制混亂,有兵部干涉禮儀事務(wù)的先例;第三,南漢禮儀活動中常因帝王的主觀意愿而造成“非禮”事件,如劉晟的“收繼婚”亂倫行為等。
到后主劉鋹執(zhí)政時,因佛僧方士和宦官集團開始替代傳統(tǒng)儒家士人在南漢小朝廷中的統(tǒng)治地位,造成南漢禮儀在歷代史家筆下多以“荒淫怪誕”“光怪陸離”而著稱。 而真實的南漢禮儀制度并沒有史書上所言的那般吊詭。
首先,南漢在禮官制度上主要繼承了唐朝的制度,禮部、太常寺、宗正寺等機構(gòu)共同形成南漢的官方禮儀系統(tǒng),負責(zé)南漢祭天、籍田、敕封等國家禮儀儀式的籌備。 另外,南漢獨創(chuàng)“崇文使”一職,這個官職也應(yīng)牽涉到南漢宗室禮儀的一些領(lǐng)域。
其次,南漢多次舉行郊祀禮、籍田禮,并建設(shè)了許多禮儀建筑,例如,這些建筑有部分可能位于珠江以南的天壇、禺山以東的太廟以及近年來發(fā)掘的康陵、德陵等南漢帝王陵墓。 南漢的禮儀與政治的關(guān)系十分密切,是在國家內(nèi)部扭轉(zhuǎn)正統(tǒng)性責(zé)難時所采取的一些應(yīng)對措施。
再次,南漢宗室還恪守著“傳嫡以長”的宗法思想。 雖然中宗的篡位和殤帝、后主的行為導(dǎo)致南漢宗室立嫡長的決定多次失敗,但我們依舊能夠從中感受到南漢十分傳統(tǒng)的宗法觀念。
此外,南漢還通過敕封地方神祇來加強各地對南漢的“國家—鄉(xiāng)土”的認同。 這在崇尚佛法的南漢,應(yīng)是一次意識形態(tài)上對鄉(xiāng)土儀禮和儒家學(xué)說的跨越與讓步。
不得不承認,薛居正、歐陽修筆下的那個“五代十國”確實是“光怪陸離”“禮樂崩壞”的年代,但研究五代十國禮儀史并不能因一家之言就認定這個時期毫無禮儀可言。 同時,我們也不能因為發(fā)現(xiàn)了南漢在國家禮儀制度、儀式上曾經(jīng)遵循禮法的約束,就否認諸多“非禮”事件的發(fā)生。 禮儀與政治一直是南漢政權(quán)正統(tǒng)性的寄托,但因為帝王自身的素質(zhì)而遭到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