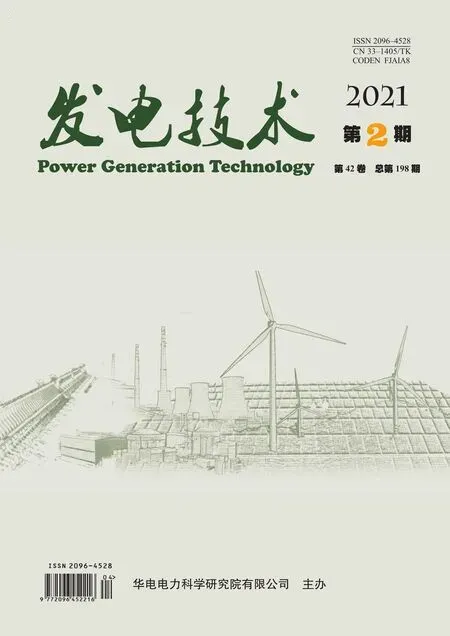鋰離子電池結合棋盤拓撲分流結構的浸沒冷卻熱管理研究
劉倩,石千磊,李凱璇,徐超,廖志榮,巨星
(電站能量傳遞轉化與系統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華北電力大學),北京市 昌平區 102206)
0 引言
鋰離子電池由于具有比能量高、質量小、體積小、循環壽命長和自放電率低[1-3]等優點而成為電動汽車研究和發展道路上的關注重點。在鋰電池運行過程中,除了正常的充放電反應外,還有大量隨之而來的副反應,一旦電池溫度過高或者充電電壓過高,副反應極易被引發[4]。如果此時電池內產生的熱量沒有得到及時疏散,極易引起電池內部溫度和壓力的急劇上升,最終使得電池進入一個無法調控的正反饋自加溫狀態,即熱失控狀態[5-6]。鋰離子電池適宜的工作溫度范圍為25~40 ℃[7-9],只要超出該范圍,就會導致電池容量下降、放電效率降低、充放電循環壽命縮短等不良后果[8],這些都將直接影響電動汽車的動力性、經濟性和安全性[5,10]。所以,電動汽車電池的熱管理成為解決電動汽車安全性問題的難點。
電動汽車電池熱管理的核心是對電池內部傳熱效果的控制,主要有3個目的[4,11]:1)溫度過高時電池組能盡快地散熱,保證其安全性;2)電池組在低溫環境能夠快速加熱,保證在該條件下的充放電效率;3)由于電池間溫差過大會使電池的性能下降、安全性降低,所以需要通過設計保證電池溫度的均勻性。此外,電池組本身的熱管理設計應考慮與電動汽車熱能綜合管理利用相協調,以實現效益最大化[12]。針對低溫加熱問題,熱管理系統通常采用高壓正溫度系數(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PTC)加熱等方式解決[13],而在高溫和溫度均勻性控制方面,目前動力電池主要采用空冷式、液冷式和相變材料(phase change material,PCM)冷卻方式實現[5,10,14]。
18650電池是目前最成熟穩定的鋰離子電池,其一致性和安全性都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在18650鋰離子電池的冷卻方面,由于圓柱型電池自身的空間分布特征,研究者也采用了多種冷卻方式以達到更好的溫控效果。在常用的3種冷卻方式中,空冷式結構簡單、成本低,但由于空氣熱容和導熱系數低,導致該方式下的冷卻能力十分有限[12,15-16]。液冷式的液體熱容和導熱系數較高,冷卻效果較好,散熱也比較均勻[8,17],冷卻結構較為緊湊,但在運行中容易發生冷卻液泄漏。PCM冷卻對于相變材料的要求較高,即使有保溫蓄熱的優點,也需要結合其他冷卻方式以達到電池熱管理的目的,這將使得設計結構復雜且成本大大提高[18-21]。隨著電池能量密度的不斷提高,電池冷卻需求越來越大,目前主流的冷卻方式是液冷。
圓柱型鋰離子電池的液冷研究大都集中于微通道冷板和扁平微管,大多采用全表面或大表面研究。有研究[22-25]發現,冷卻板上液冷流道數目和冷卻液入口速度對電池溫升情況有很大的影響。通過對常規的冷板結構進行改進,發現同向流道比異向流道的冷卻效果更好[26]。作為電動汽車領域先進技術代表的特斯拉,通過蛇形扁平微管對圓柱型鋰離子電池組進行液體冷卻,但扁平微管與電池的接觸面積十分有限[27]。在此基礎上Zhao等[28]研究發現,改變蛇形冷卻板與電池圓心的夾角可以增加冷卻液流動路徑上的接觸面積,大大改善電池組的溫度均勻性。為使電池組的性能得到更大的改善,特斯拉提出一種采用冷卻板和熱管相結合的堆疊式組合冷卻方式以滿足熱管理的需求[29]。對于電池組冷卻,有研究[15,22,30]發現,將微通道引入電池陣列中能夠有效強化換熱,為了防止冷卻液對電池的腐蝕,常常采用導熱元件或者熱管作為中間結構[31-33]將熱量導出,使冷卻液將熱量帶出電池組。Wei等[34]研究表明,柔性微通道冷板能夠較好地貼合圓柱型電池的外表面,增大冷卻面積,從而改善換熱效果。通過大量對比實驗可知,PCM和液冷相結合的方式能大大改善電池熱管理系統的性能,在滿足電池運行溫度要求的同時起到保溫蓄熱的作用[35]。在該結論的基礎上,大量關于 PCM 和液冷結合的結構被提出,研究發現,改善PCM材料的導熱性能[36]、優化 PCM 材料的包覆結構[37]、外加導熱元件[21]及優化冷卻液流道設計[38]是這一技術的關鍵。此外,對于圓柱形電池布局與液冷效果的研究[39]表明,電池交錯排布比線性排布的冷卻效果更好,具有更好的溫度均勻性。與此同時,隨著電池間距離的增大,電池組內最高溫度和溫差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降低[40]。
雖然液冷式具有較高的換熱系數和易于排布安裝等優點,但是目前的研究中多采用傳統電子器件的散熱方式,通過流道將冷卻工質分配于冷板,將冷板作為換熱的核心部件,增加了電池換熱的熱阻。而基于浸沒的冷卻方式又缺乏對工質流動的設計,較難實現冷卻工質的均勻分配。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種基于棋盤拓撲歧管分流的浸沒式強制對流冷卻方式,用于圓柱形鋰離子電池的冷卻。
1 棋盤拓撲的歧管分流浸沒冷卻結構設計
之前相關工作中所提出的棋盤拓撲歧管分流結構與微針翅相結合的冷卻研究[41]表明:通過簡單的設計,該結構可以實現冷卻劑在針翅間的網狀流動換熱。這為圓柱形鋰離子電池陣列的浸沒冷卻設計提供了新的思路。將電池浸沒冷卻與棋盤拓撲歧管分流結構相結合,可實現冷卻劑在電池間的均勻流動,減少局部熱負荷以及溫度過高的可能性。如圖1所示,電池陣列冷卻結構的設計主要由6部分組成,自上而下依次為:蓋板和入口歧管層、陽極絕緣/棋盤孔口層、電池陣列區、浸沒冷卻區、陰極絕緣/棋盤孔口層、底板和出口歧管層。

圖1 電池陣列冷卻的分層設計圖Fig. 1 Layered diagram of cooling appearance of battery array
通過結合該歧管分流結構與鋰離子電池浸沒冷卻設計,可實現冷卻液在18650電池陣列內的流動,如圖2所示。該冷卻設計的平面圖顯示了電池內部冷卻液的流動模式,對浸沒層而言,其頂部陽極絕緣/棋盤孔口層的每一個入口圓孔均對應著浸沒層底部陰極絕緣/棋盤孔口層的 4個出口圓孔,反之亦然。這樣的出入口設置既對流動進行了分配,又可以增強擾動,加強換熱效果,達到降低電池在運行時最高溫度的目的。與此同時,該設計使得在電池間冷卻液的流動較為均勻,極大程度上改善了電池內部溫度分布不均勻的情況。電池模塊360°環形面接觸冷卻液,這樣的構型使得換熱面積顯著增大,從而進一步改善了電池熱管理的效果。

圖2 冷卻流道平面示意圖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oling channel

圖3 電池陣列網格狀冷卻流道三維示意圖Fig. 3 Three-dimensional diagram of grid cooling channel of battery array
這樣的出入口布置使得冷卻液在電池陣列內部形成了三維的網格狀流動,如圖3所示。可以明顯看出,該結構設計具有顯著的流動分配優勢,使得電池間冷卻液的流動較為均勻,減少浸沒冷卻中局部熱負荷過高的問題。同時,各層結構簡單,整個冷卻系統更加易于加工制造,電池冷卻結構各層的設計尺寸如表1所示。目前,主要的動力電池包密封件主要分為膠黏劑類、實體橡膠密封件類和發泡橡膠類3類[42]。其中以特斯拉為代表的車企采用膠黏劑類密封,將動力電池蓋板徹底封堵,可靠性提高,但不利于后期動力電池包的維護;國內的車企多用可拆卸的實體橡膠密封件類和發泡橡膠類產品。本文中電池包的上下蓋板是通過相關接插件、接觸的橡膠密封圈和密封膠來實現密封。

表1 電池冷卻結構各層的設計尺寸Tab. 1 Design dimensions for each layer of battery cooling structure
2 鋰離子電池冷卻模擬的物理模型
基于上述結構設計,本文對鋰離子電池冷卻過程進行數值模擬,驗證有關設計的冷卻效果并分析冷卻系統主要參數變化對鋰離子電池工作性能的影響。
2.1 鋰離子電池的生熱速率模型
目前,關于電池的理論計算最常用的方法是Bernadi等提出的電池生熱速率模型[8]。根據能量守恒原理,假設電池內部有穩定的熱源并且均勻產熱,對模型簡化之后,認為電池內部的熱量主要來自于焦耳熱,即歐姆內阻熱和電化學反應熱2部分。生熱速率Qgen的計算式為

式中:I為電流;Eoc為開路電壓;U為電池單體的工作電壓;T為電池的溫度。
在 Bernadi等提出的電池生熱速率模型的基礎上, Drake等[43]通過實驗的方法研究了在不同放電倍率情況下鋰離子電池的生熱速率。結果表明:當所選用的18650電池的放電倍率從1 C增至10 C時,其體積生熱率從0.097 07 W/cm3增加到0.6 W/cm3,相對應的生熱量從1.65 W增加到10 W。
根據以上研究成果,在本文的數值模型分析過程中,分別采用4、6、8、10 W的穩定熱源進行模擬[44],計算得到相對應的電池體積生熱率與放電倍率的關系如表2所示。高放電倍率屬于電動汽車運行過程中確實會存在的極端工況,研究在極端工況下冷卻結構對溫度的控制,能夠更全面地評估熱管理冷卻結構的性能,同時能夠對熱失控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表2 體積生熱率與放電倍率關系Tab. 2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me heat generation rate and discharge rate
2.2 鋰離子電池的傳熱特性
對電池而言,傳熱特性要從內部和外部2個方面進行分析。在電池內部,充放電過程中的確存在電解質溶液的流動,但是這種流動特別微弱,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幾乎不考慮電池內部的熱對流;同時熱輻射的作用也極其微弱,同樣不予以考慮。因此,在電池內部的傳熱方式主要以熱傳導為主。
熱傳導的表達式為

式中:λ為導熱系數;?T/?n為法向溫度梯度。
對電池外部而言,熱量通過熱傳導傳至電池殼體壁面,外部的冷卻流體與固體壁面相接觸,發生對流換熱,雖然存在一定的熱輻射,但是較為微弱,所以主要以熱對流為主,其表達式為

式中:h為電池的表面換熱系數;S為換熱面積;Tw為壁面溫度;Tf為流體溫度。
3 鋰離子電池熱管理系統的數值模型
在所設計的冷卻結構下,基于幾何構造和流動換熱過程的對稱特征,本文分別考察2種簡化計算模型的效果并進行比對,以確定模型選取對數值計算結果的影響,并利用簡化模型分析冷卻液進出口位置對電池熱管理的影響。
3.1 模型結構
選取與所設計的新型冷卻結構相符合的2種數值模型作為研究對象,分別是單體電池模型(圖4)和由20個單體電池組成的電池模組模型(圖5)。基于對稱特性,在單體電池模型中按射流孔進出口流動,選擇1/4電池及冷卻區域作為計算單元;在電池組模型中按歧管進出口流動,選取 20個1/2電池的交錯陣列作為計算單元。

圖4 單體電池模型Fig.4 Single battery model

圖5 電池模組模型Fig. 5 Battery module model
數值模型主要由鋰離子電池、冷卻液流道以及上下2個絕緣層4部分組成。其中,用于模擬的18650電池模型主體部分由鋁組成,基于實驗結果,采用一個直徑6 mm、高42 mm的圓柱體來模擬電池在工作過程中的電發熱中心。上下 2個絕緣層厚度都為1 mm,液體流動出入口為半徑4 mm的小孔。選用去離子水作為冷卻流體。在數值模擬過程中,冷卻水和各部分材料的相關參數如表 3所示[33]。本文所選用的電池簡化生熱模型與文獻[45]中所選用的電池生熱模型在 5 C放電倍率下,720 s時電池表面的溫度都呈現梯級分布,如圖6所示,且電池上端溫度高,下端溫度低,表面最高溫度的誤差為0.848%;文獻[46]中也指出,18650電池表面的溫度呈現梯級分布。

表3 各部分材料的物性參數Tab. 3 Physical parameters of each part material
在本研究采用的棋盤拓撲浸沒式液冷電池模塊中,電池外包覆高導熱絕緣硅膠膜,在模擬計算過程中,該結構可以忽略不計,但在實際應用中可以起到防止冷卻液對電池腐蝕的作用。
目前用于電池液冷研究的冷卻劑有去離子水、水/乙二醇的混合物、硅油和丙烷等,近來也有研究發現將納米流體和液態金屬作為冷卻劑能夠達到更好的冷卻效果。本文中采用去離子水進行液冷研究,了解該結構下的冷卻性能,且進行相關結構優化。在后續的工作中,考慮在優化后的結構中選用安全性更高的冷卻劑進行實驗和模擬計算。

圖6 5 C放電倍率下電池的表面溫度分布Fig. 6 Surfac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battery at 5 C discharge rate
3.2 數值計算模型
3.2.1 控制方程
電池組部分的能量守恒方程被描述成以下形式:

式中:ρb為電池的密度;cpb為電池的比熱容;τ為時間;λb為電池的導熱系數。
熱源項的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Vb為電池的體積。
對于在冷卻通道中流動的去離子水,控制方程包括連續性方程、動量守恒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具體表達式分別如下:

式中:ρw為水的密度;cpw為水的比熱容;λw為水的導熱系數;Ts為水的溫度;為水的速度矢量;p為壓力。
3.2.2 邊界條件
對于以上2個模型,流體入口設置為速度入口,速度為 0.02 m/s,同時設置入口水的溫度為25 ℃。流體出口設置為壓力出口。上下2個絕緣層外表面設置為絕熱壁面。其余的外表面均設置為對稱邊界條件。電池和流體域的固液接觸面設置為interface-coupled,電池的壁面設置為無滑移壁面。
3.2.3 數值計算方法
選用三維單精度瞬態模型,用ANSYS fluent 19.3軟件完成數值計算。在計算中激活能量方程,采用層流模型和SIMPLE計算方法,針對所有的守恒方程選用二階迎風格式。對于連續性方程和動量守恒方程,殘差精度選擇1×10-3;對于能量守恒方程,殘差精度選擇1×10-6。
3.3 數值模型驗證
分別選用時間步長0.1 s和0.2 s對模型進行研究。選擇該模型在電池生熱量為6 W時各個時刻的最高溫度作為衡量標準,研究時間步長的無關性,結果如圖7所示,不同時間步長下各時刻對應的最高溫度如表4所示。

圖7 時間步長與各時刻最高溫度的關系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steps and maximum temperature

表4 不同時間步長下各時刻對應的最高溫度Tab. 4 Maximum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time steps ℃
由圖7可以看出,在時間步長為0.1 s和0.2 s時,模型在各時刻的最大溫度偏差均小于0.01%,因此本文采用0.2 s作為模擬的時間步長。
網格獨立性試驗是為了最大程度上保證模擬計算的精度并減少計算機的工作時間。選取該模型中的平均溫度和最高溫度作為參考指標,進行計算模型的網格無關性校驗,結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從網格2的數目減少到網格1的數目時,平均溫度的偏差為 1.55%,最高溫度的偏差為1.78%;從網格2的數目增加到網格3的數目時,平均溫度的偏差為 1.59%,最高溫度的偏差為1.86%。由此,選擇網格2作為單體模型的網格進行fluent模擬計算,以適應計算的要求,保證結果的精確性。

表5 計算模型的網格無關性校驗Tab. 5 Verification of mesh independence of computational model
4 結果與討論
4.1 電池單體模型與模組模型的比較
電池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的邊界條件及電池發熱中心的體積生熱率相同,僅考慮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結構對冷卻效果的影響。在電池生熱量為6 W時,電池運行1 600 s過程中單體模型、模組模型流體的跡線圖如圖8所示。可以看出,冷卻液從入口進入冷卻區,形成射流沖擊電池表面,由于出入口的排布,冷卻液在靠近入口且位于電池中下部的位置形成渦,在渦的位置冷卻液的流速較小。在冷卻區的底部,大部分流線沿著電池切向分布,靠近出入口部分流線沿著電池軸向分布。該工況下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的溫度分布情況如圖9所示。可以看出,對于單體模型,入口溫度為 25 ℃,經過 1 600 s后,出口溫度為29.367 ℃,冷卻液溫升為 4.367 ℃;而模組模型在入口溫度同為25 ℃且經過相同時間后,冷卻液出口溫度為29.6 ℃,溫升為4.6 ℃。
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冷卻液溫度隨時間變化情況如圖10所示。電池生熱量分別為6 W和8 W時,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在模擬過程中各個時刻的最高溫度如圖11所示。可以看出,在不同電池生熱量的情況下,電池單體和模組模型得到的溫升趨勢基本一致,且模擬結束后兩者之間溫度偏差均小于2 ℃。因此,可以用單體模型代替模組模型來研究該冷卻結構的熱性能,以減少計算工作量。

圖8 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流體的跡線圖Fig. 8 Streamline diagram of single model and module model

圖9 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溫度分布情況Fig. 9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single model and module model

圖10 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冷卻液溫度隨時間變化情況Fig. 10 Coolant temperature change with time in single model and module model

圖11 單體模型與模組模型不同工況下的最高溫度Fig. 11 Maximum temperature of single model and module model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4.2 單體模型的熱特性
對單體模型進行瞬態模擬,邊界條件與之前采用的設置相同,電池生熱量為6 W,時間步長為0.2 s,共9 000步,持續加熱時間30 min。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時刻模型內部的溫度分布情況如圖12所示。

圖12 不同時刻異側出入口布置模型的溫度分布云圖Fig. 12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ontours of different-side inlet and oulet layout model at different time
圖12表示在瞬態模擬過程中,隨著電池生熱時間的增加,該模型內部溫度分布的變化情況。在剛開始的40 s內溫升達到5 ℃;200 s內溫升達到10 ℃;加熱到800 s時,基本達到穩態;隨后溫度變化幅度很小,其值小于 0.26%,可基本認為溫度保持不變。在該工況下模擬結束時,模型的總溫升為 14.23 ℃,電池內部最高溫度小于45 ℃,處于可以安全工作的溫度范圍。
以電池的軸線為旋轉中心,θ為旋轉角,求得沿電池周向角度的對流換熱系數如圖13所示。由圖13可知,電池周向對流換熱系數呈現周期變化,這與對稱結構有關。在由入口到出口的區域(即θ=0°~90°區域),對流換熱系數整體上呈現遞增的趨勢;反之,整體呈現遞減的趨勢。其中在θ分別為 45°、135°、225°和 315°時,由于流動過程中渦的形成,對流換熱系數在此區域附近存在極小值。

圖13 電池周向換熱情況Fig. 13 Circumferential heat transfer of battery
4.3 進出口位置對電池換熱效果的影響
為確定最佳流動冷卻方案,進一步研究了冷卻液出入口設置對電池組冷卻效果的影響,在原有電池單體模型(出入口異側)的基礎上進行改進,設計同側出入口模型與其進行對比。該冷卻模型單體的幾何結構如圖14所示。

圖14 同側出入口布置模型幾何結構示意圖Fig. 14 Geometric structure diagram of same-side inlet and outlet layout model
在同側出入口布置的電池冷卻設計中,由于歧管流道的分層設計[40],需調整上層絕緣層厚度為5 mm。將冷卻液的出入口均置于電池的上部,即從上部進口歧管流入,折返后從上部出口歧管流出,下部絕緣層厚度保持不變。其他邊界、熱源設定及計算方法與上面的相同。電池生熱量為6 W時,同側與異側出入口布置模型在1 600 s時的溫度云圖分布對比如圖15所示。
從圖15可以明顯地看出,同側出入口布置的模型與異側布置的模型相比,在生熱量為6 W時,加熱相同的時間后,電池內部溫度更低。通過對流動跡線圖(見圖16)的分析可知,與原始單體模型的跡線圖相比,同側布置下冷卻液在內部的流動形成有折返的雙流程的冷卻過程,有利于強化電池與冷卻液之間的對流換熱,使電池溫度分布更均勻,并降低電池內部的最高溫度。

圖15 同側與異側布置溫度分布云圖對比Fig. 15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ontours between same-side and different-side

圖16 同側出入口布置模型跡線圖Fig. 16 Streamline diagram of same-side inlet and outlet layout model

圖17 不同工況下2種布置模型中電池的最高溫度Fig. 17 Maximum temperature of battery in two layout models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電池生熱量為4、6、8、10 W工況下,同側與異側出入口布置模型中電池最高溫度的變化情況如圖17所示。可以看出,在前100 s內,2種布置模型的最高溫度都呈急劇上升的趨勢;在前200 s內,2種布置模型同一時刻之間的溫差都很小;隨著加熱時間的增加,2種布置模型的溫度差異逐漸變大,在約800 s后溫度均保持穩定,2種布置模型間的溫差保持恒定。在模擬結束后,生熱量為4、6、8、10 W時,2種布置模型間的溫差分別為2、2.7、3.6、4.6 ℃。
4.4 冷卻液流量的影響
圖 18為同側和異側出入口布置的單體模型中壓降隨冷卻液流量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2種布置模型中壓降均隨冷卻液流量增加而增大,且壓降變化趨勢相同,但在流速超過0.06 m/s后,同側布置模型的壓降較異側布置模型顯著減小。
不同冷卻液流量下2種布置模型內電池的最高溫度變化情況如圖19所示,可以看出,在冷卻液流速從0.01 m/s增大到0.03 m/s的過程中,2種布置模型內電池的最高溫度均顯著下降;在冷卻液流速從0.04 m/s增大到0.10 m/s時,同側布置模型中電池的最高溫度稍有波動,但就變化趨勢而言,與異側布置模型相同,都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說明存在最優的入口流速。在不同冷卻液流量下,同側布置下電池的最高溫度始終低于異側布置下電池的最高溫度,且隨著冷卻液流量的增大,2種布置模型內電池最高溫度的差別減小。
綜合以上溫度和壓降對比情況可知,采用冷卻液同側出入口布置能夠更好地滿足電池熱管理的需求。

圖18 不同冷卻液流量下2種布置模型的壓降Fig. 18 Pressure drop of two layout models under different coolant flow rates

圖19 不同冷卻液流量下2種布置模型內電池的最高溫度Fig. 19 Maximum temperature of battery in two layout models under different coolant flow rates
5 結論
對18650型圓柱鋰離子電池組的熱管理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結合棋盤拓撲分流結構的浸沒式冷卻方法,設計了簡單合理的浸沒式冷卻拓撲結構,建立了電池陣列的單體模型和模組模型,并進行了數值模擬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1)單體模型與模組模型具有相似的計算結果,可采用單體模型代替模組模型,以降低計算資源需求。
2)出入口的不同布置對冷卻效果有較大影響。在不同冷卻液流量下,同側出入口布置和異側出入口布置模型的出入口壓差較小,但同側布置下的電池最高溫度均低于異側布置下;在不同電池放電倍率下,同側出入口布置均具有更低的電池最高溫度和更好的冷卻效果。并且,隨著電池生熱量的增大和生熱時間的增加,同側布置的優勢更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