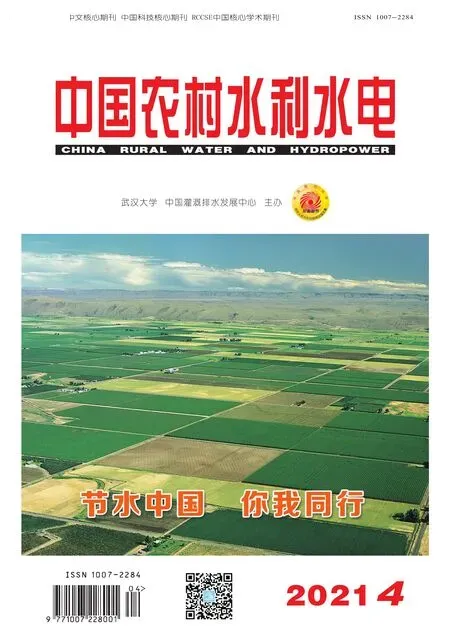水氮互作對滴灌小麥土壤硝態氮運移、氮平衡及水氮利用效率的影響
趙經華,楊庭瑞,胡文軍,阿依古麗·吾守爾,艾麥提·艾麥爾,陳凱麗
(1.新疆農業大學水利與土木工程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52;2.新疆巴州若羌縣紅棗科技服務中心,新疆若羌841800)
農業生產過程中水分與養分是影響作物生長發育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且易被人為調節控制。作物的增產優質依賴灌水與施肥的合理性,也影響著水肥高效利用[1,2]。于飛等[3]認為我國氮肥利用率近十年的均值在34.3%的水平。閆湘等[4]統計發現,我國165 個地區的主要糧食作物當季氮肥利用率波動范圍為8.9%~78.0%區間。土壤中氮素大部分會以不同的途徑消耗損失。無機氮在旱田中主要以不易被土壤膠體吸附的硝態氮形式存在,因此若累積在土壤中的硝態氮不能及時被作物汲取利用,會在灌水或降雨的淋洗下向下運移脫離根區,造成地下水硝酸鹽的污染,或造成湖泊的富營養化[5]。硝態氮在土壤中的運移、氮素平衡以及作物對氮肥的汲取與灌水、施氮密切相關。有研究發現,若超過最佳施氮量,作物獲產后硝態氮在土壤中含量會升高;但施氮量低于最佳水平時,灌水量直接導致硝態氮的淋溶[6]。李世清、PANT H K 等[7,8]研究發現,水、氮投入水平較大程度影響著玉米大田土壤剖面中硝態氮的殘留量及不同層深的分布。若施氮量超過正常水平,土壤硝態氮的含量與施氮量為正比例增長關系,作物氮素的吸收會被抑制,作物產量甚至出現不增反降趨勢。因此,探尋適宜的灌水施肥量來提高作物水氮利用效率,減少氮素淋洗,降低對農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問題亟待解決。
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區是在荒漠瘠薄的戈壁地上開發和發展起來的灌溉農業,該地區土地類型在土質結構上與一般土地區別很大,土壤肥力、有機質含量低,表層40 cm 為砂壤土,40 cm以下土層多為沙子、卵石等,土壤易滲漏,因此其水肥制度具有自身的特點[9]。旱作區作物生長和產量,以及土壤中硝態氮的遷移、累積和淋溶與灌水、施氮的關系研究較多[10-15],但水氮互作下硝態氮在土壤中的積累分布、氮損失及氮肥利用的相關研究較少。因此基于在阿勒泰地區土壤氣候條件下,研究分析土壤中水分、氮肥利用、硝態氮的遷移積累和氮素平衡在不同水氮互作條件下的變化,以期為該區春小麥灌溉制度優選及農田氮肥運籌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2016年4月-2017年8月,在阿勒泰地區福海縣地勢平坦、坡度較小的闊克阿尕什鄉渾沃爾海進行為期2年大田試驗(87°35′56″E~87°36′01″E,47°00′56″N~47°01′56″N,平均海拔445 m)。年均降水約121.90 mm,年均蒸發量約1 820.10 mm。年均氣溫4.20 ℃;極端氣溫最高達39.30 ℃,最低-41.20 ℃。該試區土質為多礫石砂土,表層40 cm 為土層,其平均干容重為1.77 g/cm3,平均田間持水量為20.07%(體積含水量);沙礫石層位于40 cm 以下,其平均干容重1.7 g/cm3,試區農田保水保肥性差。試區土壤中有機質和全氮含量為0.21%(2.1 g/kg)和0.027%(0.27 g/kg),土壤中速效磷含量9.04 mg/kg,其中由于速效氮、速效鉀含量分別為19.50 mg/kg 和92.4 mg/kg,該土質可達中等肥力水平。試區土壤全鹽含量(土水比1∶5)為0.161%(1.61 g/kg),呈弱堿性(pH:8.52),總鹽含量0.64 g/kg。
1.2 試驗設計
2016年4月至2017年8月連續2年開展小麥水肥試驗。試驗小麥采用滴灌灌溉,1 管4 行,小麥行距0.15 m,滴灌帶間距0.6 m,滴頭間距0.25 m,出流量2.6 L/h,滴灌系統工作壓力0.1 MPa。
試驗設計參照當地大田灌水及施肥處理經驗。設置水分和氮素為試驗影響因素。2016年設置了5 個水平灌水處理及3個水平施肥處理。春小麥按試驗設置灌水8 次,加出苗水1 次,各處理出苗水的灌水定額為45 mm,全生育期共灌水9 次。灌水日期分別在4月22日、5月17日、5月25日、6月3日、6月12日、6月20日、6月27日、7月4日、7月11日。通過施肥量可得N1 處理含氮量為110 kg/hm2、N2 處理含氮量為179 kg/hm2、N3處理含氮量為248 kg/hm2。各水肥處理兩兩組合,水肥試驗共設15 個處理,3 次重復,共45 個處理。2016年灌水及施肥處理具體見表1、表2。

表1 2016年各灌水處理表 mmTab.1 Irrigation water treatment table of 2016
施肥處理有如下幾個水平,如表2所示。

表2 2016年各施肥處理表Tab.2 Eac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table of 2016
2017年試驗設計在2016年的基礎上考慮了低、中、高施肥及灌水水平組合處理對作物的影響,因此設置了3 個水平灌水處理及3 個水平施肥處理。灌水與2016年相同,各處理加灌水定額為45 mm 的出苗水一次,共灌水9 次,最后一次灌水量為30 mm。灌水日期與2016年相同。通過施肥量可得N2 處理含氮量為179 kg/hm2、N4 處理含氮量為317 kg/hm2。各水肥處理兩兩組合,水肥試驗共設9 個處理,3 次重復,共27 個處理。2017年灌水及施肥處理具體見表3、表4。

表3 2017年各灌水處理表 mmTab.3 Irrigation water treatment table of 2017

表4 2017年各施肥處理表Tab.4 Eac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table of 2017
1.3 測試項目及方法
1.3.1 測試項目
(1)土壤含水率。在小麥行側不同距離布置3 根TRIME管,對不同深度土壤水分狀況進行監測。60 cm 垂直深度土層內,每隔10 cm測1個含水率。
(2)硝態氮測定。播種前測硝態氮含量底值,后從苗期開始,每個生育期取一次土。用鉆土法取土(取100 cm 土層深度,共分為5層)。將所取土樣立即帶回實驗室并于室內自然風干,再過篩制備成2 mm 土樣。經處理后的土樣,使用SEAL 流動分析儀測定在0.01 mol/L 的CaCl2浸提取液(水土比5∶1)下的土壤硝態氮含量[16,17]。
(3)植株及籽粒含氮量[18]。使用半微量凱式定氮法測定。
1.3.2 計算方法
(1)農田耗水量的計算[18]。利用實測的土壤含水量來計算作物耗水量[18],耗水量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ET1-2為階段耗水量,mm;i為土層號數;n為土層總數;γi為第i層土壤干容重,g/cm3;Hi為土壤第i層厚度,cm;θi1為土壤第i層時段初含水量,以在干土中占比計;θi2為土壤第i層時段末的含水量,以在干土中占比計;M為時段內的灌水量,mm;P0為時段內有效降水量,mm;K為時段內的地下水補給量,mm;本試驗地的地下水埋深較深大于2.5 m,地下水補給量視為0。
(2)NO3--N 累積量(kg/hm2)[19]=土層厚度(cm)×土壤容重(g/cm2)×NO3--N濃度(mg/kg)×10。
(3)土壤氮素凈礦化量[19]=不施氮肥區地上氮素累積量+不施氮肥區土壤礦質氮量-不施氮肥區起始礦質氮量。
施入氮肥、土壤起始無機氮和土壤氮素凈礦化量總體為氮輸入;作物吸收、殘留無機氮和表觀損失總體為氮輸出;表觀損失利用氮素輸入輸出的平衡模型計算。堿性土壤中的氮素主要以NO3-N形態存在,因此NH4+-N忽略不計[19]。
氮表觀損失量[20]=氮輸入量(kg/hm2)-作物吸收量(kg/hm2)-土壤殘留無機氮量(kg/hm2)。
(4)氮素收獲指數(%)[18]=籽粒氮素積累量(kg/hm2)/植株氮素積累量(kg/hm2)。
(5)氮素吸收效率(kg/kg)[21]=植株氮素積累量(kg/hm2)/施氮量(kg/hm2)。
(6)氮肥農學利用效率(kg/kg)[18]=[施氮處理籽粒產量(kg/hm2)-不施氮籽粒產量(kg/hm2)]/施氮量(kg/hm2)。
(7)氮素利用率(%)[19]=[(施氮區吸氮量(kg/hm2)-不施氮區吸氮量(kg/hm2)]/施氮量(kg/hm2)×100。
(8)氮肥表觀殘留率[19]=[(施氮區殘留量(kg/hm2)-不施氮區殘留量(kg/hm2)]/施氮量×100。
(9)氮肥表觀損失率(%)[19]=100-施氮利用率-氮肥表觀殘留率。
(10)水分利用效率(kg/(hm2· mm)[21]=籽粒產量(kg/hm2)/作物全生育期耗水量(mm)。
(11)水分生產效率(kg/(hm2· mm)[22]= 籽粒產量(kg/hm2)/作物全生育期灌水量(mm)。
1.4 數據處理
數據處理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0;統計分析軟件采用DPS,試驗數據單因素顯著性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較使用LSD法。
2 結果與分析
2.1 水氮互作下小麥不同生育階段耗水量、耗水模數、日耗水量及總耗水量的響應
由表5、表6可得,各生育期的小麥耗水模數在不同水氮處理下均接近,且從2年數據總體來看,耗水量和耗水模數在生育期內的都表現為抽穗揚花期=灌漿期>拔節孕穗期>分蘗期=成熟期>出苗期。小麥各處理耗水量在出苗期差異不大;在抽穗揚花期的耗水模數與灌漿期相近且最大,在20%~28%的范圍之間。2年日耗水量數據顯示,各處理在拔節孕穗期至灌漿期均高于其他生育時期,且其值在3.28~7.72 mm 范圍內波動。2016年日耗水量數據表明在同一施氮水平下,W1 處理與W2處理差異不顯著,W3 處理與W4 處理差異不顯著。2年的日耗水量表明W3 處理與W5 處理無顯著差異。2016年日耗水量數據表明,在同一灌水水平下,N1 處理的總是小于N2、N3 處理。2017年日耗水量數據表明,在同一灌水水平下,N0 處理總是小于N2、N4處理。說明當氮肥相對較低時,對小麥日耗水量有一定的影響。

表5 2016年水氮互作對小麥不同生育階段耗水量(CA)、耗水模數(CP)、日耗水量(CD)的影響Tab.5 Effect of water and nitrogen interaction on water consumption(CA),water consumption modulus(CP)and daily water consumption(CD)of wheat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in 2016

表6 2017年水氮互作對小麥不同生育階段耗水量(CA)、耗水模數(CP)、日耗水量(CD)的影響Tab.6 Effect of water and nitrogen interaction on water consumption(CA),water consumption modulus(CP)and daily water consumption(CD)of wheat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in 2017
從同一施氮量梯度下看,2016年數據表明(如圖1),N1 處理下耗水量與灌水量成正比例增長關系,W1N1 與W2N1 差異顯著,W3N1 與W4N1 處理差異不顯著,W4N1 與W5N1 處理差異不顯著。在含N2、N3施氮水平的各處理下,增加灌水量時耗水量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在N2處理的施氮水平下,W4N2與其他處理的耗水量差異顯著,W3N2 處理與W5N2 處理的耗水量無顯著差異。在N3 處理的施氮水平下,W4N3 處理耗水量最大,W3N3 與W4N3 無顯著差異。2017年數據表明(如圖2),小麥總耗水量隨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W3處理與W5處理的總耗水量差幅在1%~2%,差異不顯著,W1 處理與W5 處理的總耗水量差幅達到16%~24%。N0 和N2 處理的施氮水平下,W1 處理與W5處理的耗水量差異顯著。

圖1 2016年小麥總灌水量和耗水量Fig.1 Total irrig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heat in 2016

圖2 2017年小麥總灌水量和耗水量Fig.2 Total irrig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heat in 2017
從同一灌水量梯度下看,2016年中除在含W4 灌水水平處理下,總耗水表現為N1<N3<N2;其他同一灌水水平下,總耗水表現為N1<N2<N3。含N1 的各處理與W3N3、W4N3、W5N3 差異顯著,W3N2、W4N2、W5N2 處理與W3N3、W4N3、W5N3 處理的耗水量差異不顯著。2017年中總耗水表現為N0<N4<N2;N2處理與N0 處理差幅為14%~15%,N2 處理與N4 處理差幅為4%~9%。在W1 灌水水平下,W1N0 與其他處理差異顯著,在較低的水分與施氮水平組合下,對小麥耗水量有顯著影響。在W3、W5 灌水水平處理下,N0 與N2 處理均差異顯著。W3N2、W5N2 處理的總耗水量最大,除W3N4、W5N4 處理的總耗水量與W3N2、W5N2 處理無顯著差異,其他處理都分別與W3N2、W5N2處理差異顯著。
綜合2年小麥總耗水量分析表明,灌水量在285~390 mm(W1 處理~W3 處理),小麥耗水量隨灌水量增加而明顯增加,灌水量大于390 mm(W3 處理),水分發生深層滲漏損失。在同一灌水水平下,在0~248.34 kg/hm2(N0 處理~N3 處理)增加施氮量可促進小麥耗水量的消耗,但施氮量在179.34~248.34 kg/hm2(N2 處理~N3 處理)增加施氮量能有效促進小麥耗水量的消耗,施氮量超過248.34 kg/hm2(N3 處理),小麥水分消耗對增施氮素響應不顯著甚至水分的消耗被抑制。
2.2 水氮互作下0~100 cm土層土壤中硝態氮的響應
從圖3可以得出,各處理在各生育期的硝態氮含量整體都隨著深度呈現減小趨勢。不同處理各生育期下均在0~20 cm土層出現土壤硝態氮含量的最大值。在分蘗期,0~20 cm 各處理差異差幅較大,在分蘗期和拔節期,在20~60 cm 土層,W5處理的硝態氮含量遠遠小于其他處理,在分蘗期其他處理比W5處理平均高62%。在拔節期其他處理比W5處理高59.76%。在抽穗揚花期至成熟期并未施肥,在同一施氮水平下,W4、W5 處理的0~60 cm 土層硝態氮含量小于其他處理,在抽穗揚花期相差3%~132%(平均差幅44%);在灌漿期相差0.1%~86%(平均差幅14.89%);在成熟期相差0.1%~229%(平均差幅58.65%)。

圖3 不同水氮處理下小麥各生育期土壤剖面硝態氮含量分布Fig.3 Nitrate content distribution in soil profile of wheat at each growth stage under different water and nitrogen treatment
各處理土壤硝態氮含量在0~60 cm 土層隨小麥的逐漸生長變幅較大,60~100 cm 變幅較小。通過試驗發現:生育中期的土壤硝態氮含量遠高于生育后期,W5 處理水平下的各處理的硝態氮含量在0~60 cm 土層變幅相對其他處理較小,且硝態氮含量也相對其他處理低;在80~100 cm 土層的土壤硝態氮含量比灌漿期至成熟期大,且變幅也較灌漿期至成熟期大。
2.3 水氮互作對土壤氮平衡的影響
2017年與2016年試驗方案有所不同,2017年試驗在2016年基礎上更具針對性的考慮低、中、高施肥處理的情況,因此只對2017年0~60 cm 剖面土壤進行氮素平衡分析。如表7所示,土壤水分較低會影響土壤礦化量,礦化量與灌水量之間成正比例關系,提高土壤礦化量可以通過適當增加灌水量。土壤播前殘留氮量與小麥全生育期土壤礦化量共計在62.38~97.40 kg/hm2范圍內,該產量水平下作物氮素需求量可全由土壤自身供氮量提供,也揭示了施氮增而產量不增的原由[19]。在小麥獲產后利用氮平衡原理計算發現,表觀損失在N2 處理水平下為116.36~125.79 kg/hm2,N4 處理水平下為232.21~246.37 kg/hm2;N2 處理與N4 處理的表觀損失差異顯著,W3N2 處理與W5N2處理的差異不顯著,施氮量為N4的各處理間表觀損失差異不顯著。

表7 2017年不同處理小麥0~60 cm剖面土壤氮素平衡 kg/hm2Tab.7 Soil nitrogen balance in 0~60 cm profile of wheat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2017
各灌水處理下,硝態氮的淋失量(初始土體硝態氮積累量和土體殘留硝態氮)在土壤剖面中最大的是N0 處理。各處理剖面損失量在N0施氮水平下為正值,表明淋失量最大;除N0施氮水平下其他處理均為負值,表明硝態氮在0~60 cm 土層有累積量。在N2、N4同一施氮水平下,隨灌水量的增加硝態氮淋失量增大,說明土壤硝態氮累積量減小。在同一灌水水平下,隨施氮量的增加硝態氮淋失量減小,說明土壤硝態氮累積量增加,此試驗結果與栗麗一致[6]。
2.4 水氮互作對籽粒產量、水氮吸收利用效率的影響
如表8和表9數據可以看出,在各施氮處理水平下,小麥產量都隨灌水量的增加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在同一施氮水平下(除N0 外),2年的植株含氮量、籽粒含氮量、氮素收獲指數、氮素吸收效率都隨灌水量的增加也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在同一灌水水平下,隨著施氮量的增加,2年的植株含氮量都在增加。灌水定額為W3、W4(45~52.5 mm)處理,施氮量為N2、N3(179~248 kg/hm2)的水氮組合對產量增長有益,當施氮量超過N3處理(248 kg/hm2)的施氮量會抑制小麥產量。

表8 2016年度水氮互作對籽粒產量、水氮吸收利用效率的影響Tab.8 Effect of water and nitrogen interaction on grain yield,water and nitrogen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 2016

表9 2017年度水氮互作對籽粒產量、水氮吸收利用效率的影響Tab.9 Effect of water and nitrogen interaction on grain yield,water and nitrogen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 2017
2016年數據顯示,隨著施氮量從N1提高至N2,產量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漲;但當施氮量從N2 提高至N3,W2N3 產量沒有增長反而降低了9%,2017年數據顯示,將氮肥從N0 處理提高至N2處理,產量大幅提高;將N2處理氮肥用量提高至N4處理,與之相關的W3和W5處理產量降低。有學者研究表明,小麥產量對氮肥增施下的表現為:氮肥在適宜的范圍內增加用量,產量會隨之增加,若超過最佳用量范圍后籽粒產量增加不顯著,或出現不增反降趨勢。以上分析可知,灌水定額為W3、W4 處理,施氮量為N2、N3 的水氮組合對產量增長有益,當施氮量超過N3處理的施氮量會抑制小麥產量。
在2016年同一灌水水平下,籽粒含氮量與施氮量成正比;氮素收獲指數與施氮量成反比。在2017年W1 灌水水平下,籽粒含氮量也與施氮量成正比。W3、W5 灌水處理水平下,籽粒含氮量隨施氮量的增加呈拋物線趨勢,在N2 處理達到峰值,表明施肥量超過N2 水平籽粒吸收氮素的能力被影響。2017年氮素收獲指數隨施氮量的增加呈先增后減的趨勢。2年的氮素收獲指數表明于N0、N1施氮水平區間內,增施氮肥有利于小麥氮素向籽粒轉移,當施氮量超過N1 水平時,增施氮素對其后期向小麥籽粒轉移產生不利影響。
在2016年同一灌水水平下隨施氮量的增加氮素吸收效率呈先增后降的趨勢。2017年在同一灌水水平下隨施氮量的增加氮素吸收效率則減小。2年的數據表明,在同一灌水處理下,最有利于提高氮素吸收效率的為N2 處理。在同一施氮水平下(除2017年N0 施氮水平)2年的水分生產效率整體表現為隨灌水量的增加而減小的趨勢;但在同一灌水水平下,水分生產效率隨施氮量的增加規律不明顯。在同一施氮水平下(除2017年N2 施氮水平)2年的水分利用效率隨灌水量的增加整體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在W2、W3 處達到最大值;但在同一灌水水平下,水分利用效率隨施氮量的增加規律不明顯。
3 討 論
前人已對施氮量、土壤水分與不同土層硝態氮之間的關系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施氮量對各土層中硝態氮的影響,與本文結論基本一致,即各層深土壤中硝態氮含量與施氮量成正比[11,12]。而前人研究中關于硝態氮隨土壤水分運移變化相關的結論不盡一致。有研究表明,土壤水分的下滲會引起硝態氮的淋失,一部分人認為灌水或降水越多,淋失就越多,但另一部分人認為在灌水較多的作物生長期硝態氮淋失并不多[23,24]。本文研究表明,總體來看硝態氮含量在0~100 cm 土層中隨深度加深逐漸減小,呈現“上高下低”的分布情況,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25,26]。根據2年小麥耗水規律研究,小麥耗水量與灌水量呈正比例關系,但灌水量大于390 mm(W3處理),水分因大量的深層滲漏而損失。硝態氮由于不易被吸附在土壤膠體上,若土壤中累積的硝態氮不能及時被作物汲取利用,硝態氮會隨灌水下滲而向下運移脫離根區土壤。經分析表明在阿勒泰地區的土壤環境下,當灌水量大于390 mm(W3處理)時,由于該區土壤持水性能較差大量硝態氮隨灌溉水分的下滲而淋失。
試區多礫石砂土土壤持水性能較差,大量硝態氮會因灌水而淋失,根據各處理表觀損失表明,硝態氮的表觀損失隨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大,在同一施氮水平下,硝態氮表觀損失在各處理之間的差異不大,但在同一灌水水平下,N2與N4水平下的各處理的表觀損失差異明顯。如表10所示,在同一施氮水平下,氮肥利用效率隨灌水量的增加而減小,氮肥表觀損失隨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同一灌水水平下,隨著施氮量的增加,氮肥表觀損失增加。各處理的氮肥表觀損失率相比氮肥利用效率以及氮肥表觀殘留率更高,說明在此土壤條件下,損失的氮肥占施氮量的大部分。上述分析表明,灌水量對于0~60 cm 土壤硝態氮的表觀損失的影響是顯著的,其主要原因為淋溶的產生,大量硝態氮隨水分下滲被淋洗至60 cm 以下的土壤中,且施氮量的增加也加劇了硝態氮淋溶。在同等施氮水平下本試驗中的表觀損失量遠大于其他研究中[6,19,27,28]的表觀損失量,也印證了習金根、WANG F L 等[29,30]的土壤硝態氮更易在土壤性質輕薄、砂性土發生淋溶的觀點。

表10 2017年度水氮互作對水氮吸收利用效率的影響Tab.10 Effect of water and nitrogen interaction on water and nitrogen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 2017
如表10所示,在N2施氮水平下,氮肥農學利用效率隨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表明在此施氮水平下增加灌水量可促進氮肥的增產效益。在N4 施氮水平下,氮肥農學利用效率隨灌水量的增加而減小,表明在此施氮水平下增加灌水量抑制了氮肥的增產效益。在W1 灌水水平下,氮肥農學利用效率隨施氮量的增加也在增加,表明在此灌水水平下增加施氮量可促進氮肥的增產效益。在灌水量高于W1 處理的水平時,氮肥農學利用效率隨施氮量的增加逐漸減小,表明在灌水量高于W1 的灌水水平時增加施氮量,氮肥的增產效益有所降低。
2016年試驗中可以發現在灌水水平W3 與W4,施氮水平N2 下,對小麥的耗水量和生長發育的影響更為明顯,小麥產量達到了最大值,超過此灌水及施氮水平后,小麥產量都有不同幅度的降低。在2017年試驗設計更加具有針對性,集中對低、中、高肥做了對比,但由于2017年試驗設計施氮量差異較大,由于閾值的影響,試驗結果對比不明顯,但2017年試驗也可以看出與2016年相似的試驗結果。通過2年的試驗可以得到灌水和施氮在小麥生長中影響的一個閾值。前人研究表明[25,31,32]灌水和施氮對作物產量及作物對氮素的吸收有促進作用,但是在作物生長發育中水肥耦合存在一個臨界閾值,低于此臨界閾值可通過增加水肥投入促進增長,但高于此臨界閾值時,增產效果不明顯或有可能減產。
前人關于小麥水氮利用效率與氮肥、水分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且水氮交互作用對其影響的研究也較少[18,21]。在同一施氮水平下(除N0 處理外),2年的植株含氮量、籽粒含氮量、氮素收獲指數、氮素吸收效率都隨灌水量的增加呈先增后減的趨勢,W3處理達到最大值。2年試驗的植株含氮量都在增加,但氮素吸收效率隨著施氮量的增加而減小,N2 處理達到最佳。本試驗通過2年的小麥水氮互作的研究表明在同一施氮水平下(除2017年N2施氮水平)水分利用效率隨灌水量的增加總體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在W2、W3 處理處達到最大值。在同一灌水水平下水分利用效率隨施氮量的增加規律不明顯。但試驗于阿勒泰的多礫石砂土上進行,因此還需對不同土質上水氮互作對作物的影響繼續深入研究。
4 結 論
經過2年試驗表明,施肥量在179~248 kg/hm2(N2 處理~N3 處理),灌水定額為45 mm,灌溉定額為390~405 mm(W3 處理)的水氮組合為干旱地區多礫石砂土的土壤條件下的最佳水肥組合。當增加施氮量超過248 kg/hm2(N3 處理),籽粒吸收氮素能力受到影響,籽粒產量增加不明顯,且有降低趨勢。當灌水量大于390 mm(W3處理),大量灌溉水會發生深層滲漏損失;土壤硝態氮含量也受到顯著的影響,大量硝態氮隨灌溉水的下滲而淋溶。此試驗中氮素損失,主要原因是淋溶的損失,大部分硝態氮隨水分滲漏被淋洗至60 cm 以下的深層土壤中,且隨著施氮量的增加硝態氮淋溶更為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