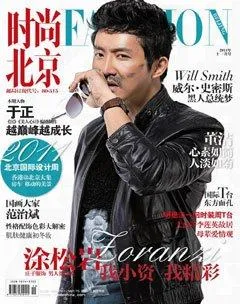社保所長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幫親屬“參保”是貪污還是受賄
一、基本案情
2009年9月,某鎮(zhèn)社保所所長林某在辦理“征地農(nóng)民養(yǎng)老保險(xiǎn)”時(shí),發(fā)現(xiàn)符合參保條件的張某、周某沒錢繳費(fèi),自愿放棄參保。林某便告知熊某(林妻的嫂嫂)可以拿5萬元“參保”,熊某同意并分兩次交給林某5萬元。9月30日林某將其中的28700元用于繳張某、周某的參保費(fèi),剩余的用于個(gè)人開支。11月28日,林某、熊某一起到銀行領(lǐng)取第一筆保險(xiǎn)金7500元,林取出錢后就將錢和存折一起交給熊某。2013年1月,林某聽到有人議論后便將存折收回交給張某、周某。2009年11月至2013年1月,熊某共領(lǐng)取養(yǎng)老保險(xiǎn)金58410元。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rèn)為,林某身為某鎮(zhèn)社保所所長,在經(jīng)辦被征地村民農(nóng)轉(zhuǎn)非養(yǎng)老保險(xiǎn)事宜中,采取虛假手段,致使國家財(cái)產(chǎn)為其親屬所有。由于林某主觀上無非法占有養(yǎng)老保險(xiǎn)金的故意,其行為實(shí)質(zhì)為濫用職權(quán),因損失達(dá)不到濫用職權(quán)的立案標(biāo)準(zhǔn),其行為不構(gòu)成犯罪。
第二種意見認(rèn)為,林某明知參保費(fèi)只需繳2.87萬元,之所以索要5萬元,認(rèn)為還有一些其他開支,包括自己的辛苦費(fèi)。熊某也清楚繳保費(fèi)用不了5萬元,多的錢是給林某的感謝費(fèi)。林某利用職務(wù)便利為熊某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并收取好處費(fèi),其行為構(gòu)成受賄罪。
第三種意見認(rèn)為,林某利用管理公共財(cái)物的便利,采取虛假手段,騙取養(yǎng)老保險(xiǎn)金為其親屬所有,因?yàn)椤耙苑欠ㄕ加袨槟康摹辈灰欢ǚ且救苏加校部梢杂傻谌苏加校帜潮救耸欠駥?shí)際分得財(cái)產(chǎn),不影響貪污罪的構(gòu)成,林某的行為構(gòu)成貪污罪。
第四種意見認(rèn)為,林某利用管理公共財(cái)物的便利,隱瞞事實(shí)真相,利用他人身份信息為其不符合參保條件的親屬“參保”。林、熊二人具有冒用他人名義騙保的故意,并共同實(shí)施了騙保的行為,屬于共同貪污。
三、評(píng)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四種意見。
(一)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不局限于本人占有
刑法調(diào)整和規(guī)制的是犯罪行為,刑法思維的基點(diǎn)是犯罪行為對(duì)社會(huì)的危害,而不是行為人從犯罪行為中獲得的利益。評(píng)價(jià)一個(gè)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罪,不是看行為人本人從中獲得的收益,而是看行為給權(quán)利人造成了什么危害。有的行為即便沒有給行為人本人帶來任何好處,甚至可能對(duì)行為人本人造成損害,但只要該行為損害了他人的合法權(quán)利,對(duì)社會(huì)造成了危害,符合刑法的明文規(guī)定的,即構(gòu)成犯罪。從刑法思維的這一基點(diǎn)出發(fā),在侵犯財(cái)產(chǎn)犯罪中,不管行為人是將他人財(cái)物非法占為己有或者轉(zhuǎn)為第三人所有,都以行為人對(duì)他人財(cái)物事實(shí)上的非法控制為前提。就權(quán)利人而言,一旦自己的財(cái)物被他人非法控制,即意味著其對(duì)物的所有權(quán)受到了侵害,亦即喪失了對(duì)該財(cái)物進(jìn)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quán)利。因此,將他人財(cái)物非法占為己有或者轉(zhuǎn)為第三人所有,都表現(xiàn)為排除權(quán)利人對(duì)財(cái)產(chǎn)的合法控制,并以此為前提排除權(quán)利人對(duì)財(cái)產(chǎn)進(jìn)行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quán)利,從而實(shí)際剝奪權(quán)利人對(duì)財(cái)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
貪污罪的主觀方面必須出于故意,而且必須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財(cái)物的犯罪目的。但貪污罪的主觀方面不應(yīng)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將公共財(cái)物非法占為己有或非法取得公共財(cái)物的所有權(quán)的犯罪目的為必要條件,只要行為人具有非法排除權(quán)利人對(duì)公共財(cái)物的所有權(quán)而將公共財(cái)物置于自己的非法控制的意圖,即已充足了貪污罪的主觀要件。行為人控制公共財(cái)物后是否據(jù)為己有,不影響貪污既遂的認(rèn)定。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并非僅指行為人自己將公共財(cái)物占有并享用,也包括將其轉(zhuǎn)歸為第三人非法所有。在本案中,林某利用職務(wù)便利將公共財(cái)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即使自己一分錢不得而轉(zhuǎn)歸他人,仍然構(gòu)成貪污既遂。
(二)林某的行為不能認(rèn)定為受賄
刑法對(duì)貪污罪和受賄罪都規(guī)定有“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但貪污罪是利用管理公共財(cái)物的職務(wù)便利,受賄罪是利用管理公共事務(wù)的職權(quán)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條件,貪污罪利用職務(wù)上便利的內(nèi)涵小于受賄罪利用職務(wù)上便利的內(nèi)涵。林某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幫熊某“參保”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頂替他人的指標(biāo),用熊某自己的名義參保;一種是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參保”。如果林某利用職權(quán)讓熊某以自己的名義參保,林某的行為符合受賄罪的利用管理公共事務(wù)的職權(quán)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行為要件,涉嫌受賄罪。但在本案中,林某是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參保”,交給熊某的是投保戶的領(lǐng)款存折,其行為更接近貪污罪經(jīng)手管理公共財(cái)物的行為要件。林某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始終未能讓熊某實(shí)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參保(行為人認(rèn)為已參保是認(rèn)識(shí)上的錯(cuò)誤),熊某每月領(lǐng)取社保金只不過是“騙保”過程的延續(xù)。所以,不能將熊某所謂的“參保”,理解為是林某為其謀取到的利益,從而將此案定性為受賄。
還有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林某“騙保”是手段行為,為熊某謀取利益并收受財(cái)物是目的行為。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發(fā)生牽連,屬牽連犯,應(yīng)當(dāng)從一重處,定貪污罪或受賄罪。筆者認(rèn)為,牽連犯的成立的條件是,數(shù)罪必須出于同一個(gè)犯罪目的。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過實(shí)施犯罪行為達(dá)到某種危害社會(huì)結(jié)果的心理態(tài)度,也就是危害結(jié)果在犯罪人主觀上的表現(xiàn)。貪污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共財(cái)物,受賄的目的是索取和收受他人財(cái)物,目的明顯不一致,不能按牽連犯處理。那么,如何理解林某“騙保”與為他人謀取利益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呢?筆者認(rèn)為,林某礙于親情,為親屬謀取利益,是林某“騙保”(貪污)的動(dòng)機(jī),“騙保”才是林某的真正目的。犯罪動(dòng)機(jī)是指刺激、促使犯罪人實(shí)施犯罪行為的內(nèi)心起因或思想活動(dòng),犯罪動(dòng)機(jī)是產(chǎn)生犯罪目的的原因。貪污罪不以特定的犯罪動(dòng)機(jī)為其主觀方面的必備要素,只要故意實(shí)施了利用職務(wù)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財(cái)物的行為,無論出于何種動(dòng)機(jī),不影響貪污罪的構(gòu)成。
(三)本案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wù)便利實(shí)施的共同犯罪
本案是否屬于共同犯罪,關(guān)鍵是看林、熊二人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據(jù)林某供述:“在張某和周某簽了不參保的承諾書后的兩、三天,我就給熊某說有兩個(gè)人不繳費(fèi)參保,你先冒名繳了之后自己領(lǐng)取養(yǎng)老保險(xiǎn)金。以后我讓她(指熊某)把存折本交出來就要交出來。她表示同意。”從以上供述可以看出,熊某應(yīng)當(dāng)知道林某是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讓自己“參保”,因此,林、熊二人主觀上都具有騙保的故意。從客觀方面看,本案應(yīng)該有兩個(gè)實(shí)行行為,一是張某、周某放棄參保后,林某利用職務(wù)便利讓熊某“參保”;二是熊某每月領(lǐng)取保險(xiǎn)金直至案發(fā)。林某用他人的身份信息讓熊某“參保”,是共同貪污實(shí)行行為的前部分,熊某每月冒名領(lǐng)取保險(xiǎn)金是實(shí)行行為的后部分。如果只有前部分行為,林某最多只能算貪污未遂,因?yàn)榇藭r(shí)公共財(cái)物并未發(fā)生轉(zhuǎn)移。林某為熊某辦理所謂“參保”的手續(xù),以及熊某冒名領(lǐng)款的行為與公共財(cái)物被非法占有的犯罪結(jié)果具有直接的因果聯(lián)系,共同構(gòu)成完整的貪污犯罪的實(shí)行行為。林、熊二人之所以構(gòu)成共犯,是因?yàn)樗麄兊男袨槎俭w現(xiàn)共同的意志,其行為方式不同是分工不同而已,共同對(duì)犯罪結(jié)果的出現(xiàn)起著決定作用。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貪污、職務(wù)侵占案件如何認(rèn)定共同犯罪幾個(gè)問題的解釋》(2000年6月27日)第1條規(guī)定:行為人系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jié)、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wù)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cái)物的,以貪污罪共犯論處。在本案中,熊某(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林某(國家工作人員)經(jīng)手管理公共財(cái)物的職務(wù)便利,共同貪污社保資金29710元(58410元-28700元),其中林某實(shí)得21300元,熊某實(shí)得8410元。林某、熊某應(yīng)當(dāng)以共同貪污罪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