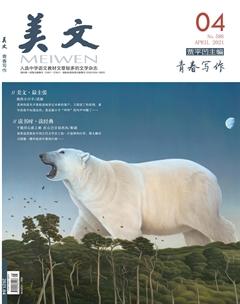渭河,我們的精神原鄉
陳敬楊

每個人關于故鄉的夢里,都有一條無法與生命割裂的河流。在無數個輾轉反側的不眠之夜,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條承載著我們悲喜苦樂的河流。無論是生活在寶雞,還是遷移到西安,渭河就是那條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值得守護的家鄉河。
渭河是黃河的最大支流,也是西安的最大水源。在長安八水中,涇河、灃河、澇河、潏河、滈河都直接或間接地注入渭河。渭河流經的區域,繪制出美妙絕倫的自然景觀。元代趙善慶在《山坡羊·長安懷古》中寫道 :“驪山橫岫,渭河環秀。”數千年來,渭河猶如一條玉帶,蜿蜒行走在三秦大地,為顯得有些頹敗和悲壯的關中平原增添了幾分色彩和靈性,使人在春華秋實的繁華里沉醉其中,流連忘返。試想,如果沒有渭河,何來“八水繞長安”的盛景?
其實,渭河也是關中的生命河和西安的母親河。她一路披荊斬棘,穿過西北高原,沖出秦嶺的懷抱,在西安的春光中放慢了腳步,以廣博的胸懷,龐大的水系,甘冽的清泉,灌溉了河流兩岸八百里秦川的阡陌良田,打造出富甲一方的“天府之國”,滋養著上千萬秦人的生命,使之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安居樂業。
有趣的是,說到“天府之國”,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成都,又有幾人知曉,這個名稱開始并非形容四川,而是描繪關中。早在戰國時期,縱橫家蘇秦便對秦惠王說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隨后,在秦末漢初,張良更是坐實了這個觀點 :“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可惜的是,這個描述忽略了渭河的意義。正是因為渭河的存在,才養成了廣袤豐沛的關中平原和美麗繁榮的十三朝古都。
若是僅僅如此,渭河并不會讓我如此難忘。渭河身上散發著傳統文化的魅影,遠超它的絕世美景和現實價值。渭河對中國農業文明的深遠影響和農耕文化的根本塑造,才是她縈留我心,久久不散的原因。傳說中的神農氏穿越了雄偉險峻的秦嶺山脈,跨過了洶涌澎湃的渭河流域,發明刀耕火種,創造耒耜,播散五谷,發展農耕 ;嘗遍百草,確定藥性,發明醫藥 ;統一時間,固化地點,實施物物交換,融合華夏民族等,成為民族文化中的“農業之神”“醫藥之神”“太陽之神”,奠定了中國農業文明的基礎。至今,他在與自然和社會的斗爭中激發出的創業精神、奉獻精神、敢為人先的創造精神,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仍然散發著可與日月爭輝的光與熱,影響著這一方水土這一方人。陜西被稱為華夏故里,中國人被稱為炎黃子孫,無不彰顯其功。說神農氏用一個人的力量形塑了整個渭河流域乃至整個民族的農業文明和農耕文化也不為過。他推動了渭河發展的同時,渭河也養育了他。沒有這條洶涌澎湃的河流,又怎會有中華民族如今的繁榮昌盛和源遠流長。
初識渭水時,我從未想過她還有這樣一重身份。她不僅僅養育了關中平原的這片熱土,而且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甚至塑造了國人的精神品格,建構了我們的精神原鄉。在渭河流經的地方——周至樓觀臺,老子創作了名垂千古的《道德經》。渭水長期的浸潤,讓他頓悟了水的智慧。他在書中寫道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這段文字的字面意思是說君子在做人方面應像水一般,隨物賦形,與世無爭,待人真誠。實際上,它完美地詮釋了中華文化有容乃大、開放包容的文化品格。
詩人王昌齡、杜牧、白居易、書畫家顏真卿、閻立本等人無不佇立在藝術的頂峰,以自己胸懷和氣度書寫著“盛唐氣象”的華章。若不是受惠于渭水的洗禮,他們又怎么會展現出如此之高的藝術成就?若不是那條奔騰不息的河流,又怎會出現這座積淀了厚重歷史的古城?自此以后,長安成為承載著文人情懷的精神原鄉,吸引著千千萬萬的羈旅游子。誰能想到,中華文化最為璀璨的部分竟來自一條在史書中稍顯黯淡的大河。當周秦漢唐最閃耀的歷史畫卷在世人面前一一鋪展開來時,它以無與倫比的姿態告訴世人 :中國最強盛的千年史,就是喝渭河水的歷史!
渭河,一條擁有如此重要價值和意義的河流,它是我們生命得以存活的保證,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是我們精神皈依的空中花園。在全世界水資源奇缺的年代,我們有何理由不去愛她、保護她呢?我們要用一顆勇敢、堅定、火熱的心去守護她,去反哺她,去報答她。對我們來講,保護以渭河為代表的水資源,不僅是為我們謀求物質食糧,而且是為我們探尋民族文化的根脈,更是為我們的靈魂尋求安放的家園。這樣,我們才算理解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