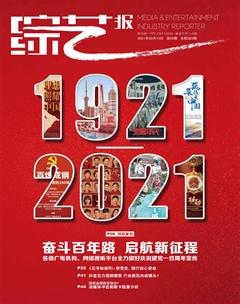節慶季是媒體融合成果的考驗季
胡正榮
中國教育電視臺總編輯,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曾任中國傳媒大學校長。主要研究傳播學理論、新媒體。國際傳播、傳播政治經濟學等領域。
主流電視媒體的各種春作品品和產品,為什么鮮有如《唐官夜宴)》這般,在互聯網平臺如此出圈、如此網紅般的傳播呢?
每年的1月、2月是節慶集中的季節(公立新年、農歷春節、正月十五等),更是人們精神產品消費的集中時節。媒體是此時人們歡慶節日最為重要的儀式平臺與通道之一,更是人們消費精神產品的最為重要的平臺與手段之一,特別是在媒體融合的今天,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今天,基于媒體的節慶儀式和節慶消費更具意義。
在我國,媒體成為人們節慶不可或缺的儀式與消費平臺的最典型案例,就是電視春節聯歡晚會。自從1983年中央電視臺首次以直播形式播出電視春節聯歡晚會以來,各地電視媒體都在年復一年地復制著這種節慶儀式與消費模式,并且衍生出了各種新的形態,如春節戲曲晚會、相聲晚會,以及跨年晚會等,將儀式與消費延長并縱深化。21世紀新媒體興起之后,互聯網平臺則將這種節慶季的媒體產品生產與消費升級到更加多樣化、垂直化、互動化、以用戶為中心的形態。實際上,這也在大大擠壓傳統主流媒體的儀式平臺空間和消費渠道機會。
今年春節各種媒體的表現,更加突顯了這種轉向的趨勢。河南電視臺春晚節目《唐宮夜宴》在電視消費場景中的影響力,遠遠沒有在互聯網上穿越各種消費場景的影響力大,其互聯網傳播更是基于用戶自主自愿而生成的。主流電視媒體的各種春晚作品和產品,為什么鮮有如《唐宮夜宴》這般,在互聯網平臺如此出圈、如此網紅般的傳播呢?事情似乎頗有“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偶得之趣,不過,河南電視臺表示“何以回報,唯有作品”!這還真是應該有的答案。不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無論是核心競爭力還是內容,這里所說的內容是媒體融合時代,特別是全媒體時代應該有的界定,其內涵已經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內容本身,還應該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與外延,比如形式與內容、工具與內容、封閉性/開放性與內容等。
媒體融合時代,我們不應該孤立地看待一臺春晚、春晚中的一個節目,即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個內容,而應該系統、融合、全媒體、全業態地看待一個內容。因此,我們需要處理好內容本身的原創性,以及以用戶為中心的創作、生產動機與動力,還要處理好內容與形式、內容與工具、內容中人與物、經典與流行、內容封閉性與開放性、形態融合與分散等各種復雜多樣的關系。這些都是媒體融合時代對媒體生產與消費提出的新挑戰。
從今年開年的節慶季媒體儀式與媒體消費中,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挑戰的嚴峻性。首先,媒體上節慶消費的是內容還是形式,是內容還是工具,是內容還是技術?答案不言而喻,應該是前者重于后者。不過,現實中,形式大于內容,工具依賴重于內容吸引,技術崇拜強于內容創新仍比比皆是。一味地突出新式聲光電;機械地鋪陳各種光影效果;迷信地超前運用VR和AR等;炫技般追求新工具使用,如無人機集群、上帝視角拍攝等,都已經成為潮流。其實這種形式主義、工具理性、技術理性,早已經是被人詬病的,貌似先進、其實陳腐的觀念和做法。最先進的技術和工具、最絢爛的形式,也無法彌補內容的貧乏、空洞、無力。
其次,節慶季媒體儀式和消費的主體是人還是物?答案也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前者當然應該重于后者。不過,我們還是在媒體奉獻的節慶季作品中看到了“遺憾”。場面越來越大,空間越來越排場,天宇般LED巨幕,升降起伏舞臺,而人已經成了點綴,渺小到個體都是麻麻點點的一片。互聯網時代,各類平臺都重視中近景乃至近景與特寫,目的是突出人,突出人的表情,突出人的行為。《唐宮夜宴》內容中的人及其服裝、表情、動作的成功,是其得以出圈的根本動力和原因。人是儀式的主體,人是消費的主體。
第三,節慶季媒體儀式和消費是一種自娛自樂的閉環系統還是與民同樂的開放系統,是內容封閉、平臺集中還是內容開放、平臺融合?答案應該是后者更符合媒體融合時代的要求。去年,中央文件已經提出媒體融合要“強化媒體與受眾的連接,以開放平臺吸引廣大用戶參與信息生產傳播,生產群眾更喜愛的內容,建構群眾離不開的渠道”、傳統媒體的專業化,造就了相對閉環的策采編評發系統和傳統;但是,閉環生產的產品、中心化的平臺,其實是與全媒體傳播體系漸行漸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