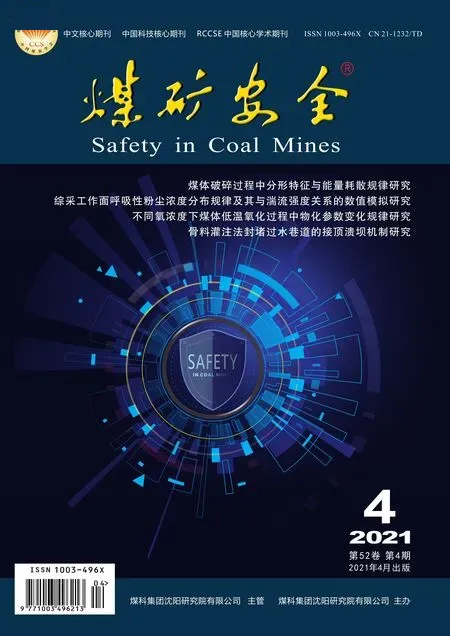加載方式與沖擊速度對煤裂紋擴展規律的影響
樊國偉,孫 荘,尚軍寧
(1.運城職業技術學院 教學礦井,山西 運城044000;2.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能源與礦業學院,北京100083)
在地下工程中,特別是在煤炭開采過程中,一直伴隨著煤巖體的失穩破壞,這是由煤巖體在不同受載條件下的斷裂失穩導致的。近年來,我國煤炭資源的開采重點轉入深部開采[1],高應變率下的沖擊斷裂失穩更是頻有發生,對生產安全和人員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因此,研究煤巖體在不同加載方式下的動態斷裂特性,認清煤巖體在沖擊載荷下的裂紋擴展規律,將對沖擊地壓等動力災害事故的現場工程防治與煤礦安全指導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
斷裂力學將基本加載方式分為Ⅰ型加載(張拉型),Ⅱ型加載(剪切型),Ⅲ型加載(撕開型)[2],2 種以上加載方式的組合為復合型加載。而在工程實體中,Ⅰ-Ⅱ復合型加載較為常見[3],因此,Ⅰ-Ⅱ復合型加載及其基本加載方式即Ⅰ型和Ⅱ型加載成為了研究的重點。為此國內外學者分別對銹巖[4]、花崗巖[5]、大理巖[5]及合成材料如聚氨酯[6]等脆性材料開展了Ⅰ型、Ⅱ型以及Ⅰ-Ⅱ復合型加載時的斷裂韌度研究。Ayatollahi 等[7-8]研究了納米晶體鎂、改性聚合物水泥和大理石等材料的Ⅰ-Ⅱ復合型斷裂特性。Lin等[9-10]采用數字散斑技術研究大理巖和砂巖在Ⅰ型、Ⅱ型以及Ⅰ-Ⅱ復合型加載的裂紋擴展特征,并揭示了其在不同加載條件下的斷裂破壞機理。Xia 等[11-12]開展了花崗巖和大理巖在沖擊載荷下Ⅰ型和Ⅱ型動態斷裂試驗,研究了加載率和圍壓試樣的動態斷裂韌度和裂紋擴展的影響規律。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多集中在準靜態條件下脆性材料的斷裂特性,而對脆性材料在不同加載方式下的動態斷裂特性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而且對煤的Ⅰ型、Ⅱ型以及Ⅰ-Ⅱ復合型動態斷裂的綜合研究更是鮮有報道。此外,Ayatollahi 等[13]提出的ASCB(the asymmetric semi-circular bend)試件加工簡單,試驗穩定性好,且不需要改變試樣預制裂紋的幾何形狀,僅改變底部支撐間距即可實現不同條件下的加載方式。為此采用霍普金森壓桿裝置和數值模擬方法開展了ASCB 煤樣在沖擊載荷下的動態斷裂試驗和模擬,對比分析了煤樣在Ⅰ型、Ⅱ型以及Ⅰ-Ⅱ復合型加載下裂紋演化規律差異特征,并研究了沖擊速度對煤樣在不同加載方式下的起裂時間和破壞形態的影響規律。
1 試驗煤樣和試驗方案與設備
1.1 煤樣制備
試驗所用煤樣取自山西忻州窯礦的11 號煤層,煤樣類型為煙煤,煤樣物理力學性質見表1。在現場取回的完整大塊煤樣中,順著層理面鉆取直徑為50 mm 的長圓柱。然后沿著垂直于層理方向將圓柱切割為若干相同厚度為25 mm 的圓盤,再將圓盤沿層理方向切割為2 個半圓,最后在半圓底部中間切割寬度為1 mm,長度為10 mm 的預制切槽,加工完成的ASCB 試樣示意圖如圖1。

表1 煤樣物理力學性質Table 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al samples
1.2 試驗方案與設備

圖1 ASCB 試樣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SCB sample
試驗采用直徑為50 mm 的霍普金森壓桿系統開展動態試驗,試驗設置0.52、0.54 、0.56 MPa 3 種不同發射氣壓,經測速儀測試子彈速度分別為3.3、4.2、5.4 m/s。
根據Ayatollahi 等[13]提出的ASCB 試件,僅通過改變右側支撐間距S2大小即可實現試樣的Ⅰ型、Ⅱ型以及不同程度的Ⅰ-Ⅱ復合型加載。即在S2=S1=20 mm 時為I 型加載,當S2縮小時為Ⅰ-Ⅱ復合型加載,當縮小至YⅠ=0,YⅡ≠0 時(YⅠ和YⅡ分別為Ⅰ型和Ⅱ型無量綱幾何因子),通過ABAQUS 軟件計算得出試驗所用樣品在S2=2.13 mm 時為Ⅱ型加載[14]。為此,制作S1=20 mm,S2=2.13 mm 的底部支座開展了沖擊載荷下煤樣在以上3 種不同沖擊速度下的Ⅱ型動態斷裂試驗,每組速度有3 個試件,試件信息與試驗結果見表2。

表2 試樣信息與試驗結果Table 2 Samples information and test results
試驗時,采用高速攝像機拍攝煤樣的破壞過程,確保高速相機和子彈同時觸發。相機圖像采集速度設置為90 000 fps,即采集到的圖像時間間隔為11 μs。試驗后,通過圖像處理獲取完整的煤樣破壞過程圖,并記錄每個試樣的起裂時間。然后采用數值模擬手段通過對Ⅱ型動態斷裂試驗進行校核驗證后,再開展多種沖擊速度下煤樣的Ⅰ型和Ⅰ-Ⅱ復合型動態斷裂數值模擬研究,充分地研究不同沖擊速度與不同加載方式下煤樣動態斷裂特性。
2 數值模擬
模擬采用基于連續-非連續單元方法(Continuum-discontinuum element method,CDEM)適用于模擬材料在靜、動載荷作用下非連續變形及漸進破壞的數值模擬軟件[15],ASCB 試樣模型網格如圖2。模型為二維模型,共有約6 233 個三角形單元組成,切槽尖端進行加密處理。模型內部由單元和接觸面構成,單元物理力學參數同煤樣實際參數相同,本構模型設置為斷裂能模型[14]。接觸面參數通過對試驗結果中試件破壞形式和裂紋起裂時間校核驗證而得出。

圖2 ASCB 試樣模型網格Fig.2 Model grid of ASCB sample
模擬中對模型底部2 個支座處施加法向位移約束,頂部施加速度載荷來模擬試驗中的沖擊載荷。模擬設置3 種右側支撐間距S2,分別模擬3 種加載方式,即S2=20 mm(I 型加載),S2=6 mm(Ⅰ-Ⅱ復合型加載),S2=2.13 mm(II 型加載)。然后對以上3 種加載方式煤樣模型分別開展沖擊速度為1~8 m/s 的8 種動態斷裂模擬。
3 試驗與模擬結果
3.1 煤樣動態斷裂破壞過程
II 型加載下數值模型煤樣在4 m/s 沖擊速度下的載荷-時間曲線如圖3。由圖3 可以看出,煤樣同樣和準靜態加載一樣都經過壓密、彈性和屈服破壞階段。

圖3 載荷-時間曲線Fig.3 Load-time curve
為充分研究煤樣在動態加載過程中的裂紋演化特征,以與圖3 曲線中時間點相對應為原則進行加載,煤樣在II 型加載下不同時刻的最大主應力云圖、損傷演化圖分別如圖4、圖5,煤樣在II 型加載下不同時刻的試驗結果圖如圖6。

圖4 煤樣在Ⅱ型加載下不同時刻的最大主應力云圖Fig.4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cloud of coal sample at different times under mode Ⅱloading

圖5 煤樣在Ⅱ型加載下不同時刻的損傷演化圖Fig.5 Damage evolution image of coal sample at different moments under mode Ⅱloading

圖6 煤樣在Ⅱ型加載下不同時刻的試驗結果圖Fig.6 Test results of coal sample at different moments under mode Ⅱloading
由圖4~圖6 可以看出,煤樣在加載初期僅在頂部產生較小應力集中,并未出現損傷;在40 μs 彈性階段,由于非對稱加載,試樣在切槽尖端產生了偏向左上方的“心型”應力集中,但此時并未產生破壞,僅在試件頂端和切槽尖端產生損傷;在50 μs 時,裂紋在切槽尖端向左上方起裂。此外,試件右側支座處在該時刻產生了明顯的應力集中和損傷;在58 μs時,數值模型與對應的試驗結果均在右側支座處發生破壞;在70~88 μs 即在峰值載荷附近,試件切槽尖端主裂紋繼續向左上方擴展至試件頂端,右側支座處裂紋繼續垂直向上擴展;在122 μs 可以看出,試件在峰后階段開始產生試件頂點向下的之裂紋,右側支座處煤塊也發生了剝離,試件更加破碎,直至試件的最終破壞。
在4 m/s 沖擊速度下煤樣在Ⅰ型和Ⅰ-II 復合型加載下不同時刻的最大主應力云圖如圖7。由圖7可以看出,煤樣在Ⅰ-Ⅱ復合型加載下的裂紋演化特征同Ⅱ型加載相似,都是由于非對稱加載導致切槽尖端發生偏向左上方的應力集中,最后致使裂紋向左上方擴展至試件頂端。同樣在右側支座處發生劈裂破壞,不同的是起裂角小于Ⅱ型加載條件下的裂紋起裂角。而I 型加載由于加載對稱,在切槽尖端形成對稱的“心型”應力集中區,最終發生沿試件中心線的張拉型破壞。
3.2 沖擊速度對裂紋起裂時間的影響
由于在試驗和數值模擬結果中均可發現,煤樣在3 種加載方式下,裂紋均從切槽尖端起裂,且在Ⅱ型和Ⅰ-Ⅱ復合型加載條件下裂紋為曲線形式,不便于研究裂紋擴展速度。此外,試驗中子彈沖擊速度約束很大,即發射氣壓過小,不足以將子彈發射出;發射氣壓過大具有操作危險性。為此,在3 種沖擊速度基礎上,又開展了3 種加載方式下沖擊速度為1~8 m/s 的8 種動態斷裂模擬,來研究沖擊速度對不同加載方式的裂紋起裂時間與破壞形式的影響規律。不同沖擊速度下煤樣的起裂時間如圖8。

圖7 煤樣在Ⅰ型和Ⅰ-Ⅱ復合型加載下不同時刻的最大主應力云圖Fig.7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of coal samples under mode Ⅰand mixed mode Ⅰ-Ⅱloading at different times

圖8 不同沖擊速度下煤樣的起裂時間Fig.8 Crack initiation time of coal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impact velocities
由圖8 可以看出,試驗中Ⅱ型加載下煤樣在沖擊速度為3.3~5.4 m/s,裂紋起裂時間分布在55~80 μs,隨沖擊速度的增大而減小。這是由于相同時間內,沖擊速度越大,試樣所吸收的彈性能就越大,就越容易更早發生破壞。此外,可以看出:模擬結果和試驗結果大致吻合,稍有偏差。可能由于試驗中相機拍攝圖片間隔11 μs 的精度問題和裂紋起裂時刻肉眼難以判斷等原因導致,而數值模擬手段則可準確確定裂紋的起裂時刻。
3 種加載方式的模擬結果均與試驗結果相似,即裂紋起裂時間均隨沖擊速度的增大而減小,表明模擬結果的可靠性。可以發現裂紋起裂時間在沖擊速度低于3 m/s 情況下,受沖擊速度影響較大。而后隨沖擊速度的增大影響逐漸減小,最終趨于緩和。表明煤樣在3 種加載方式下的裂紋起裂時間都不會隨沖擊速度的增大無限減小,而是趨于一個定值。在模擬中也發現,當沖擊速度過大時,由于頂端應力過于集中,裂紋在煤樣頂端最先起裂,這已不符合試樣的斷裂測試原則。
對3 種加載方式下的模擬結果進行曲線擬合,擬合公式如下:

式中:tⅠ、tⅠ-Ⅱ、tⅡ分別為Ⅰ型、Ⅰ-Ⅱ復合型、Ⅱ型加載下的起裂時間,μs;v 為沖擊速度,m/s。
對起裂時間求極限,可以得出沖擊速度為無限大時Ⅰ型、Ⅰ-Ⅱ復合型和Ⅱ型加載下的裂紋起裂時間分別為43.2、45.6、52.2 μs,Ⅱ型加載裂紋起裂時間最長,可能由于Ⅰ型Ⅰ-Ⅱ復合型加載試樣承受載荷都有拉伸載荷,而Ⅱ型加載承受載荷為純剪切載荷,導致其試樣較難發生破壞。同樣可以發現,Ⅱ型加載裂紋起裂時間在所有沖擊速度下均大于其他兩者。而Ⅰ型和Ⅰ-Ⅱ復合型加載在相同沖擊速度下的裂紋起裂時間大致相同,沖擊速度小于4 m/s時,Ⅰ型加載裂紋起裂時間較大;沖擊速度大于4 m/s 時,Ⅰ型加載裂紋起裂時間較小。
3.3 沖擊速度對煤樣破壞形式的影響
Ⅱ型加載條件下煤樣在不同沖擊速度下的破壞形式如圖9。3 種加載方式下煤樣在不同沖擊速度下破壞形式的模擬結果如圖10。
由圖9 可以看出,不同沖擊速度下煤樣均產生了切槽尖端起裂向左上方擴展的主裂紋和右側支座處的劈裂裂紋,而后又產生了頂點向下的之裂紋和右半部分橫向之裂紋。但是由于煤樣的非均質性和試驗沖擊速度范圍較小的原因,試驗沖擊速度對煤樣破壞形式的影響不太明顯。因此,選取了典型的數值模擬結果來研究沖擊速度對破壞形式的影響規律。

圖9 不同沖擊速度下煤樣的破壞形式Fig.9 Failure modes of coal samples at different impact velocities
從圖10 可以看出,隨沖擊速度的增大,煤樣的破壞程度逐漸變大。對于Ⅰ型加載,煤樣由于承受對稱的拉伸載荷,裂紋基本呈直線形式,裂紋較為穩定,受沖擊速度影響最小,僅在沖擊速度較大7 m/s時產生底部和頂部的之裂紋。而對于Ⅰ-Ⅱ復合型和Ⅱ型加載,煤樣裂紋則受沖擊速度影響較大。不難發現,兩者在沖擊速度較小時僅分布有切槽尖端起裂的主裂紋和右側支座處的劈裂裂紋。而在沖擊速度較大時,還產生了頂端向下連接右支座的劈裂裂紋和其他橫向裂紋。

圖10 煤樣在不同沖擊速度下破壞形式的模擬結果Fig.10 Simulation results of coal samples failure at different impact velocities
4 結 論
1)煤樣在Ⅰ型動態加載下,裂紋呈穩定的直線形式;在Ⅰ-Ⅱ復合型和Ⅱ型加載下,由于承受非對稱加載,煤樣裂紋形式為切槽尖端向左上方起裂并擴展的曲線形式,不同于Ⅰ型動態加載和準靜態加載,其在右側支座處也產生了向上的劈裂破壞。
2)在3 種不同加載方式下,煤樣裂紋起裂時間均隨沖擊速度的增大而減小,但其影響逐漸減小。煤樣在Ⅱ型加載下由于承受純剪切載荷,起裂時間明顯大于其他2 種加載方式。
3)煤樣在3 種不同加載方式下的破壞程度均隨沖擊速度的增大而加大,其中Ⅰ型加載影響較小,Ⅰ-Ⅱ復合型和Ⅱ型加載影響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