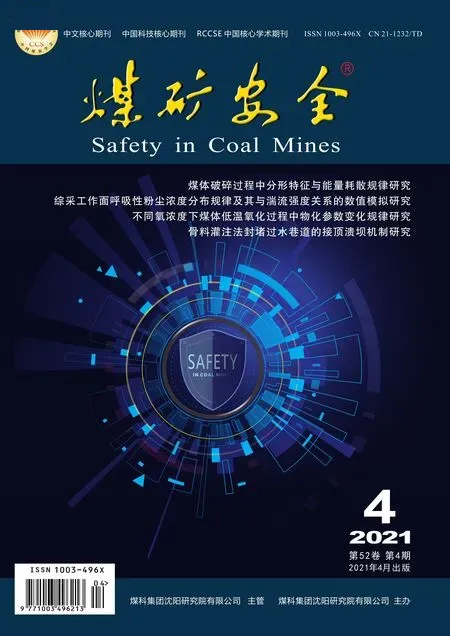骨料灌注法封堵過水巷道的接頂潰壩機制研究
牟 林
(1.煤炭科學研究總院,北京100013;2.中煤科工集團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陜西 西安710054;3.陜西省煤礦水害防治技術重點實驗室,陜西 西安710054)
煤礦發生突水淹井事故后,采用骨料灌注法實施截流堵巷是礦井突水災害治理的重要手段。截流過程分2 個階段,即骨料灌注階段和注漿截流階段,前者為整個治理階段的重點和難點。
何思源[1]等在1984 年范各莊特大突水事故治理中設計了骨料快速灌注系統和連續造漿灌注系統,研發了孔內投放速凝水泥包的裝置。王則才[2]結合2002 年國家莊煤礦突水治理經驗,提出當鉆孔漏失量小時以單液漿為主,當孔內暢通跑漿嚴重時,以注骨料和雙液漿為主的注漿工藝。南生輝、蔣勤明、劉建功等[3-4]結合2003 年東龐礦特大突水災害的注漿治理經過提出了旋噴注漿、充填注漿、升壓注漿、引流注漿4 個關鍵技術階段。劉生優、邵紅旗等[5]結合2010 年駱駝山煤礦特大突水淹井水害治理情況,提出了在接近靜水條件下骨料灌注效率低時,可采用雙液漿法快速建造阻水體骨架,再采用綜合注漿法灌注水泥漿液加固墻體,取得了優良的堵水效果。岳衛振[6]通過黃沙礦截流堵水經驗,在巷道煤巖強度低導致截流段反復沖潰的情況下,提出了采用壓力平衡法改善水閘墻兩側受力條件進行水害治理。
在定性研究層面,為了研究骨料灌注過程,李維欣[7]、惠爽[8]設計了多孔灌注可視化試驗模型,對骨料截流過程中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從現象角度研究了低流速條件下細粒骨料灌注截流過程。
在定量研究層面,針對骨料堆積、接頂、潰壩等機理層面的研究未見相關報道。骨料在水流中的運移過程,本質上為固-液兩相流耦合問題,近年來采用計算流體動力學和離散單元法相結合求解兩相流問題的方法已受到廣泛關注(簡稱CFD-DEM)。骨料灌注過程屬于流化床問題,景路等[9]模擬了水下滑坡坍塌過程,較好地描述了海底邊坡的失穩、流動和堆積過程;劉卡等[10]分析了水下拋石初始速度、拋石粒徑、拋石密度因素對水下拋石運動規律的影響;蘇東升[11]模擬了泥沙沉降、明渠水流泥沙運動過程,研究了流體運動特征及顆粒遷移分布形式;邵兵等[12]對大粒徑的、非常規巖屑顆粒在水平井段的運移規律進行了模擬,得出了顆粒形狀對鉆井液攜巖效果的影響。為研究動水巷道中骨料接頂、潰壩現象及內在發生機制,采用CFD-DEM 數值方法對典型工況下骨料灌注過程進行動態、定量計算研究。
1 單孔連續灌注實驗研究
1.1 基本參數設定
顆粒參數均按如下設定:模擬過程為清水環境,水的密度998.2 kg/m3,運動黏滯系數10-6m2/s,顆粒采用Hertz-Mindlin“軟球”模型,楊氏模量為5×106N/m2,泊松比0.3,恢復系數0.3,滑動摩擦系數0.1,顆粒密度2 650 kg/m3。
1.2 靜水灌注實驗
骨料在靜水條件下的堆積狀態如圖1。現場施工中所灌注骨料粒徑大多集中在5~50 mm 顆之間,將其分為3 個主要的粒徑區間:5~10、10~30、30~50 mm,假定每個粒徑區間的顆粒級配曲線呈線性分布。在靜水條件下,采用相同的灌注速率向3 個相鄰區域分別灌注不同粒徑的骨料,發現水下骨料堆積角與天然堆積角接近,在灌注到一定程度時骨料很快發生接頂,僅能在孔底附近形成有限寬度的堆積體。

圖1 骨料在靜水條件下的堆積狀態Fig.1 Accumulation state of aggregate in hydrostatic water
靜水條件下的進行骨料灌注的目的是在鉆孔之間形成人工圍堰,為后續注漿、防止漿液溢流至注漿范圍之外提供屏障,靜水注漿可采用水泥漿和雙液漿進行充填。所謂靜水條件,一般是指突水發生后,巷道系統內的水位與突水水源的水位標高一致,巷道中的水流流速很小接近靜水狀態。靜水條件下建造阻水墻所需的時間和工程量小,但是不能有效地為搶先復礦爭取時間,僅能起到截流的作用。
1.3 動水灌注實驗
骨料在動水條件下的堆積狀態如圖2。

圖2 骨料在動水條件下的堆積狀態(流速0.9 m/s,灌注速度1 kg/s)Fig.2 Accumulation state of aggregate under hydrodynamic water(velocity of 0.9 m/s, grouting velocity of 1 kg/s)
在一定流速下灌注不同粒徑的顆粒,骨料開始下落后速度逐漸增大(綠色),落底后速度為0(深灰色)。對于5~10 mm 顆粒組,堆積高度增加至一定程度后高度不再增加,而是在長度方向向下游不斷增加,這種情況在10~30、30~50 mm 粒徑組中沒有出現,說明不同粒徑組的啟動速度存在差別。這也說明了細骨料適用于現場灌注的鋪底過程,而粗骨料適用于接頂過程中的大流速環境。
2 多孔灌注截流接頂過程
2.1 小流量截流實驗
小流量多孔灌注實驗如圖3。

圖3 小流量多孔灌注實驗(5~10 mm,流速0.3 m/s)Fig.3 Multi hole combined grouting under low flow(5-10 mm, velicity of 0.3 m/s)
當突水量較小時(0.6 m/s 以下),采用5~10 mm細骨料進行灌注,堆積體能以較快的速度達到接頂狀態。堆積體向巷道下游運動生長的趨勢很弱,最終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堆積。受限于第1 個堆積體的阻水升壓效應,巷道內的流量進一步降低,后續第2 個、第3 個鉆孔的堆積形態幾乎與靜水形態完全一樣。流量小的情況下堆積體之間會殘余較大的未充填區域,只能通過后續注漿充填。
2.2 大流量截流實驗
大流量多孔灌注實驗如圖4。當流速較大達到0.6~1 m/s 以上時,骨料的運動狀態開始發生明顯變化。t=100 s 之前為細骨料鋪底階段,100~200 s 之間為粗骨料充填階段,200 s 之后為混合骨料接頂階段。在鋪底階段,鉆孔之間的骨料堆積長度會逐漸變長直至相互搭接為一體,搭接后下游的高度相應增加直至與流場形成新的平衡狀態。充填階段需要適當增加粒徑以適應更高的流速環境,使堆積高度和堆積長度同步增長。進入接頂階段后,需要反復調整骨料粒徑,粗細搭配直至成功接頂。流速較高的區域以彩色顯示,滯留或者緩慢運動的顆粒以灰色顯示,同等灌注條件下下游鉆孔相對容易接頂,已接頂的區域會逐漸向上游逆勢生長直至全段接頂。
3 堆積段接頂-潰壩的力學機制
3.1 顆粒拱效應分析
散體材料拱效應示意圖如圖5。顆粒拱效應又稱土拱效應,最早可以追溯到1884 年,由英國學者Roberts 首次發現“糧倉效應”:當糧倉中糧食達到一定高度后,糧倉底部的最大應力值不再隨堆積高度發生變化。隨著糧食高度的增加,糧倉墻體與糧食之間的摩擦力不斷增加。在糧倉壁面摩擦力的作用下,主應力發生偏轉傳遞到墻體上,這種現象即“糧倉效應”,內涵與土拱效應一致,顆粒拱尺寸由幾厘米到幾米不等。

圖4 大流量多孔灌注實驗(初始流速1 m/s,0.4~1 kg/s,5~50 mm)Fig.4 Multi-hole combined grouting under high flow(initial velocity of 1 m/s, 0.4-1 kg/s, 5-50 mm)

圖5 散體材料拱效應示意圖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arch effect of bulk materials
候明勛[13]將光彈實驗應用于研究了巖土顆粒材料的離散特性導致的“應力網格”及“拱效應”特性。結合顆粒間力鏈分布形態定義了應力拱的概念,直觀展示了強力鏈和弱力鏈的相互關系,證明了顆粒材料間的架拱效應,驗證了土顆粒應力拱效應產生條件:①顆粒之間產生不均勻位移或相對位移;②存在作為拱受力的支撐點。顆粒間力鏈的存在直觀描述了骨料接頂堵塞通道時的受力狀態。
顆粒材料中的應力拱效應是材料本身的自發現象,在邊界條件、自重或外力載荷作用下,顆粒材料發生變形壓縮,當顆粒體系的邊界條件不一致時,可將產生不均勻位移,以致顆粒間產生相互“楔緊”的作用,這樣在一定的范圍內就產生了土顆粒應力拱效應。土拱效應不僅存在于垂直方向,水平方向也存在,合理利用其存在條件,可最大限度發揮材料自身的抗剪能力,增加系統穩定性。
接頂區粗骨料的成拱效應示意圖如圖6。當骨料顆粒伴隨高速水流在頂部殘余過水通道之間運動時,由于巷道和底部砂體的起伏及自身糙度影響,通道中總存在一些寬度變窄“楔形”區域。在這些區域粗骨料在慣性力作用下以簡單塊體或復合性塊體形式楔入其中形成一夫當關的“楔鎖”結構,之后沖刷而來的骨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排列、旋轉、咬合形成臨時性的顆粒拱。顆粒拱之間的其他顆粒則處于自由狀態,顆粒拱的形成可有效阻擋這些自由顆粒發生進一步運移,防止細顆粒流失。在粗骨架和細顆粒的復合作用下,拱效應影響區最終形成了具有一定抗載荷能力和抗滲能力的復合結構。當這種結構的規模達到一定程度連成整體時,成功接頂成為可能。

圖6 接頂區粗骨料的成拱效應示意圖Fig.6 Arching effect of coarse aggregate in top joint area
3.2 顆粒拱結構的剪切-失穩模型
顆粒拱結構的存在為接頂區阻塞過水通道提供了力學模型,顆粒拱系統提供的有效阻力越大,穩定性儲備越高,越能阻抗更大的流速。決定骨架穩定性的因素包括骨料顆粒的參數和邊界條件。骨料參數主要包括粒徑、級配、形狀和密實程度,理想的骨料參數有利于在水平方向形成穩定的抗剪力,使系統破壞時不至于從骨料內部發生剪切破壞。骨料所處位置巷道頂板及側幫是天然邊界,底部的細骨料是人工邊界。
對于天然邊界,影響其對顆粒拱作用特征的因素包括巷道糙度和力學強度。巷道糙度包括各類凸起或凹陷的深度、形狀、出現頻率等,主要與巖體的節理、采掘方式、應力條件及支護方式有關。巷道糙度越小,起伏越小,其提供的水平抗剪力越小。天然邊界處的巖土體在泡水軟化、顆粒沖刷擠壓后發生變形失穩,最終導致顆粒拱從該區域“潰壩”失穩,此情況主要發生在飽和強度低的軟弱煤巖巷道中。
人工邊界是指骨料堆積過程中形成的堆積體頂界面,頂界面的狀態直接決定了后期接頂的難度。如果前期骨料灌注中,急于追求施工進度,導致鉆孔間存在較多未充填的空間,則殘余過水通道總體狀態不穩定,近鉆孔窄而中間變寬,導致顆粒拱形成的概率和穩定性大打折扣,降低了接頂的效率和降壓阻水效果。因此前期灌注過程中需要盡可能的使骨料以近水平狀態鋪滿巷道空間,減少接頂期間潰壩失穩的概率。
3.3 堆積體顆粒的滲透-失穩模型
堆積段內細骨料遷移及滲流失穩現象如圖7。

圖7 堆積段內細骨料遷移及滲流失穩現象Fig.7 Migration and seepage instability of fine aggregate in accumulation section
在堆積體多次瞬時接頂之后,通過不斷調整灌注配比,可間歇性的形成相對穩定的接頂狀態。此時粗顆粒骨架與可流動細顆粒的力學狀態存在顯著差異,尤其在頂部最薄弱的區域。粗顆粒骨架承擔了主要力的載荷,細顆粒主要起到改善粗骨料的應力平衡狀態、降低孔隙率和提高水流阻力的作用。然而在施工過程中,由于骨料的堆積狀態、級配狀態、巷道糙度條件、堆積長度、流速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即使接頂后堆積體依然存在“潰壩”的風險,但此時的“潰壩”機制與初期的剪切-失穩模型存在明顯區別。
這種因高速滲流導致堆積體中細顆粒大量流失引起的失穩現象,屬于工程地質學中的“管涌”范疇。管涌是指在水流作用下,骨架空隙中的細顆粒隨著流速增大引起細顆粒被沖刷帶走的現象。涌水口徑從幾厘米到幾米不等,突水口周圍多形成隆起沙環[14],常見的管涌現象如圖8[15]。

圖8 常見的管涌現象Fig.8 Common piping phenomenon
管涌概念常用于壩基、河堤防滲抗災領域,管涌導致無黏性土體失穩原因主要有[16]:①土中粗顆粒所構成的孔隙直徑必須大于細顆粒直徑;②滲透力能夠驅動細顆粒在孔隙間移動。
張剛[17]研究了采用不同粒徑砂組成的砂體在水頭作用下的管涌發展規律,不均勻系數(D60/D10)與臨界水力梯度的關系如圖9,不同級配下水力梯度與滲透系數相互關系曲線如圖10。

圖9 不均勻系數(D60/D10)與臨界水力梯度的關系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omogeneous coefficient and critical hydraulic gradient

圖10 不同級配下水力梯度與滲透系數相互關系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hydraulic gradient and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under different gradations
采用了5~10 mm 粗骨料構成骨架顆粒,0.075~2、0.5~1、0.25~0.5 mm 3 種粒徑的標準砂配制可流動細顆粒,通過研究發現:①骨料的最大流流失粒徑與細顆粒的級配有關系,細顆粒含量在25%~33%區間時,發生細顆粒流失最少,發生管涌的概率最低;②臨界水力梯度為0.26~0.42,骨料不均勻系數越大,臨界水力梯度越低[18];③低于臨界水力梯度時,滲透系數不變為層流,超過臨界水力梯度時滲透系數快速增長,發生潰變可增大3~6 倍以上。該文研究的骨料粒徑范圍、物理模型與本文骨料接頂后堆積體的滲流模型條件相吻合,對解釋骨料堆積段發生“管涌”形式潰變過程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由此可見,即使骨料接頂之后,如果水力梯度超過骨料所能承受的極限,作為薄弱區的頂部區間,仍存在“潰壩”失穩的可能性,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經歷相對穩定的接頂時間后,又突然轉為潰壩的情形。管涌導致潰壩是骨料中水流由低速滲流向高速滲流、管道流逐漸演化發生質變的過程,也是細顆粒不斷流失導致顆粒系統潰變失穩的直觀反應。
3.4 失穩潰壩后的運動形式
將模型巷道中預先用5~50 mm 的混合顆粒充填滿,按0.3、0.5、0.8 m/s 的水流流速進行測試。結果發現在較低流速時,顆粒能夠原地保持穩定,當速度逐漸達到0.8 m/s 時,堆積體上部一定厚度范圍的顆粒發生整體遷移,細顆粒優先運動,隨后粗顆粒伴隨這細顆粒的流失逐漸暴露于流場之中,最終大量流失,此時骨料顆粒呈現出流化床的運動特征,隨著時間的推移頂部被沖刷帶走的顆粒越來越多,如不及時注漿加固則會造成貫通性潰壩導致截流失敗。管涌突破后殘余通道內的骨料整體運動如圖11。

圖11 管涌突破后殘余通道內骨料整體運動Fig.11 Aggregate movement in residual channel after piping breakthrough
4 截流堵水工程案例
大型截流堵巷工程案例施工數據統計見表1。
靜水條件下截流工程量主要與施工方案有關系。如申家莊礦和桃園礦為了兼顧巷道充填和后續陷落柱的治理,截流采用了灌注純水泥漿的方案,注漿量分別達到了4.5 和6.1 萬t。駱駝山礦在截流時針對骨料灌注效率低的情況,采用雙液漿法在阻水段兩端快速形成阻水骨架,進而為后續充填注漿創造了有利條件,有效降低了無效跑漿工程量,注漿量僅為6 500 t。唐家會礦則采用了改進的防噴孔骨料灌注工藝,在靜水條件下實現了較大的骨料灌注量(2 060 m3,約130 m),注漿量僅為1 萬t。

表1 大型截流堵巷工程案例施工數據統計表Table 1 Construction data of roadway blocking projects
動水條件下截流堵水,與靜水條件相比存在顯著差異,骨料在動水中被攜帶搬運至下游,巷道中存在大量不能有效接頂的無效堆積區域。骨料灌注過程中可能不斷發生接頂、潰壩事件,需反復灌注直至成功截流。骨料灌注期間井下涌水量變化曲線圖如圖12。由圖12(a)可以看出,骨料灌注期間水量相對穩定,至截流成功后沒有反彈情況出現,由圖12(b)可以看出,情況則相反,灌注期間出現多次潰壩后才成功截流,這主要與技術條件的變化有密切關系。

圖12 骨料灌注期間井下涌水量變化曲線圖Fig.12 Variation curves of underground water inflow during aggregate pouring
5 結 語
1)采用CFD-EDEM 兩相流耦合計算模型,分別在靜水和動水條件下進行了單孔連續灌注試驗,得出了2 種條件下骨料堆積形態的差異性,驗證了細骨料更適用于搬運和鋪底過程。
2)通過多孔灌注試驗模擬了骨料接頂過程,實驗表明流量小時搬運能力弱,鉆孔之間存在大量未充填區域,大流量條件下骨料會根據流場條件發生不同程度的水平生長直至孔間接龍,下游鉆孔優先于上游孔接頂,接頂區逆勢向上游生長至全段接頂。
3)引入顆粒拱模型分析了骨料隨機接頂的力學機制,提出了骨架的剪切失穩模型,從細顆粒流失導致潰壩的角度進一步引入管涌概念解釋了潰壩機制,最后分析了潰壩過程中骨料的運移形式。
4)結合工程案例驗證了靜水和動水截流在施工上的差異性,指出動水截流過程中剩余過水量作為主要指標判別截流成功與否存在不確定性,該過程可能需要經歷多次反復才能最終成功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