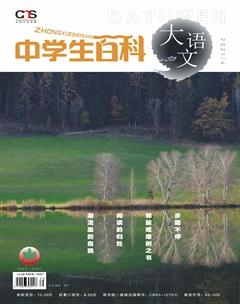魏晉風度與潮流引領
目田君
從現代往前看,每朝每代,都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如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秦漢時期的儒法融合、初唐的盛世氣象與邊塞情結、宋代的理學風潮、明代的士大夫文化。“弄潮兒向濤頭立”,時代的潮流各有不同,但談古代引領潮流的典范,就不可不談魏晉南北朝的那些名士。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動蕩,戰爭頻發。與承平日久的年代不同,這個時代的人們都有一種慷慨悲涼和世事無常之感,于是形成了一種魏晉多名士,好談玄、服藥、飲酒的風氣。這一塊,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里面就談到了,他提及何晏是服藥的祖師,常服用“五石散”。吃了這五石散,身體發熱,需要走路行散,于是留下了“散步”這一名詞。很多人也跟著服藥,就是不服藥的人,也效仿這些名士,裝作發散。吃藥之后,皮膚容易磨破,于是要著寬衣、穿木屐。因為這些人活躍于正始年間,被稱為正始名士。另一個團體,就是我們熟知的“竹林七賢”,包括阮籍、嵇康等人。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世說新語》中記載了很多關于正始、竹林時期的名士軼聞,一時風頭無兩。
在魏時,原來的東漢儒家經學已經神學化,很多人對讖緯化、神學化的經學心生反感,由是開始了玄談,閱讀《周易》《老子》《莊子》,由儒入玄。自正始名士開始談玄,以道釋儒學,引來很多人效仿,當時社會風氣以談玄為佳話。西晉王衍、東晉殷浩就是其中談玄的翹楚。據說王衍氣宇不凡,好談玄理,但言談時常常有自相矛盾處,被人們稱為“口中雌黃”(雌黃是當時涂在紙上修改文章的用具)。而殷浩在《世說新語》中有多個清談軼事:有一次另一位玄學名士孫安國到殷浩家清談,兩人來回辯駁,旁邊的飯菜也顧不上吃,飯菜涼了又熱,熱了又涼,來來回回好幾遍,手上所持的拂塵(清談時需要持拂塵)被兩人清談甩動,拂塵上的毛落滿了飯菜。又一次殷浩去拜訪當時的丞相王導,王導召集了當時諸多高官,并且親自和殷浩清談。雙方談完,已是三更,而周圍的人都還聽得如癡如醉。清談潮流,可見一斑。
而談及王導,此人是東晉的丞相,“王與馬,共天下”中的“王”,東晉門閥政治的實際開創者,也是瑯玡王氏的名士。據《晉書·王導傳》記述,東晉內憂外患不斷,先有王敦之亂,后發生蘇峻之亂,弄得朝廷元氣大傷,財政困難,要靠變賣庫存物資來維持運轉。而庫存只有數千匹粗絲織成的布,叫作“”。這些也賣不出多少錢來。于是王導親自領著一批名士,用這些粗絲布做成單衣,集體穿著,一時間引起士人爭相效仿,布價格飆升。
與王氏合稱“王謝”的謝氏家族,也是高士輩出:謝鯤、謝安、謝玄。但論及潮流影響,都比不過他們的孫輩謝靈運。后世有載:“凡衣服器用,(謝靈運)一有制作,世共宗之。”可以說影響力極大。史載他發明了一種登山用的鞋:“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后齒。”后世稱為“謝公屐”,李白也在《夢游天姥吟留別》里寫道:“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
魏晉南北朝名士層出,不可勝數,但說到底,魏晉名士談玄、服藥、行為放蕩,“越名教而任自然”,源于社會的動蕩和變革。魏晉之際,正是華夏南北民族大融合之時,是豪族、門閥走向最高峰而后衰落之時,所謂“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最后歷史的出路在北朝,終究是陳寅恪語“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雖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