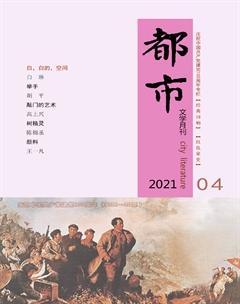《青春萬歲》的“五條金線”
劉照華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
讓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
和幸福的瓔珞,編織你們。
……
讀罷王蒙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這些句子是必定會留存于心里了。好一個“編織”啊!這是對那激動人心的時代最有力的呼應——生逢其時,青春就要蓬勃綻放。
作品描寫的是新中國成立不久,1952年至1953年北京女七中高三畢業班同學的成長故事,而這部小說的創作就開始于1953年。當時作者王蒙19歲,他已經感覺到“勝利的高潮,紅旗與秧歌、腰鼓的高潮不可能成為日常與永遠”,于是覺得“自己有一個使命,把這一段歷史時期、這一段歷史時期的少年——青年的心史記錄下來”。可以說,小說中講述的,便是在中學生活中陪伴了王蒙的那些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因此,他當然是把所有情感都鮮明地放入其中了。1956年,王蒙發表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引起熱烈反響,這時,《青春萬歲》改完交稿。年方22歲的他,以天才般的寫作實踐著打造經典的理想。這部小說后來改編為電影作品搬上銀幕,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
這部作品貫穿著對青春的闡釋與思考,進行著異彩紛呈的刻畫與表達。你不由得為這青春形象及內涵淋漓盡致的顯現而贊嘆:青春啊青春!你究竟能附著多少美妙的語言啊!究竟幾多描摹,才能將你的奇幻說出啊!
小說從始至終,都是王蒙詩意盎然的講述。細細體味,可以從中找到他編織這部青春歷史的五條金線,分別對應關于青春的五個命題。
之一:青春的“坐標”——一代人的底色
作家王蒙對青春生命的描寫有個扎實的基礎,這就是對時代特征的精準把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們是在1947年下半年進入初中,新中國成立的第三個年頭升入高三。“她們的中學時期,開始于新中國成立前最黑暗的年代,也是人民的斗爭最英勇,最偉大,和終于獲得勝利的年代。那時,她們雖然幼小無知,但是,殘酷的生活和激烈的斗爭,整個舊社會崩潰前夕的動蕩與革命風暴的雄威,遠遠勝過童年的歡樂和漫不經心,在她們的心上刻下了嚴峻的痕跡。”這種社會更迭的巨大反差,深刻影響了這一代中學生的心理基調。
“一九五〇年,學校生活剛剛開始正常,人們瞻望和平幸福的明天,喘出了一口氣。這時,朝鮮戰爭的炮火又驚動了她們……接著是‘三反運動……”而當“社會民主改革運動已經基本上完成,朝鮮戰場上也取得了偉大勝利,建設任務日益提在首位”時,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全面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高潮即將到來。在這種快速前進的時代,“人們來不及去歡迎、吟味和欣賞生活的變化,就被卷到生活的變化中去了”。這火熱的時代、濃縮的生活,鍛造著別樣的青春,構成經典人生。正如小說中班主任袁先生所言:“從來沒有一班,像你們這一班這樣幸福。在你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在你們自己身心迅速成長的時候,也正是我們國家發生大風暴、大變革的時候……”
當“這一年,團中央在紀念五四的指示中號召中學畢業生積極準備考入高等學校”時,當“這一年的五一節,北京的女學生第一次普遍穿上花衣服、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時,這些中學生們是無比幸運地站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門檻上了。她們需要從這里邁出關鍵的一步,走入廣闊的時代社會中。
如此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語境,賦予了她們這一代人專屬的青春坐標。
對于這樣的一代中學生,作家王蒙抓住了他們共同的精神特質,這種特質可以用一個關鍵詞概括,那就是“我們”——“每一天都是青春的無價的節日。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發現,所有的一切,都歸我們所有。藍天是為了覆蓋我們,云霞是為了炫惑我們,大地是為了給我們奔跑,湖河是為了容我們游水,昆蟲雀鳥更是為了和我們共享生命的歡欣。……明天還不快來,時間過得真慢!”這是獲得解放的生命對他們共有的時代的抒情,他們是這個新的國家的主人翁。
正是這樣一代人,當他們夜里看到天安門前為國慶閱兵而練習的大炮、坦克,會情不自禁地說:都是我們的!這樣一句簡單的話,會引起他們深深的共鳴,這是因為他們這“受盡苦難的貧弱國家的新一代,想起祖國正漸漸富強起來,因而十分感動”。這種對“我們”的歸屬感與自豪感,會成就一代青年的“大我”情懷,而這正是邁向崇高的起點。
之二:青春的綻放——燃燒生命的激情
作家王蒙善于刻畫不同人物的青春特質,寫出青春的不同類型,不同狀態,由此呈現了青春的絢麗綻放。
鄭波的青春綻放于與黑暗的斗爭中,“還在上小學的時候,她已經會唱《跌倒算什么,我們骨頭硬》”,當她升入女七中后,在十四歲的年紀便參加了北平地下黨組織所領導的民主青年聯盟,并經歷了國民黨抓捕學校自治會活動分子、學生中的地下黨員被迫轉移、進步同學被嚴密監視的考驗。“有一個短時期,能和北平地下黨取得聯系的,只剩下了初一的盟員鄭波……”北平解放,生活沸騰了。鄭波加入了黨組織,狂熱地激動地工作著,并且,她“似乎沒想到自己要按部就班地讀下書去,而是‘時刻準備著聽候組織的調動。當干部,參軍,下江南或者去朝鮮”。
李春的青春曾經是那么絢爛地綻放。她是升高一年級時,從天津考入北京女七中,加入鄭波、楊薔云中間。她的“帥”勁使楊薔云歡喜,她在新生聯歡會上“唱了一個維吾爾文歌、一段京韻大鼓、一首民謠,這一切使同學們——特別是楊薔云欣賞得要命”。當大家得知李春功課棒,1949年就入了團、當過團總支委員,在《天津日報》上發表過文章……便毫不猶豫選她當學生會執委,李春在全校出了名。
楊薔云身上體現著生命熱情的自然流淌,可謂青春原生態的代言人。她熱情、友善——“沒有通常的所謂‘美……但是在她的臉上,目光里,卻像是擁有照耀一切人的光亮”;她單純、快樂——“你盡情地享受生活,就像大小姐享受她家里無盡的財富似的……”;她敏感、外向——“當我看著睡下了的帳篷,還有這清明的天空和滿池的荷葉,我想起我們的暑假,想起你的已經過去了的,和我的正在其中的中學時代,幸福就好像從四面八方飛來,而我禁不住流淚……”她積極、樂觀——“我覺得一切都近極了,生活就像縛在噴氣式飛機上,一日萬里。……明年就實行五年計劃,說不定,不久,一覺醒來,周圍已經是社會主義——鄉村里的發電站也建立起來了。”在王蒙筆下,楊薔云是一個描寫得非常豐滿的形象,“她勇敢,所以容易正確,當然也容易錯,但錯了也容易改”,與此同時,在全班五十二名同學中,她是最有朋友緣的人,她像自然舒展地綻放著的清香花朵,釋放著感染力、親和力。另一方面,她知無不言,愛憎分明,比如,在發現李春自私、驕傲、自高自大等缺點后,楊薔云將對李春的批評記在日記本上:“我算認識李春的‘真面目了,她騙取了我的友誼!”而那之后,她與鄭波并肩負起了糾正、幫助李春的責任。
在小說中,這三個人物的友誼和斗爭形成了起伏,演繹著甜甜澀澀的青春故事。
之三:青春的淬煉——踏過“痛點”與“拐點”
如前所指,殘酷的生活和激烈的斗爭,在這些女中學生的心上刻下了嚴峻的痕跡,小說中,鄭波、李春、蘇寧、呼瑪麗都是受過精神傷痛的青年。
鄭波十一歲時,她的小職員父親被“盟軍”的吉普車撞死在雪地里,“喝醉了酒駕車逆行的美國司機,轉了個彎,喊了聲‘OK跑掉了……”母親帶著她寄人籬下,受氣挨餓,苦苦掙扎,直到她結識了女七中高中學生黃麗程,開始接觸進步活動,在斗爭中成長起來。在她身上,直接體現著時代和社會前進對青年生命的鍛造。正是在參加反抗黑暗、建設光明的革命斗爭中,鄭波發現了生活的希望、生命的價值,她的目光超越了自我,超越了家庭局限,將熱情的生命投入到為國家、為大眾的事業中。
少年時代的傷痛刺激了鄭波的成長,然而,一個新的矛盾也必然地出現了,成為她青春的“痛點”。因為在解放之初,“在接連緊張的運動里,鄭波和其他學生中的優秀分子習慣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生活:晚上不自習而去聽大報告,課外活動時間召開各種會議”,而當中學生們“站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門檻上”時,鄭波發現,正如校長所言,“今后的要求不同了,不學好功課,那么一切都談不到……問題就是這樣尖銳地擺著;或者大家趕上去,把政治工作和精通科學結合起來,或者落在后邊,變成空頭政治家……”為鼓勵廣大同學努力學習,校務委員會決定為上學期成績優秀的同學頒發獎章,作為“功課差勁的‘先進同學”,鄭波落榜了,她在反思——“這次,在平凡的和主要的學習任務面前,沒有保持住光榮,沒有盡到責任。作為一個團分支書記、共產黨員,往后,她怎么‘動員別人努力學習呢?會不會被看作說空話的‘先進分子呢?”
面對青春的痛點,鄭波的態度是迎難而上,主動克服。于是她經常成為教室里唯一的留守者,可以堅持九個鐘頭攻下一道難題……
與鄭波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李春。
李春出身小地主家庭,但父親早亡、隨母親寄人籬下的經歷與鄭波相似。在母親也棄她而去后,只有四歲年紀的她,受著伯父憐愛與伯母虐待的雙重待遇,然而,環境歷練出她過人的生存能力。她悟出了討好伯父和盡量躲開伯母的生存秘訣,靠著自己的聰明,在無父無母的困難情況下站住了腳。而這種經歷造就了李春“什么都不怕,一切靠自己闖”的觀念,于是她“在冷酷的命運面前,自小東沖西闖,一日不敢稍懈,受過別人沒受過的苦,用過別人沒用過的心機,居然,自己變成了個‘出類拔萃的學生。五年上學免費,三次得獎”。“新中國成立后,她毫不猶豫地從解放頭一天起就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很快就入了團,她相信像她這樣聰明、積極,過去又是‘受壓迫者,現在前途真的‘無限了。”
然而,李春內心深處的自私和個人奮斗的想法,讓她在已成為女七中風云人物的時候栽了跟頭。原本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成為積極分子的她,在1950年12月軍事干部學校向高中學生招生時,卻反復斟酌著自己的前途,內心沖突起來,最終稱病回避了。但是李春不報名真是太扎眼了,大家由此看到了真實的李春——“嚷嚷的時候比誰都積極,干真事就縮回去了”。李春的青春由此出現“拐點”,她覺察到別人的冷淡,便離開了集體,并且將原本還有的羞恥心轉成了一種怒意,甚至退出了學生會工作。這之后的李春將個人學習的“出類拔萃”當作了最高追求,“李春鼓起勁,埋頭讀書,她想,咱們賽吧,現在嘰嘰喳喳你們棒,總有一天,你們會羨慕我的!”
小說中,鄭波、李春、楊薔云,這三位主人公之間的故事,構成了“青春的金線”,精妙地詮釋著那個時代的青春狀態。因為李春疏遠集體、轉入狹隘的“個人奮斗”,她們三人的關系出現了大拐點。憑著成績優秀拿到校務委員會頒發的獎章后,李春不僅得意,而且有意對鄭波、楊薔云挑釁、譏諷,以成功者姿態勸鄭波“先自己念好書吧”,勸楊薔云“有工夫多制幾個圖好不好!”告誡全班“什么你選我、我選你呀,談談思想情況呀,你批評我、我批評你呀,申請入黨呀——還遠著呢,——往后擱一擱,不礙事。”她甚至公開以一種個人功利主義的思想,議論人民英雄是幸運還是倒霉。直至有一次,她把同學吳長福打扮起來逗樂取笑,并大聲宣布是“肥豬舞”,由此暴露了對同學的輕視與冷漠,再一次成為集體的對立面,遭到大家批評,在這場風波中,李春與鄭波、楊薔云形成尖銳對立,沖突達到最高級。
小說于沖突的發展中,完成了對李春青春問題的診斷,找到了她內心遠離同學、遠離集體的癥結——“終日沉浸在冷靜的計算和個人的進取中,……甚至于,她很少自己對自己講講知心話……”經歷了這樣的“痛點”與“拐點”,李春開始走出小我,走向寬闊——而只有這時,她才與鄭波、楊薔云真正地相遇,真正地開始她們的友誼了。
作家王蒙由此寫出了青春的復雜,也寫出了青春的偉大。
之四:青春的秘語——編織你的心靈
青春像燃燒的一團火,也像飄忽的一片云,變幻不定的面容下,是一顆顆驛動的心。而正是在這種心緒的起伏波動中,完成著一絲一縷的沉淀,完成著青春的自省。
對于這驛動的心情狀態,作家王蒙當年懷著燃燒著的青春之火,作了感同身受的探秘:“新學年把升級的喜悅帶給孩子們,她們高興:仿佛不是由于長大而升了級,倒是由于升級而突然長大了,同時聰明和有力得多了。除了學生,誰能這樣穩如泰山地意識到自己的上升,意識到自己正在逐日地接近那光明閃耀的未來呢?”
是的,享受著這黃金年華的青年們,他們不是從時間本身感受變化,而是在生活的前進變化中感知時間,他們對一切新鮮與陌生抱著迎接的期待,因為他們隨著年齡而上升,實現著“聰明和有力”的過程,一切未知的都是光明閃耀的。這是多么穩如泰山般的富有啊!而正是在這種上升的過程中,甜酸苦辣,五味雜陳,歡樂與傷感,捉摸不定。這是對年輕的心靈的編織,也是對青春的經驗的充實。
愛情是青春的助燃劑,最能激發心靈的感悟。小說中,當楊薔云朦朧地感觸到張世群送來的感情的絲線時,內心翻出從未有過的復雜:“平常,她對周圍的感受是那么多,那么奇妙,那么動人心弦,就像今夜飛跑時閃過的諸種景象,拂過的甜蜜的晚風,和不知從哪兒來的友情,像海水擊打巖石一樣,輕輕敲打著她的心房。但是薔云不知道這究竟是些什么,一切都難以述說和難以形容,當薔云去努力捕捉那些曾經萬分實在地激動了她的秘密的時候,一切卻又像霧一樣地飄走了。”這些文字,將那種初次體驗時興奮而又陌生的感覺完全展開了,明明是真實地觸到了心弦,卻又因未曾嘗試而無從梳理。內心無法平息,而身體的劇烈動蕩恰能沖淡對焦躁的品嘗,正如作家王蒙對楊薔云“青春之跑”的描摹——“她覺得自己那小小的身軀,裝不下那顆不安分的心、那股燒不完的火。于是她往往激動、焦灼,永遠不滿足。而現在的這種超乎尋常的拼命飛跑,卻使她得到片刻的適意和平靜了。”讀著這樣的文字,似乎還能感覺到天才作家王蒙身上散發的青春氣息。關于“青春秘語”的體察,這短短幾句話,勝過一萬句隔靴搔癢的文字。
在這特殊的人生年齡,熱情、友善、助人為樂的楊薔云,開始發生少女情感需求帶來的變化,“不知從哪兒來的一種寂寞感覺壓在薔云心上……她的難過,她的快活,她的熱情比誰都高……她有時候覺得自己對別人的愛簡直多得容不下。她總是瞎操心,窮受累。她整天幫助這個,幫助那個……但是,她告訴自己說:‘我也需要撫愛,需要關切,我也是軟弱的啊。”讀到這里,我們與楊薔云這個人物心靈相通了——她一定是意識到了,熱情以及助人本身并不代表全部的自己,她開始從女性特有的細膩出發,進一步地思考自己人生的價值了。
再如鄭波,在新中國成立后,她入了黨,她激動地工作著,“一邊忙碌,一邊還幻想自己被派到臺灣做地下工作,年齡小好掩護。”然而,這個花季少女身上,青春的甜蜜、浪漫和繽紛色彩似乎無所附著了,隨著和平生活的展開,這種缺失感帶來的煩惱便擾上了她的心頭,她的少女世界需要多加幾條彩線,好好地編織一下了。
在豐富了對生活的感受之后,鄭波意識到了自己青春的不完整。“這些年,我親近了一切人,卻沒有好好地親近自己的媽媽。”她在日記里對自己說:“生活多么美呀,我好像最近才在女七中過活似的。許多東西,也許是小事情,過去從來沒發現過,現在卻特別引起我的興趣。”“白天匆匆地過去了,我覺得自己仿佛比前一天長得高大了些。又微微有些懼怕:難道這一天這樣簡簡單單地過去了嗎?”
青春的秘語雖然無聲,但卻是最深刻地烙上了成長的痕跡。
之五:青春的靈魂——追問崇高與永恒
在鄭波與同學們臨近畢業之際,學姐黃麗程受邀返回母校參加活動,并與當年由她帶入革命斗爭中的鄭波做了心靈共鳴,她指著花朵一樣的少先隊員說:“她們夢想著各種美好的事情,她們很幸福。可我也不羨慕,我們在她們這種年紀的時候,已經嘗夠了生活的苦味兒,已經經受了一些風霜。嚴酷的斗爭使一個人精神上升得很高,雖然我們只做了一點點事情,但是它給我們許多考驗和鍛煉。……要永遠記住我們最初走向革命的時候所受到的教育,使我們不僅是在戰斗中,而且要在和平建設中,不僅在沖突憲兵包圍的時候,而且在燙著頭發的時候,(她撩一撩頭發)都有一樣的火熱的斗志。”
在大學考試結束,人生抉擇擺在眼前時,鄭波告訴好友楊薔云,因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學生數量增長了好幾倍,教員太少了,教育局決定留下少數高中畢業生做初中教師。為此,她放棄大學,同意留下。楊薔云非常吃驚,也為她可惜:“你報的志愿可是橋梁建筑呀!”這時,鄭波給出了振聾發聵的答案:“新中國成立前,我失過學,我知道想念書而沒能念書的孩子聽到學校的鐘聲是什么滋味,我應該去建筑另一種橋梁,孩子們通過它走向文化、科學和覺悟……”
而對于楊薔云的人格成長,小說中同樣有深入靈魂的筆觸,她在愛情失敗的同時,實現著精神的提升——“在張世群告訴她他愛著什么人之后,他們的友誼變得更無私,更純潔,也更美麗了,雖然這種驕傲是以隱約的創痛做代價的;當人們收起了眼淚,靈魂就會變得崇高。”
《青春萬歲》中的女主人公們是楚楚動人的,她們都找到了青春的靈魂,這就是“大我”,就是崇高!而伴著這樣的靈魂,友誼也自會地久天長——“如果幸運地邂逅的那個人恰恰和自己有著同樣的心境、同樣的愛,有著同樣為朋友鞠躬盡瘁的愿望,那么這一切就會成為長久不滅的紀念。”
在故事末尾,鄭波找回了缺失的青春色彩,第一次把留長了的頭發梳成短短的兩個小辮,她的由藍、黃、赭石三種顏色構成的小碎花圖案的襯衫,看來也非常悅目。而楊薔云則宣布:“誓言不改變,實現誓言的人卻要變,她將不再依賴一時的熱情了”,“最主要的是實際干!”
她們的青春日漸豐滿起來,向著崇高,向著永恒。
責任編輯 楊睿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