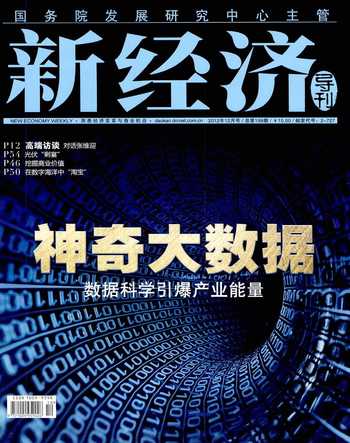光伏如何過冬?
岳敬飛 林坤
有人認為,光伏產(chǎn)業(yè)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首先要歸咎于地方政府。認為光伏產(chǎn)業(yè)是受地方政府的政績推動而盲目擴張,變得畸形,尚德、賽維都如此陷入困境。我認為,不完全是這樣。
以尚德為例,大約在十年前,政府也投了部分資金,那是為了扶持它,但在后來引入風(fēng)投后,政府就退出了。當(dāng)時,政府這么做沒錯,締造了一家在全球范圍有競爭力的新能源企業(yè)。只不過,后來很多小的地方政府(縣級、地級等),看到尚德的成功,或者說無錫的成功,就動了心思,它們很快上馬了大量的光伏項目,造成大量重復(fù)建設(shè),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凡是地方政府推動的光伏細分領(lǐng)域,中國企業(yè)的產(chǎn)能全部嚴(yán)重過剩。
同時,還要看行業(yè)審批有沒有規(guī)則,如果有規(guī)則,要看是不是兌現(xiàn)執(zhí)行了。現(xiàn)在看來,審批部門也有責(zé)任,它們沒有調(diào)控好,沒有按照科學(xué)的方式來批項目。本來地方政府的沖動是可以遏制住的,但有些地方政府跑到部委來要批文,項目就批下來了。有關(guān)部門來審批項目,是不是做到了統(tǒng)籌安排,如果做了統(tǒng)籌安排,大家就不會一窩蜂地上。相比之下,很多發(fā)達國家建設(shè)光伏項目,主要是制造型企業(yè),會考慮環(huán)境污染問題、耗能問題、對就業(yè)拉動的可持續(xù)問題等等,可能批得不多,產(chǎn)能過剩的情況很少。
對光伏的補貼是不是導(dǎo)致光伏產(chǎn)業(yè)危機的原因之一?我不這么看,相反,如果光伏的電對中國的國家能源戰(zhàn)略確實有益,補貼還應(yīng)適度提高。這一行業(yè)只有十年的歷史,各國對光伏都有補貼,只是補貼力度不同,補貼的時間長短不同。目前看來,中國政府在應(yīng)用領(lǐng)域的補貼還是很小的,因為中國的光伏應(yīng)用其實才剛剛開始,一開始就補貼很少,這對于行業(yè)的起步,是不利的。
此外,光伏產(chǎn)業(yè)在技術(shù)方面不存在問題。光伏的產(chǎn)業(yè)鏈很長,從礦石里面提取硅料開始,一直到鑄錠(拉棒)、切片、電池片、組件,最后才是電站。其中,還需要接線盒、切割液、鋼絲繩,玻璃、邊框、整流箱、逆變器等等子行業(yè)加以配套。可以說,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提高,上述各個環(huán)節(jié)的成本都在2012年降到歷史新低,而且這個降價的過程在未來,隨著技術(shù)的進一步提升,是持續(xù)的。同時,實驗室的太陽能電池的能量轉(zhuǎn)化率也在提升。在三五年后,光伏發(fā)電有望在中國的很多地區(qū)接近甚至低于火電的價格,將帶來大規(guī)模推廣光伏應(yīng)用的商機。相對來說,太陽能還是可再生能源,而煤炭、石油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光伏還是有優(yōu)勢的。
目前,光伏產(chǎn)品的消費者,也就是終端應(yīng)用,買組件裝到電站的,還是在國外,國內(nèi)的光伏產(chǎn)品也就只能以出口為主。國內(nèi)不是用不起光伏產(chǎn)品去發(fā)電,而是中國的火電價格相對于歐美國家,顯得太低,光伏發(fā)的電只在電價高昂的局部地區(qū)有競爭力,靠補貼是不夠的。但是情況正逐漸好轉(zhuǎn),結(jié)合“十二五”的能源規(guī)劃,隨著金太陽、分布式電站等政策的刺激,中國2012年的光伏組件裝機量,估計會達到5GW左右,較之2010年,增長500%。后續(xù)國家和地方針對大型地面電站的扶持政策,應(yīng)該會陸續(xù)出臺。2015年,如果充滿想象力,中國的裝機量或許會達到30GW,這是2012年全球一年的裝機量。
光伏產(chǎn)業(yè)是不是受創(chuàng)業(yè)投資資本推動而導(dǎo)致出現(xiàn)現(xiàn)在的困局?我感覺,光伏投資的主體應(yīng)該是產(chǎn)業(yè)資本,比如以前做房地產(chǎn),做礦的企業(yè)和個人,他們對這個行業(yè)的發(fā)展過分樂觀,紛紛進入了這個領(lǐng)域。并不能說是風(fēng)投推動的泡沫,創(chuàng)投不過是錦上添花,因為行業(yè)內(nèi)有風(fēng)投投資的企業(yè)不過九牛一毛。很多硅片廠的投資額動輒數(shù)億美元,而創(chuàng)投這幾年的在光伏領(lǐng)域投資的絕對金額不會超過50億。
中國很多產(chǎn)業(yè)都是這樣被搞壞的。一旦一個行業(yè)有人賺錢了,大家都會去跟風(fēng)、仿效,然后就是產(chǎn)能過剩,行業(yè)就完了。光伏行業(yè)本身門檻不算高,也不低,但很多項目都是通過貸款來完成,因此產(chǎn)品打折賣,它們并不在乎,好像做大了就安全了,但這樣一下就把別人的利潤弄沒了,自己也沒有好日子過了。
現(xiàn)在,全國有幾十個光伏產(chǎn)業(yè)園,不排除其中有很多是真正想發(fā)展光伏產(chǎn)業(yè)的,但其中很多都是以光伏產(chǎn)業(yè)園的名義拿地、圈錢,這是“掛羊頭賣狗肉”。有些地區(qū)沒有任何積淀就這么搞,沒有任何意義,它們的所作所為只能是損人不利己。
我認為,光伏產(chǎn)業(yè)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產(chǎn)能過剩問題,可以說是嚴(yán)重過剩。中國的產(chǎn)品銷售將近占全世界的80%,產(chǎn)能是世界的200%甚至更高。因為統(tǒng)計口徑不同,具體多少很難講。有些地方政府,看到尚德、賽維等企業(yè)火了,為引進企業(yè)也動了心思,比如政策支持、批土地,協(xié)調(diào)銀行貸款等,沒有考慮項目引進之后,技術(shù)是不是有領(lǐng)先的優(yōu)勢,有沒有市場,有沒有客戶,產(chǎn)品出來合格率有多少,產(chǎn)品有沒有口碑,一系列跟銷售有關(guān)的東西怎么弄?
這樣一下子多出這么多產(chǎn)能,怎么辦?企業(yè)只能打折出售。因為大家的利潤率狂降,有些企業(yè)的毛利率都是負的,這樣老外不說你傾銷、補貼才怪。
解決產(chǎn)能過剩問題的方法可以是:把那些中小型、沒有核心競爭力,沒有核心技術(shù)優(yōu)勢的企業(yè)重組淘汰,進行優(yōu)勝劣汰,留下真正有實力的企業(yè)。具體來說,中國光伏產(chǎn)業(yè)要熬過這個難關(guān)方法有二:一是通過行政主導(dǎo),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原來關(guān)閉中小煤礦就是這么干的,中小鋼鐵廠、水泥廠也是,光伏產(chǎn)業(yè)同樣可以這樣;二是,通過市場本身來優(yōu)勝劣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很多企業(yè)扛不住了,很多地區(qū)大批光伏企業(yè)關(guān)門停工,需要關(guān)注的是,這些企業(yè)以后還會不會復(fù)工,如果它們把設(shè)備賣了,把廠房租給別人搞別的產(chǎn)業(yè),說不定行業(yè)就OK了。
光伏產(chǎn)業(yè)跟鋼鐵、造船產(chǎn)業(yè)一樣,走上同樣的產(chǎn)能過剩的老路都是重復(fù)的低附加值的,而沒有高精尖的技術(shù),政策設(shè)計時候就沒有規(guī)劃好。都說中國造船能力很強,其實不是。只能說中國造出噸位很大的用途簡單的船,但實際利潤很低,沒有多少技術(shù)含量,單從需要多少工人上講沒有意義。韓國人造一艘高技術(shù)含量的船的利潤,可能會超過中國人造20艘大的油輪的利潤。因此,今年中國造船企業(yè)很慘,低端產(chǎn)品沒有競爭力,遠洋運輸行業(yè)不好,企業(yè)更難過,很多船廠只能關(guān)了。
松禾在光伏產(chǎn)業(yè)鏈有接觸、布局。我們在光伏產(chǎn)業(yè)上中下游看了很多企業(yè),在北京投資了一個早期項目。它們擁有一項比較優(yōu)秀的技術(shù),我們投的資金不大,有為科技獻身的勇氣在里面。還有一個做接線盒的零部件企業(yè)(通靈電氣),今年相較去年還能實現(xiàn)一定的增長,主要是因為行業(yè)地位靠前,技術(shù)有一定的領(lǐng)先,對客戶的服務(wù)不錯,客戶構(gòu)成還可以,在危機中還在發(fā)展,并新接了不少優(yōu)質(zhì)客戶。
在光伏產(chǎn)業(yè)嚴(yán)峻的形勢下,投資還是有機會的。我們選擇光伏企業(yè),主要的投資標(biāo)準(zhǔn)是:首先看它是做什么的,組件、電池片這一類的我們現(xiàn)在肯定是不投的;然后看這個團隊是不是優(yōu)秀、技術(shù)是不是領(lǐng)先、行業(yè)地位是不是前三名,這家企業(yè)的老板有沒有遠大的抱負、創(chuàng)始人是穩(wěn)健型的還是激進型的。不是說激進好,或者穩(wěn)健好,我們更親睞面對機遇該出手時就出手的企業(yè)家,也喜歡面對危險能抵制住誘惑的企業(yè)家。你比如說,現(xiàn)在國內(nèi)的光伏電站領(lǐng)域,就需要果敢的企業(yè)家去開疆辟土,而不能固步自封,否則很快會被別人超越。
對于光伏企業(yè)的過冬準(zhǔn)備,我想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首先,要提高技術(shù),降低成本,這是行業(yè)大勢所趨;其次,對客戶要慎重選擇,可以選擇付款條件相對好點的客戶,要會甄別客戶實力,不要盲目去接新的單子,防止發(fā)生壞賬。同時,要把現(xiàn)金流安排好,確保后繼有力。松禾也在與被投公司一起面對行業(yè)變幻,我們理解企業(yè)家面對的局面,也會受邀參與重大決策,其實主要是幫助提供參考意見。
綜合外部環(huán)境、行業(yè)現(xiàn)狀、政策措施等,我認為行業(yè)一定是有機會的。因為核能利用或許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風(fēng)電自身的種種弊端,比如安裝維修太花錢,再比如夜里發(fā)電多,大量用戶卻是白天用電,這些問題導(dǎo)致風(fēng)電也不一定能成為主流;生物質(zhì)能又受制于原材料的采集。再有,雖然美國人頁巖氣革命搞得不錯,但中國頁巖氣面臨難題。而我們在光伏產(chǎn)業(yè)有一定基礎(chǔ),如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國內(nèi)的光伏應(yīng)用做起來,技術(shù)提高把每度光伏電的成本再降低一些,行業(yè)還是有前景的。
總之,我們希望國內(nèi)市場能夠發(fā)展起來,希望政府能夠從比較長遠的角度來考慮,能夠多關(guān)注光伏行業(yè),想辦法通過國有化或其他方式,挽救光伏行業(yè)。“抓大放小”或是很好的策略。很多民營企業(yè)家害怕國有化,其實被國有化的企業(yè)是很少很少的,不是行業(yè)問題,而是這家企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出了問題。任何一個行業(yè),都沒有永遠的春天,要過冬,企業(yè)家需要練內(nèi)功。雖然也沒有永遠的冬天,但你要等得到立春。(岳敬飛系松禾資本投資總監(jiān))